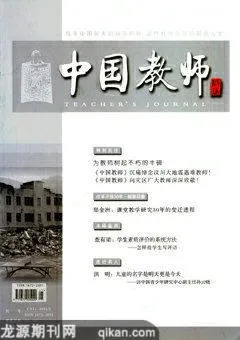“城鄉孩子互換體驗”帶給我們的深層思考
筆者曾在新疆支教兩年,有一位朋友聽說那里條件比較艱苦,當地的農牧民生活水平還比較低,但是大多數農牧民子女學習非常刻苦,比漢族孩子努力多了。這位朋友曾經想讓自己養尊處優的孩子能夠和當地的學生“結對子”,讓他通過接觸,認識到這個世界上還有貧富兩極分化,讓孩子能夠學習維吾爾族孩子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自強不息,通過自身的努力改變生存環境,改變家鄉落后面貌的精神。筆者在支教時,也常常教育、鼓勵當地的孩子能夠“走出去,放眼看世界”。
在西部大開發的宏偉戰略中,山東招遠高級職業學校和寧夏固原等地聯合辦學,學校團委開展了城鄉孩子互換體驗活動,讓學生在另外一種環境中生活一段時間,讓他們有機會跳出原來的生活圈子,打破城鄉壁壘,到生活的另一端去感受別樣人生,從而達到自我教育的目的,端正學習和生活態度,以積極的心態迎接今后的挑戰。
有的家長為了讓城市里已經厭倦了富足生活的“紈绔子弟”親歷生活困苦和艱辛,真正明白自己富足生活的珍貴,找到生活的意義和目標,他們親自物色互換的對象,有意識地選擇條件反差較大的家庭,想真正觸及孩子的靈魂深處,讓孩子認識自己的問題所在。
也有的城市家長讓自恃有優越感的孩子,到沿海那些已經先富起來的新農村去,挫挫他們的傲慢與自負,褪去城市的浮華與霸氣,讓他們懂得理解與尊重,感受田園牧歌式的清新與恬靜,明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回歸自然未嘗不是現代社會的一種理想的選擇。
隨著活動的深入開展,引發了我們對教育問題的深層思考。那種走馬觀花、蜻蜓點水式的互換已經不適應公眾的需求。人們不再滿足于讓農村的孩子來體驗坐車乘機、眼花繚亂的快感,也不再滿足于讓城市的孩子領略山青水綠、鳥語花香的新奇。我們關注的焦點,不再只是孩子自身的問題,還有家長的問題和教育環境的問題。
我們發現,一些成人眼中的叛逆的問題少年,在新的家庭面前,人性的復蘇,親情的回歸,速度之快令我們詫異。由此我們想,孩子性格的扭曲,人格的殘缺,家長和社會難道就沒有責任嗎?
對于生活在貴州、云南等地山林深處的少數民族地區的孩子們,十幾年來未曾走出大山一步,但他們的內心從沒有停止過對外界的向往。第一次走出大山的他們,人生注定要隨之改變。要么在感覺體驗中迅速和現代都市接軌;要么進入城市家庭后,城市人的生活刺激了他們敏感的心,緊緊地將自己封閉起來,帶給他們的是壓抑和沉默。因此提前做些預防性的心理疏導是必要的。走出大山,開闊視野,是必然的,但是走出大山不是人生的唯一選擇。我希望這些孩子在經歷了城市的洗禮之后,將來能夠利用千百年來當地村民保留下來的完整的民族習俗、服飾和傳統所形成的“文化孤島”的資源優勢,弘揚這份古樸與純真,開發旅游資源,吸引人們來這里感受原始和現代氣息交融的獨特氛圍和神韻,發展當地經濟,造福一方百姓。
筆者在新疆支教時,每當到了肉孜節和庫爾邦節(如同我們漢族人的小年和春節),我們都會被維吾爾族朋友邀請到家里做客。過古爾邦節的時候,他們也給孩子分發壓歲錢。至今給年紀小一點的孩子,仍然是一兩元,大一點的也不過是五元錢。他們送給孩子的只是一種新年的祝福,單純自然。而我們內陸地區,長輩給孩子壓歲錢,動輒上百元甚至上千元,好像不如此不能顯示自己的闊綽,不如此不能表達與主人之間的情誼深厚,甚至還有人借機大搞權錢交易,傳統的節日變了味!到頭來,有的孩子春節期間竟然能收到上萬元的壓歲錢。新學期開學后,孩子之間互相攀比、炫耀、打壓,對他們健康成長十分不利。另外,維吾爾族人民信仰伊斯蘭教,從小他們就懂得:在長輩面前,孩子不能抽煙喝酒;在哥哥面前,弟弟不能抽煙喝酒。長幼尊卑,井然有序。而我們,則常常當著孩子的面推杯換盞,噴云吐霧。孩子耳濡目染,有何裨益?
“城鄉孩子互換體驗”,如果能夠把握合適的時機,選擇合適的對象,針對孩子實際,找準切入點,孩子不可能沒有觸動。他們會朝著教師和家長期望的方向發展,在感受別樣風情的同時,也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自己。另外,在孩子接受熏陶和感染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好好地審視一下目前的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以免再給孩子造成不良的影響。
(作者單位:1.山東招遠一中2.山東招遠高級職業學校)
(責任編輯:王哲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