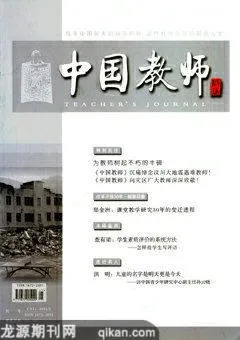語文測評,為何重復昨天的故事
我們這里說的“昨天的故事”,是指在世紀之交的語文教育大討論中受到人們猛烈抨擊和強烈反對的語文標準化考試,主要表現在:語文測試唯教參、命題者擬定的標準答案是從,如:“雪化了是( )”,只能填“水”,或“水蒸氣”,填“春天”就不行。根據句子“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刻畫描摹得非常逼真”的意思寫成語,只能寫“同心協力”和“惟妙惟肖”,若寫成“齊心協力”和“栩栩如生”就只能判錯。“進”的反義詞只能是“出”,而不能是“退”。又如作文命題學生根本不用思想,只需編造一個故事或找一些論據來證明命題者思想就行了。寫《堅韌——我追求的品格》或《戰勝脆弱》,只有編造父母雙亡,父母下崗或自己身殘志堅的故事,才能得一個好分數。寫《春天》,只能跟著古往今來的文人們贊美春天好,若說春天不好,老師就指責你胡思亂想、動錯了腦筋。從理論上說,在語文教育大討論距今已十個年頭,《語文課程標準》已頒布實施,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已向縱深推進的今天,我們所列舉的這些,應早已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但是,這些不該發生的故事,在2006年11月的某市小學二年級半期語文考試居然又重演了。試卷中有一道題是這樣的:
把相關聯的詞語用線連起來:
涼爽的 藍天 認真地 點頭
高遠的 花香 使勁地 叫喊
淡淡的 空氣 緊緊地 觀察
清清的 陽光 慌張地 拉住
金黃的 河水 微微地 推開
試卷發下后,同事領著他的孩子找到我,說孩子不服,理由是老師判錯了,扣了他的分。我仔細看了試卷,其中,孩子是這樣連接相關聯的詞語的:
淡淡的河 清清的花香 使勁地叫喊慌張地推開
我作為一個語文教師,反復推敲,實在找不出孩子這樣連接何錯之有。評卷教師、也是課任教師一定判錯了。為慎重起見,我讓孩子說說他的理由,他說:“可以造句呀!”“說來聽聽。”我鼓勵他道。
“小明被綁架了,他使勁地叫喊。”
“狗在追小紅,小紅慌張地推開門。”
對這些需要連接的詞語,學生懂了,會用了,也就足夠了。對于一個小學二年級的學生,我們還要苛求他們什么呢?我不能找不是理由的理由讓孩子與命題者、與教師的想法一致;出于成人世故,我也不敢鼓勵學生去找老師討回公道,因為我實在不敢想象學生這樣做的后果。
據了解,這是全市小學的統一語文考試,這份試卷不是出現在一所小學,而是該市所轄的所有小學。
兩年前,一小學期末考試五年級的語文試卷有這樣一道習作題。
夏天有什么特點?你喜歡夏天嗎?為什么喜歡?請你仔細觀察,夏天的人、景、物等有什么變化,把它寫下來,題目自擬。
客觀地說,這道習作題貼近學生實際,能讓學生有話可寫。因為考試之時,正是夏天,學生只要看看室內,望望窗外,回憶剛剛過去的春天,聯想即將到來的秋天,都能十分輕易寫出夏天人、景、物等的變化。但是就是那刺眼的“為什么喜歡”一句話,給人以被強迫思想的感覺。我不知道命題者為什么要強迫所有的學生都喜歡夏天,而且要說出喜歡的理由。那不喜歡夏天的學生又寫什么,如何寫呢?唯一的辦法只能是為了得到一個好分數,言不由衷地說謊。據了解,這套試卷是用于全州小學語文統一考試。這與2002年5月31日《中國青年報》第五版披露的武漢市荊州區某小學老師強迫學生都寫“春天好”如出一轍。其實,在作文中,喜歡或不喜歡夏天,與培養學生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無多大關聯。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學生喜歡或不喜歡夏天,都有他們各自特殊的緣故,命題者和教師應尊重和保護學生的情感自由。《語文課程標準》要求在寫作教學中,要“珍視個人的獨特感受”,“要感情真摯,力求表達自己的獨特感受和真切體驗”,要“說真話、實話、心里話,不說假話、空話、套話”、“要減少對學生寫作的束縛,鼓勵自由表達和有創意的表達”。可以說,無論是要求學生贊美春天好,還是強制學生喜歡夏天,都背離了《語文課程標準》,剝奪了學生言說的自由,扼殺了學生的言語生命,嚴重違反了語文教育的規律。
為什么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向縱深推進的今天,語文測評還在重復昨天的故事,發生不該發生的嚴重教育事故,這很值得我們每一個語文教育工作者、每一個關心語文教育的人深入探究。
是“應試教育”的壓力嗎?不是! 這些年,不少人把語文教育的低效簡單地歸罪于“應試教育”,這可以說是大錯特錯。因為在我國九年義務教育已基本普及的今天,小學階段的教育基本不存在升學考試的壓力,完全可以按照語文學科的特點和語文教育的規律,根據《語文課程標準》的要求開展正常的語文教學活動,讓學生愿學、樂學。
是語文教材質量有問題嗎?也不是!在世紀之交的語文教育大討論中,語文教材也曾是屢遭詬病的對象,且言之鑿鑿,但當我們打開新世紀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語文教材,可謂“新”風拂面。如教材編者把像《雪化了是什么》《事物的正確答案不止一個》等有利于培養學生創新思維和創造能力的文章編入語文教材,并沒有要求我們教師和學生都贊美春天好或都喜歡夏天呀!人民教育出版社義務教育課標準實驗教材《語文》一年級上冊有一篇叫《四季》的課文:
草芽尖尖,他對小鳥說:“我是春天。”
荷葉圓圓,他對青蛙說:“我是夏天。”
谷穗彎彎,他鞠著躬說:“我是秋天。”
雪人大肚子一挺,他頑皮地說:“我就是冬天。”
課文后面還有一道很有意思的《說說畫畫》的練習:“你喜歡哪個季節?為什么?把你喜歡的季節畫一畫。”
在這里,課文并沒有說哪個季節美或哪個季節不美,而是四季都美,四季都可愛。課文后面的練習只是問“你喜歡哪個季節?”并沒有硬性規定學生喜歡或不喜歡哪個季節。這才是正確、全面、健康的語文教育,尊重學生獨特感受體驗的個性教育。如果說是語文教材讓我們命題者和評卷教師這樣做的,那語文教材何罪之有。只能說語文命題者、評卷教師的語文教育觀念還停留在語文標準化考試時代,他們對《語文課程標準》和語文新教材的教育理念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
是語文教學參考書的原因嗎?更沾不上邊。顧名思義,語文教參,僅供參考,并沒有讓命題者和教師照抄照搬。葉圣陶先生說,在語文教學過程中,教師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更何況是語文教學參考書呢。
語文測評重復昨天的故事,既不能歸因于“應試教育”,也不能怪罪語文教材,更非語文教參的原因,那原因又是什么呢?在我看來,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命題者缺乏編制語文試題的資質,考試管理部門缺乏一套嚴格科學的管理程序。命題者只要略有一點語文常識,略知語文教育規律,決不會犯在今天看來已是最低級的常識錯誤。連小學二年級學生都知道“使勁地叫喊”、“慌張地推開”可以造句,命題者的智商總不至于不如一個小學二年級的學生吧。而作為考試管理部門,倘若認真審查命題者的資質,并聘請真正的語文教育專家對其編制的試題予以審查,這樣的低級錯誤完全是可以避免的。須知,在考試“指揮棒”功能仍顯著的今天,違反語文學科特點和語文教育的考試,對語文教學的誤導是顯而易見的。現今,我們中小學生作文仍充斥假話、空話、套話,選材雷同、立意趨同,詞匯貧乏,語言表現乏力,缺乏個性,作為語文教學“指揮棒”的語文測評,難辭其咎!
第二,語文教師自身的素質有待提高。長期以來,不少語文教師形成了這樣一種思維定勢:凡語文教材、語文教參、語文試題及標準答案,一切都照單全收,缺乏基于語文學科和語文教育立場的自我分析和判斷能力。我所在城市的所有小學,都要求學生購買某出版社編寫的語文習題集——《英才考評》和《英才教程》,且教師都要求學生按部就班、一題不漏地完成。不少語文教師之所以形成唯教材、教參、標準答案是從,照單全收的思維定勢,其深層原因是缺乏從事語文教學的基本語文素養和語文教學素質。近些年,為提高中小學教師學歷,一些地方高校與當地各縣市聯合舉辦了各種形式的學歷提高班。我曾先后為近千名語文老師面授過寫作課。在授課結束考試時,我先將一道題為《傘》的兒歌改成散文排列形式:“公路邊的大樹,是小喜鵲的傘。水塘里的大荷葉,是小青蛙的傘。山坡上的大蘑菇,是小螞蟻的傘。下雨了,大家都有一把傘”。然后編了兩道小題,要求學員從作者寫作意圖的角度分析歸納這節文字的主題,指出這節文字屬于什么文體。結果,有超過半數以上的學員不能分析歸納主題,多數學員說這節文字是記敘文,說明文或議論文。我實在不敢想象,這些每教學一篇課文都要分析歸納中心思想的老師,自己竟然不能獨立分析歸納中心思想,連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不知為何物的語文教師,居然去教語文。因而,省事而保險的做法,只能照搬教參和標準答案。或許,這樣的推測有些以偏概全,然而數百人竟是這樣一種狀況,又能“偏”到哪里去,豈不讓人怵目驚心。
但是,若把語文教學低效的“板子”完全打在語文教師身上,也是不公平的。為了推進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各地教育部門每個假期都要舉辦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新課程培訓班;為了提高小學教師學歷,各地教育部門和高校聯合舉辦了各種形式的學歷提高班,小學教師大專化的目標已基本實現。作為教育行政部門和相關的培訓機構,包括曾對中小學語文教師進行職前教育的各級各類師范院校是否也應該反思一下,自己是否也有一份責任,也該挨一點“板子”呢?
在世紀之交的語文教育大討論中,有不少學者曾不無偏激地說語文教育“誤盡蒼生”、“人神共憤”。某大學中文系教授說得更具體:在完成識字教學后,哪怕所有語文課都讓學生自己讀書,也要比現在強。看來,這樣的聲音在今天依然沒有完全消逝,還不時在我們耳邊回響。
救救語文!
救救在語文課堂上痛苦呻吟的孩子!
救救在語文考場上為尋覓標準答案而“捻斷數莖須”、失卻童心童趣的孩子!
(作者單位:貴州省黔南民族師范學院中文系)
(責任編輯:王哲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