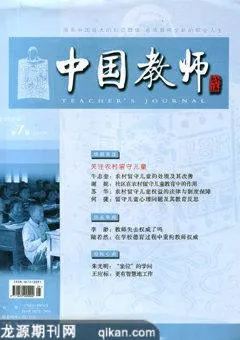漢字與古代田獵文化
《孟子》中有這樣一段話:“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這是對遠古時期先人生存環境的描述。當時,天下一片洪荒,野草叢生,亂木成林,鳥獸大量繁殖,對人類形成了嚴重的威脅,即使在中原地區,也都布滿了鳥獸行走的印跡。這些印跡對人類的生存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人們正是根據這些印跡來判斷鳥獸的類別,如果是兇猛的鳥獸,則提高警惕,或者隱藏躲避;如果是弱小的鳥獸,則設法捕獲,用以充饑。后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需要區分的事物越來越多,光靠鳥獸之跡已無法滿足這種需求,于是人們在鳥獸之跡的啟發下,發明了漢字。這正如許慎《說文解字敘》所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看到鳥獸的足跡,知道據此可以辨別不同的鳥獸,因而開始模仿鳥獸的足跡創造文字。可見,漢字從一產生起,就跟田獵有著密切的關系。
甲骨文有一個(biàn)字,后來演變為,正像一個野獸的腳印。這個字小篆字形作,楷書字形作“釆”。《說文》解釋說:“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古人造字時,正是用鳥獸的足印來表示辨別之義的。后來,這個字分化成兩個字,即“釆”和“番”,其中“釆”專表辨別義,“番”則專表獸足義。《說文》:“獸足謂之番,從釆,田像其掌。”“番”金文寫作,其下部不是田地的“田”,而是像野獸圓圓的腳掌。由于“番”字和腳有關,后來便又加上了“足”字旁,作“蹯”。《左傳?宣公二年》記載,晉靈公是一個無道之君,有一次他的廚師做飯時沒有把“熊蹯”煮熟,晉靈公一生氣就把他殺了。這里所說的“熊蹯”就是熊掌。其他一些從“釆”、從“番”的字,也往往有“仔細觀察”、“分析”之類的意義,如“審”(“審”的繁體字)義為“仔細辨別”,“釋”義為“分別物類”,“悉”義為“詳盡明白”等,這些都可以看出“獸足”和“分別”義之間的關系,也可以看出田獵在漢字構形中留下的痕跡。《周禮》中有所謂的“跡人”之職,其任務就是專門察看鳥獸的足跡,以判斷它們的藏身之處。《左傳?哀公十四年》:“跡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就是說,跡人來報告,在逢澤這個地方發現了一只孤身的麋鹿。
田獵的“田”和田地的“田”本為一字,甲骨文像田地阡陌縱橫的樣子(見圖1)。那么,為什么田獵和種田有如此密切的關系呢?前面說過,由于草木叢生給野獸提供了藏身之地,于是古人采用焚燒的方法,驅趕或者圍捕野獸。野獸趕走了,野草也燒光了,留下來的空地正好可以開墾出來種植莊稼,這樣,農田便出現了。
除了火獵之外,古人還使用弓箭、網、陷阱等多種狩獵方式。如 (罹難的“罹”)是用帶有長柄的網把鳥罩住,(羅網的“羅”)是用張設的大網把大象圍住,(陷阱的“陷”)是用挖好的陷阱把鹿困住,(表示野豬的“彘”)則是用箭將野豬攔腰射穿。這些生動形象的字形,為我們再現了當時狩獵活動驚心動魄的場面。
狩獵的“狩”與野獸的“獸”本為一字,楷書繁體寫作“獸”,甲骨文有等多種寫法(見圖2)。在這些不同字形中,右邊表示動物形狀的部分,無論繁簡都是“犬”字,沒有出現其他動物,說明在這個字形中“犬”不是被獵獲的對象。因為如果“犬”是代表獵獲對象的話,它就應該可以用其他動物來代替,很多漢字都可以證明這一點。如羅網的“羅”既可以寫作(網住大象),又可以寫作(網住鳥)、(網住鹿)、(網住老虎)、(網住兔子)、(網住野豬)等,最初造字時并無定形,在能夠用網捕捉的動物中,選一個代表就行了。而甲骨文“狩”字中的“犬”,沒有被別的動物替換的用例,說明“犬”在構成該字時,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說文》:“狩,犬田也。”所謂犬田,就是用犬去打獵。田獵的“獵”字從犬,很多可以充當獵物的動物也從“犬”,這說明,古人很早就開始使用犬進行捕獵了。犬的嗅覺靈敏,又通人性,可以幫助人們找到獵物的藏身地,因而成為古人打獵的好幫手。可見,甲骨文“狩”字中的“犬”,不僅不是捕獵的對象,反而是以捕獵者的身份出現的。
圖2:甲骨文的“狩”字
除了“犬”字之外,甲骨文“狩”字的另一半作、,或作、、,對于這部分字形究竟代表什么,還存在著一些爭議。一般認為,寫作、的,后來演化為干戈的“干”字;寫作、、的,后來演化為“單”(也就是后來的“彈”)字,其實它們最初都是一個字,像一種捕獵工具的樣子。這種工具剛開始只是一個簡單的樹杈,可以用來捶打或戳刺野獸,后來逐漸在樹杈的兩個頂端,分別綁上圓形的石塊,以增加打擊的力量。這種捕獵工具,不僅可以在考古發現中找到證據,而且可以在現代民俗中得到證明。半坡遺址出土了大量的經過琢磨的圓形石塊;周口店遺址博物館的放映廳里,也藝術再現了石器時代北京人用樹杈和石塊捕獵的場景;甚至遠在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工具;而更為鮮活的例子,就存在于云南納西族不久前的田獵活動中。據瑞典人林西莉《漢字的故事》描述:納西族人在半公尺長的繩子兩頭各栓一個石球,中間做一個繩扣,或者用繩頭結一個把手,然后手執把手,讓石頭在空中旋轉,待達到一定速度時,朝野獸的方向飛速拋出,擊中獵物的身體或者纏繞獵物的腿腳。甲骨文中又可以增加一只手,作,正像手執長柄拋擲石塊的形狀,這更證明了這種田獵方式的推測并非臆想。只有樹杈時作“干”,增加石塊后作“單”,發明彈弓后作“彈”,用于打仗時作“戰”。這一系列漢字表明,古老的石塊雖然在不斷地演進,但其原始的蹤跡則一直保留在漢字字形中。
隨著田獵技術的提高和工具的改進,古人捕獲的獵物越來越多,在滿足人們食用之外開始出現盈余。怎么安置剩余的獵物,成了當時人面臨的新問題。人們逐漸摸索著對獵物進行圈養,甲骨文的“牢”字正描述了這一過程:圈的是牛,圈的是羊,圈的是馬。這些動物不怎么兇猛,可以圈養起來,以備食物缺乏時食用。圈養動物的做法,也標志著古人由田獵時代過渡到畜牧時代,由居無定所轉變為有了相對固定的家。“家”的構形是房子里面有一頭豬,意味著飼養動物才是“家”的真正開始。羅常培《語言與文化》一書說:“中國初民時代的‘家’大概是上層住人,下層養豬。……現在云南鄉間的房子還有殘余這種樣式的。”現代民俗學的考察證明,不只是在云南鄉間,在其他不少地區,都可以看到“家”字所勾畫的“人畜同舍”的情景,如傣族的竹樓、羌族的碉房、苗族的吊腳樓等。
在飼養動物的過程中,人們逐漸發現,動物不僅可以養來吃,還可以通過馴化,使之成為勞作的工具。在古代漢語中,表示勞作的意義常用“為”字,甲骨文寫作,像用手牽著大象的樣子。那么,勞作和大象有什么關系呢?原來,我國遠古時期中原地區氣溫較高,濕度很大,十分適合大象生存。在山西、陜西、河南等地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了不少大象化石。直到商代的遺址中仍然可見大象的遺跡,而且在甲骨文中,還有關于商王田獵時“獲象七”的明確記錄,說明在那個時候,大象在中原地區依然常見。只是到了西周時期,由于氣候及其他原因,大象才被迫南遷。據文獻記載,古人很早就開始馴化大象。如《論衡?書虛》記載,傳說“舜葬于蒼梧下,象為之耕”。這是用大象耕種的較早的記述。據羅振玉推測:“古者役象以助勞,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馬以前。”后來,大象在中原地區逐漸為牛馬所代替,但在南方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用象的歷史則一直沿用了很久。如《史記?大宛列傳》把當時的滇越國稱為“乘象國”,唐代的傣族用象耕作,元明清時期用象作戰等,都是對甲骨文“為”字所表示的古老勞作方式的傳承。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王哲先)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圖表、注解、公式等內容請以PDF格式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