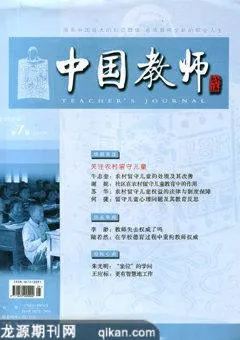《人間詞話》深處的教育啟迪
讀書時候,我便尤其鐘情于語詞委婉、表達含蓄的宋詞,長短錯落的字里行間,那遮掩不住的別緒閑愁,千絲萬縷地縈繞我花季雨季潮濕的心情,一時間便恍如纖手泛舟的女子,緩緩劃槳進入宋詞的意境里。于是,賞花時,我仿佛看到李后主“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的去國憾恨;聽雨時,我仿佛聞見李易安“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的身世之慨。在這個人心浮躁的年代,無可否認吟誦宋詞曾給我們的心靈一份超然的慰藉,但,讀她,誰曾求甚解過?愛她,誰曾輾轉反側過?
直到那個月光如水的夜晚,我點一盞小燈,捧讀起青島市中小學教師“十一五閱讀工程”的《每周一讀》2007年卷中《人間詞話》的節選,隔著久遠的歲月長河,聆聽國學大師王國維精辟獨到地品宋詞,印象中那些活色生香的文字再次被溫暖喚醒。
大師說: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綜觀古今文論史,“境界”說早在劉勰《文心雕龍》和鐘嶸《詩品》中已見端倪,至王國維筆下已將其作為審視古代詩詞曲賦的審美宗旨。“境界”何物?引人入勝,流連忘返,余音繞梁,三日不絕,等等,使人共鳴之筆。“境界”何來?此便需要詞人將自己的真摯感情和景物憑借文字巧妙地珠聯璧合,所謂情景交融。正如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為何婦孺皆知、膾炙人口,只因那個月圓人不圓的仲秋夜,詞人把原該自怨自艾的哀怨牢騷轉化成了一份豁達的胸襟,月尚有盈虧,人又豈無離別,只要彼此牽掛的親人平安,縱使天各一方也可共同欣賞到這一輪美好的明月,于是就有了“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千古佳句。
“各種事物都有它的極致。虎嘯深山、魚游潭底、駝走大漠、雁排長空,這就是它們的極致。”我又想到了孫犁先生的這句話。那么我們教育的境界和極致又是什么?沾有余香的贈花之手就算是創造教育的境界了嗎?依我看來,讓授花者懂得他手中接過的玫瑰可以芬芳更多人的人生,這樣的教育境界當屬“自成高格”。
大師還說:“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詞美,美在她錯落有致的長短句;詞艷,艷在她華麗考究的遣詞。可滿目綺麗繁華非但境界全無,還會使人審美疲勞,于是細節便是提升境界的取勝法寶,李頻的“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便是作者嘔心瀝血提煉的艱辛,而值得慶幸的是王國維先生解得“字字看來都是血”,牽一發而動全身,抓住一個字眼便使得詞的意境了然于心。
諸如此類的名句還有“僧敲月下門”,單憑一個“敲”字,便引起我們無窮無盡的遐想,清冷明亮的一輪月,幽靜空曠的四野,虛掩著的一扇柴扉……仿佛身臨其境怡然自得。
成功的教育同樣贏在這樣看似漫不經心、實則煞費苦心的細節,在孩子不舒服的時候,輕輕地給他愛撫,為他倒一杯氤氳著愛的熱水;在孩子調皮闖禍的時候,用眼神和他真誠交流,營造出師生間的無聲勝有聲;在孩子陷入困境時,拉一把那雙稚嫩的小手,留下彌散一生的愛的芳澤……我們的教育總會因為這些愛的細節而異彩紛呈、境界全出。
掩卷沉思,竟不想在大師的啟發中引發了自己對教育的諸多思考,如今,翩翩宋詞的花事凋零了,山河蒼老了,燈火闌珊了,而大師則憑借《人間詞話》這本留給后人的精神財富而熠熠輝煌在燦如星河的歷史名家中,感謝他讓我對宋詞有了更深層次的審美,感謝他讓我對教育有了更多的回眸。
(作者單位:山東省青島市嶗山區登瀛小學)
(責任編輯:朱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