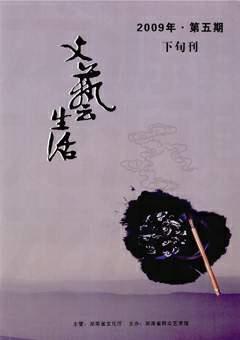論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規則的立法整合
靳姍姍 楊壘營
摘要:不安抗辯權的精華內含在預期違約制度中,只是英美法不像大陸法那樣強調不安抗辯權的突出地位,沒有這個形式化的概念而已。不安抗辯權的本質,乃在于賦予當事人對債務人缺乏履行能力的合理主觀推測,而這正是與給付拒絕或明示預期違約的根本區別所在。
關鍵詞:預期違約 明示預期違約 默示預期違約 不安抗辯權
中圖分類號:D9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09)15-
一、預期違約的概念及其分類辨析
預期違約(anticipatory breach of contract )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期到來前,一方當事人肯定地、明確地表示他將不履行合同或一方當事人根據客觀事實預見到另一方到期將不履行合同。
英美法上的預期違約制度有兩種形態:一是當事人明確地、肯定地并無條件地向相對人表示其將不履行合同義務。這種情形被稱為“明示的預期違約”(Repudiation)。①二是當事人雖然沒有明確聲明其將不履行契約義務,但其行為及客觀情況表明了他將不能到期履行義務。在許多情況下,合同一方的行為及履約能力上的明顯瑕疵,同樣會起到與語言構成的毀約同樣的作用。②這種情形被稱為“默示的預期違約”(Diminished expectation)。
預期違約源于英國1853年的霍克斯特訴德拉圖爾一案。案中被告于4月12日與原告約定,從1852年6月1日起雇傭原告為伴游服務員。但在同年5月11日,被告致函原告表示不再需要他的服務了。原告立刻提起訴訟請求賠償,法院判決原告勝訴。③主要理由是,一方當事人明確表示將不履行合同,允許受害人締結其它合同是合理的,如果讓他坐等到實際違約的發生必將陷入無人雇傭的困境。這一判決確立了預期違約受害人的訴權。而1894年英國辛格夫人訴辛格案中,被告在婚前向原告許諾,婚后將一棟房屋轉歸原告所有,但被告又將該房屋賣給他人,使其許諾成為不能。法院認為,盡管不排除被告重新買回該房以履行其許諾的可能性,但原告仍有權解除合同并請求賠償。
值得注意的是,有學者指出,在英美法系的重要著作或者論文以及法典中,從來沒有正式的將預期違約以“明示”和“默示”為標準來進行區分。實際上,在英國法上主要規定了兩種情況,即拒絕履行之表示和因債務人自己的行為而發生的履行不能。美國法上的預期違約形態有三種,前兩種和英國基本相同,屬于傳統的預期違約類型,第三種是債權人有合理理由相信債務人將不履行債務,經請求提供充分之履行保障而不提供的,視為構成履行拒絕。因此也有學者直接將英美法系中的預期違約劃分為預期拒絕履行和預期不能履行兩種形態。這種劃分的依據或許在于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609條、第2-610條規定的不同。
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610條規定,任何一方在合同義務尚未到期的情況下毀棄合同,且造成的損失將嚴重損害合同對對方的價值,非毀約方除可以等待對方繼續履行合同義務或繼續履行本方義務外,還可以停止自己對合同的履行。而何謂“在合同義務尚未到期的情況下毀棄合同”,則進一步被《美國合同法重述》第250條加以明確。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610條所規定的預期拒絕履行即相當于傳統英國法中的拒絕履行之表示和自我導致喪失履行能力,是傳統英美法系預期違約的內容。而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609條規定當事人有理由懷疑對方不能正常履行時,可中止履行,并以書面形式要求對方提供正常履約保證,對方只有在不超過30天內的合理期限內不提供擔保,才構成預期違約,這是美國新發展的預期違約形態。該種違約也即所謂的預期不能履行。
其實,在筆者看來,無論是明示預期違約和默示預期違約的劃分,還是預期拒絕履行和預期不能履行的劃分,其實質意義均在于區分預期違約人的違約表達狀態。明示預期違約和預期拒絕履行意在表達當事人明確地、肯定地并無條件地向相對人表示其將不履行合同義務,該種表示既可以是面向相對人的語言或書面表達,也可以是當事人顯而易見的明顯故意的逃避義務履行的行為,該行為之蓄意性為相對人所知。表示方式的不同不影響兩者內在的同質性——即違約人以外在的表達方式表明自己將確定地不履行合同義務,該項表達為相對方所明確感知。而默示預期違約和預期不能履行,則側重于相對人對違約人一系列外在行為的主觀推測,相對人并不能徹底且無疑地獲知對方將確定性地終局違約,而只得通過對方當事人并非顯而易見、且不具有明示針對性的默然外在行為表達,來主觀感受違約人可能面臨的履行狀況。因此,明示預期違約和預期拒絕履行,默示預期違約和預期不能履行,在本質上并無區別。與其沿用英美法通用的,易造成我們混淆不明、不知所云的預期拒絕履行-預期不能履行的劃分,倒不如完全依照我們漢語習慣,采用簡潔明確易區分的明示預期違約默示預期違約的表達方式,明、默兩端,一目了然。
可以說不安抗辯權的精華內含在預期違約制度中,只是英美法不像大陸法那樣強調不安抗辯權的突出地位,沒有這個形式化的概念而已。不安抗辯權的角色由默示預期違約扮演,明、默兩端并行不悖,縱使邏輯上略有瑕疵,但在英美法的背景下卻如滴水入海,消融于實用主義平臺而根本不成其為問題。可以說,兩大法系各取所需,互為借鑒,各自構筑起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二、我國《合同法》關于此問題之癥結所在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不安抗辯權,是借鑒了英美法默示預期違約規則,對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權進行了以下完善:
其一,借鑒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不拘泥于財產減少這唯一的條件,擴大了行使不安抗辯權的法定事由,即經營狀況嚴重惡化;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喪失商業信譽;有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這樣,就更符合現實生活的需要。
其二,“當事人沒有確切證據中止履行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的規定,可以防止不安抗辯權的濫用。
其三,突破了大陸法系對不安抗辯權救濟方法的約束,不僅可以如大陸法系一般進行中止履行救濟,在中止履行后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擔保的,還可以移植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的救濟方法——解除合同。有學者認為,這般引進,更能有效地解決糾紛,從而可以實現“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規則的一次偉大的整合”。④
筆者對此觀點不敢茍同。《合同法》在“合同履行”中規定的不安抗辯權與它在“違約責任”中規定的明示預期違約在適用上極容易產生混亂。根據第 108條的規定,“一方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義務”應屬于明示預期違約的適用范圍;而根據第68條的規定,一方“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應屬于不安抗辯權調整。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將“一方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視為“一方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義務”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連“一方轉移財產、抽逃資金債務”這樣嚴重的行為都不足以表明一方將不履行義務,那么到底什么樣的行為才能表明一方將不履行義務呢?對此,恐怕我們的立法者們也難以回答;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一方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可以視為“一方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義務”,那么不安抗辯權和預期違約在適用范圍上便發生了重疊,這樣當出現“一方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的情形時,我們是應適用第68條的不安抗辯權呢,還是應適用第108 條的預期違約呢?這給實踐中的法律適用造成了很大的混亂。
邏輯上講,在先履行義務人中止履行后以先行對待給付或提出充分擔保來對抗中止履行權利人,從而恢復合同履行。若后履行義務人未在合理期限內恢復履行能力或提出擔保,則先履行義務人獲得合同解除權。而《合同法》第94條、第108條規定的救濟途徑卻是直接解除合同,要求預期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不必經過中止履行這一緩沖的階段。由此造成相同的法定事由存在不同的救濟途徑。如此無序吸收默示預期違約制度,不僅在邏輯上造成平行混亂,有違民法體系嚴謹性的宗旨,在實踐上竟也無太大助益,形成法條沖突,在大陸法系邏輯和英美法系實用交加下淪為不折不扣的“四不像”。
三、整合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制度之立法建議
首先,應明確第94條第2款以及第108條所規定的“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合同義務”足以表明該方不履行債務的主觀意圖相當明顯,乃是以積極主動的姿態表明其將不履行合同義務,而無論其是否具備客觀上履行合同義務的能力。在此,債務人也即預期違約人客觀上將確定不履行,而非債權人主觀推測。債務人的明確的債務不履行表示使得債權人的等待或要求提供擔保等依托于債務人之自覺意識的救濟路徑失去了意義。如果考慮我國大陸法系的傳統,將其確定為給付拒絕之概念或許更合適。即將明示預期違約在法釋義學角度解釋為給付拒絕,作為債務不履行的一種法定形態,納入大陸法系債務不履行體系中。
其次,還原不安抗辯權作為抗辯權之法定類型在大陸法體系內的防御性質。不安抗辯權適用于后履行一方在客觀上出現財產惡化狀況或其他可能嚴重影響其履行合同義務之能力的客觀情形,而這些狀況或情形的出現,或是因后履行一方主觀逃避債務的意圖所導致(如蓄意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或是非因上述惡意逃避債務意圖而由其他主客觀情形(如發生生產經營困難,商業信用嚴重降低等)而致形成難為對待給付之虞。無論何種原因,終歸是由于后履行方未明確向先履行方表示其將確定地不再履行合同義務,因此先履行方只能透過上述外在情形做出一定程度的主觀推測,從而成就了其維護自身利益的“自助”舉動。一味解除合同意味著合同關系的結束,交易的終結,就后履行方帶有主觀色彩的推測而言,該救濟手段顯然過于激烈和武斷;而坐以待斃顯然亦非后履行方的理性選擇,也有違合同的公平原則和交易雙方利益的衡平。而不安抗辯權一方面賦予后履行方中止履行之權利,確保其現有利益,靜待對方恢復履行能力;另一方面可要求先履行方提供相當擔保,提供一個彼此緩沖的余地,合同不能當然解除。待先履行方面拒絕或不能提供相當擔保時,則可確定表明其“明確表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以自己的行為表示其將不履行合同義務”,給付拒絕規則(亦即明示預期違約規則)便擠身前臺,后履行方將有權選擇解除合同。
綜上分析,不安抗辯權的本質,乃在于賦予當事人對債務人缺乏履行能力的合理主觀推測,而這正是與給付拒絕或明示預期違約的根本區別所在。可以說,不安抗辯權與給付拒絕(明示預期違約)規則無論在救濟方式還是最終效力上,具有層級效應。
注釋:
①楊永清.預期違約規則研究.民商法論叢.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頁.
②王軍.美國合同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76-377頁.
③【英】AG?蓋斯特.英國合同法與案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頁.
④賀驍.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之比較研究.廣東青年干部學院學報.2004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