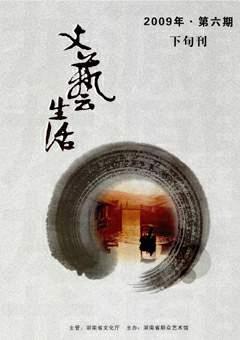淺析武氏祠畫像石的裝飾藝術
董珊珊
摘要:漢畫像石是我國文化遺產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除文物考古的史料價值外,它的藝術價值更值得我們發掘和借鑒。山東的武氏祠畫像內容豐富,本文對武氏祠畫像的畫面構圖、造型規律、和畫面處理等裝飾特點加以分析。
關鍵詞:畫像石 武氏祠 飾
中圖分類號:K879.42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09)18-
我國的裝飾藝術歷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時代人類就用開始用二方四方連續對器物進行裝飾。商周時期,大量動物形象與紋樣裝飾青銅器。到了漢代的墓葬裝飾形式就是畫像石。畫像石在全國分布廣泛,山東地區的武氏祠畫像宏偉莊重,是中國美術史上的藝術珍品。
武氏祠畫像的總體裝飾特點是莊重、渾厚。據“武梁碑”記載:“選擇名石,南山之陽,擢取妙好,色無斑黃、前設質坦、后建祠堂、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渾厚與此地的硬質石質材料有關,莊重則是畫像刻畫嚴謹工細,形象嚴謹,體現了陽剛之氣。
從雕刻技法看來,武氏祠堂畫像的雕刻是用陰刻線在打磨光的石面上刻出形象的輪廓線,然后將輪廓以外的空白剔去一層,畫面形象凸起。最后在輪廓線內的形象上加刻陰線描繪細部。這種平面減地又加線的技法使主體形象突出,不注重刻劃細部,而用簡練概括的手法突出形象,強調造型的整體感。
武氏祠的構圖形式上的最大特點是分層作畫。自上而下分為三大層,每一層又根據內容安排劃分為數格,或橫或豎。雖然有的畫面題材內容極為豐富,但畫面分層(一層刻畫神話傳說中的神仙、奇禽異獸,一層刻畫古代帝王歷史故事,另一層刻畫現實生活的宴享、樂舞百戲、庖廚、車馬出行等場景)加強了形式感、秩序性。“泗水撈鼎圖”中橋梁不僅分格畫面,也起到了穩定畫面的作用。也使畫面具有濃郁的裝飾美感,畫面情節表述明確。
采用打破時空概念的散點透視法是武氏祠畫像的又一特點。即采用視點移動的方法,所有圖像幾乎采用平視角度。鋪陳中達到氣韻生動,“氣”凝聚其中。“樓閣宴居圖”中上層左上方的五只鳥,兩只在樹上,另三只自下向上向右飛,引導視線內聚,右邊上層闕上層一人上抬的手也起到引導視線聚氣的作用。下層兩人身朝向樓房視線往中間聚,但一人回首與另一個對視,使得畫面氣流旋轉,氣韻生動。
畫面布局的特點是:“滿”構圖。形象景物勻稱的充滿畫面,沒有大面積空白,有空白處也多加鳥頭、云紋、龍頭等。畫面飽滿,形式緊湊。這與“天人合一”的自然觀聯系,表現了創作者對完善生活追求和構圖飽滿的心態。這種填充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在特定情況下,它能創造出極有情趣的藝術韻味。如“泗水撈鼎圖”中的飛鳥形象,它們慌恐飛散的狀態正襯托了繩斷鼎落一剎那的緊張氣氛,且飛的動勢是圍繞畫面中心“鼎”,加強了畫面的引導性。
有些學者認為漢字“美”就是“羊大”,就是說“大為美”。這點體現在畫像石畫面上就是,按照形象的重要性規定其刻畫的尺度。這種構圖彌補了“滿”構圖鋪陳均勻的方法客能造成的畫面無秩序、無重點的弱點。使視線首先抓住要點。如“樓閣宴居圖”上層的兩層樓房內刻畫的男女主人與身邊侍從比身體大許多。
武氏祠單個形象裝飾體現了“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的樸素、古拙之美。人物刻畫以最能體現五官特征和身體動態的側面居多。表現車馬的形態也采用側面平視角度,以陰線表示人物面部衣紋和車馬等細節,形象單純,具有剪紙般的裝飾效果。刻畫馬的形象,背部明顯夸大,同時將四條腿處理的很細,正好與碩大身軀形成對比,表現強烈的內在張力,而背部曲線成滿弓形,凝聚了力量,似乎一觸即發。
用反復、呼應、對比等裝飾手法使畫面顯出統一中的變化、靜態中的律動。幾匹馬的排列組合中馬姿態的回轉,突然上揚的馬頭跟排列整齊的馬蹄形成對比;刻畫孔門弟子二十人形態各異,俯仰有合;扶桑樹的圓、滿形態用高度的概括手法刻畫出來,體現了飽滿有生命的形象。
主題式畫面的組織也頗具用心。抓住典型人物的典型特征,表現瞬間動作,渲染主題。如“荊軻刺秦王圖”真實地再現歷史上有名的“圖窮匕見”事件。(參看《史記?刺客列傳》)選擇了荊軻奮力擲出匕首的瞬間。畫面中間立一柱子,交代了事件發生背景,也把對立的雙方荊軻、秦王分隔在兩個空間。左面荊軻怒發沖冠,形象呈直角三角形,造型擴張,暗含穩固的上升動勢。右邊秦王一段衣袖砍落,整體呈傾斜的三角形狀,刻畫退縮、逃離動勢,且兩足往朝向右邊,但頭和手臂回轉,描繪出秦王被突來的場面嚇壞慌忙逃竄的瞬間動作。而秦舞陽像卻不倒翁一樣嚇倒在地,四腳朝天,更襯托出荊軻勇武的形象,構成了活靈活現的畫面。
武氏祠畫像石風格嚴謹工細,具有剪影式的效果。其裝飾的構圖、造型、神態刻畫和畫面處理等方面都展示了古代藝人的造詣。它包含的裝飾美的因素對我們今天裝飾藝術的發展具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李硯祖.裝飾之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2]張從軍.黃河下游的漢畫像石藝術.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