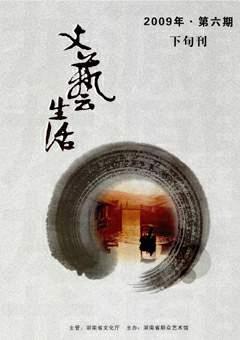再讀《文心雕龍》
蒲 政
摘要:《文心雕龍》評論了晉宋以前二百多位重要作家,總結了三十五種文體的源流演變和特點,全面論述了文學創(chuàng)作和評論上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全書共五十篇,本文不在于《文心雕龍》做深入的學術研討,而是介紹《文心雕龍》的基本內容。
中圖分類號:I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09)18-
讀《文心雕龍》必須要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和作者的身世、思想、和著書動機、意圖等,特別是魏晉以來盛行的世族制與出身寒門的劉勰之間的矛盾;漢末儒學衰微之后佛道思想流行,劉勰既是佛教信徒而又高舉“征圣”、“宗經”旗幟的原因和實質;建安以后文學藝術由經學附庸轉而獨立發(fā)展,出現(xiàn)了文學史上的空前繁榮,又很快走上了追逐浮華的道路,產生在這個時期的《文心雕龍》是怎樣對待這種趨勢的。這些是《文心雕龍》研究者不可心中無數(shù)的問題。有的須做專題論述,有的可從歷史和文學史著作中知其詳情,有的則可從《文心雕龍》本身得到認識,這里不作評述。
一、總論
由《原道》、《征圣》、《宗經》三篇構成。《原道》中所論“自然之道”,主要說明萬事萬物有其形就必有其自然之文采:“形立則章成矣,聲發(fā)則文生矣”。劉勰以此說明:文學作品必須有文采。持論既重文采,又反對雕琢繁飾,全書從這一基本觀點出發(fā)。《征圣》、《宗經》兩篇主要是強調學習儒家經典的寫作原則,這種思想集中體現(xiàn)為《宗經》篇的“六義”,認為學習儒家經典對文學創(chuàng)作有六大好處:“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教)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邪);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要求從儒家經書學得“情深”、“風清”、“事信”“義直”等,是側重于內容方面的要求。劉勰認為圣人著作“銜華而佩實”,所以《征圣》篇強調:“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這正是《原道》和《征圣》、《宗經》三篇總論提出的核心觀點。第四篇《正緯》,主要論緯書(漢代以神學迷信附會儒家經義的一類書,其中也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話傳說,也記錄一些有關古代天文、歷法地理等方面知識)之偽,沒有什么重要意義。
二、文體論
從第五篇《辨騷》到《書記》共21篇,為文體論。這部分對各種文體大都從四個方面來論述:一是文體的起源和發(fā)展概況。二是解釋文體的名稱、意義。三是對各個時期有代表性的作品進行評論。四是總結不同文體的特點及寫作要領。所以,這部分不僅論文體,還具有分體文學史的意義,是批評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本書的創(chuàng)作論證是以這部分所總結各種文體的創(chuàng)作經驗為基礎提煉出來的。
三、創(chuàng)作論
從《神思》到《總術》共十九篇是創(chuàng)作論;《時序》、《物色》兩篇介于創(chuàng)作和批評之間,有一些論創(chuàng)作的重要意見。這是本書的精華所在。分別對藝術構思、藝術風格、繼承與革新、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文學與社會現(xiàn)象、自然現(xiàn)象的關系等重要問題作了專題論述;也對聲律、對偶、比興、夸張以至用字謀篇等問題進行了具體的探討。不少論述是相當精辟的,且為文學理論史上第一次所作的專題論述。它總結了先秦以來點點滴滴的有關論述,也對后世文論有著深遠的影響。
對于這部分內容,我們要逐篇進行深入細致的研讀,不能割斷和全書的聯(lián)系而孤立地看待。首先,每一個論題都是在總論的基本觀點指導之下所作論述;其次,各篇之間也有一定聯(lián)系,合之則成一整體。如《風骨》篇提出“風清骨峻”的要求,怎樣才能把作品寫得“風清骨峻”?本篇提到必須“洞曉情變,曲昭文體”,這就是緊接在《風骨》之后的《通變》、《定式》兩篇繼續(xù)論述的內容。有人讀到《聲律》以下有關藝術技巧的幾篇論述,就懷疑劉勰是形式主義論者。如結合《情采》篇強調的“述志為本”,再從“連辭結采,將欲明經”中了解到劉勰論辭采的目的,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所以,應掌握它一篇一論的特殊結構而從全面著眼,這是閱讀《文心雕龍》應特別注意的問題。
四、批評論
本書集中闡述文學批評理論的是《知音》篇,這也是需要從全書著眼的一個問題。把全書作為一個整體看,三篇總論也就是批評論的總論了;文體論就是對各種文體的作品所作評論,也就是作品論了;《才略》篇論述歷代作家的才華,《程器》篇論歷代作家的品德,就是作家論了。創(chuàng)作論中所論創(chuàng)作原理,也正是劉氏評論作家作品的原理。所以,從整體看,就可見其批評論相當全面豐富;也只有如此,才能認清劉勰的文學評論。
此外,最后一篇《序志》說明作者寫此書的動機、意圖、態(tài)度、以及全書內容的安排等,對了解劉勰其人其書都很重要,雖然列書末,實應先讀。在研讀《文心雕龍》過程中,筆者也產生了以下幾個疑問:
第一,《頌贊》篇:“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周振甫注曰:“極,終也。”即是說:“四始”都是美好的,《頌》是排在最后的。這和緊接著的闡述在敘述邏輯上是不通的。因為緊接的闡述是:《頌》呀,包容了世間的一切美德!是眾美之極也。所以,我覺得此處的“極”字應該作“最”解為妥。
第二,《詮賦》篇:“詩有六義,其二曰賦。”為什么要強調“賦”居其二呢?這和今天“賦、比、興、風、雅、頌”或者“風、雅、頌、賦、比、興”的排法怎么不一樣呢?“賦”的古今意義是否一樣呢?
對三,陶淵明乃晉、宋時期的大家,為什么《文心雕龍》卻不見提及?是不是陶淵明在《文心雕龍》時代還不夠偉大呢?又是為什么原因成就了陶淵明在后世地位的了?
以上幾個問題,是在讀書時偶然想到的。有先賢“述而不作”的漂亮借口在前,筆者也就僅僅提出來罷了。
參考文獻:
[1]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2]周振甫.文心雕龍.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注.濟南:齊魯書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