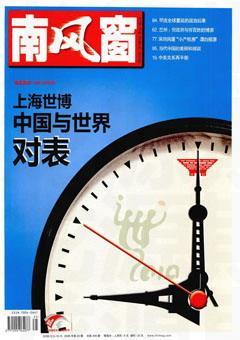打造幸福的世博會
陳惠雄
世博會要追求快樂的可持續性,成為中國確立幸福觀、處處體現以人為本的轉折點,不應過分追求表面的奢華。
上海的世博會,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實話實說,上海世博會這個主題拔得不夠高,它的關注點還是城市本身的發展。世博會作為一個多元文化對話的平臺,歐洲文化、美國文化、中華文化,以及其他文化都會在這個平臺上對話。那么,在中國大地上會不會碰撞出一股“世博精神”,激發出新的文化和價值觀來呢?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了30來年,最近幾年國內外調查都顯示,中國國民的幸福感沒有什么提高。“經濟有發展,快樂無提高”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一個新難題。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種狀況呢?
最主要的、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以往我們的一些經濟發展并不是以人為本的發展。人的本是什么,是快樂幸福,即經濟的發展必須要圍繞人的快樂來進行。在經濟學上,經濟發展是工具價值,人的幸福快樂才是終極價值,工具價值最終是為了人民快樂幸福這個終極目標服務的。假如GDP上去了,但人們的幸福感沒提高,有焦慮、有過多的競爭、有過大的貧富差距、有過多的生態環境的污染、沒有潔凈的水、沒有閑暇,這些與生命相關的東西都被鏟除掉了,人民的幸福寄托到哪里去?當你用50個單位的環境犧牲來換取30個單位的GDP增長的時候,這種增長還不如不增長。
中國人的幸福指數為什么會比較低,歸根結底是一些地方政府以GDP為中心,傳導到企業,企業則以利潤最大化為中心,再傳導到個人,個人以財富增值最大化為中心,這樣就形成了從宏觀到中觀到微觀這樣的“拜物教”價值傳遞鏈條,局部社會已經變成一個一切向錢看的社會。
過分地追求財富,追求GDP最大化帶來對人們健康的損害,對生態的損害,對閑暇的侵占,使得人們喪失安全感,導致精神貧困和焦慮,所有這些問題都會導致人們幸福與健康的下降。往深里面講就是價值觀危機,現在有些人既不信鬼神,也不信良心,什么都不相信,只信錢,什么賺錢什么干,這是最危險的。
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里,少數人又在政府部門把自己的部門利益法律化,《人民法院報》報道說已經有“部門利益法律化”的現象,為了鞏固部門的利益,以法律的條文定下來。
只要以GDP為中心的導向不轉過來,只要地方政府不真正把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落實下去,那不管這個社會的GDP如何增長,個人錢如何多,社會都會陷入精神貧困的狀況里面。
中國人到歐洲旅游,最直接的感受是為什么別人可以這么閑,同時有那么高的收入,有比較明顯的幸福感?而中國30多年持續發展,GDP和各類基礎設施有了很大發展,人們生活的硬件整體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某些方面中國甚至超過了一些發達國家,但人們的幸福感并無明顯提升,無論是所謂的成功人士還是一般老百姓,大多數都處于焦慮的狀態,對未來沒有安全感。
為什么中國和歐洲會存在這種差異呢?我們可以從歐洲文化與中國文化以及美國文化的差異中尋找根源。
歐洲文化是傳承了古希臘的社群主義文化或者叫共同體主義的,那個文化的核心價值強調人與人的平等,它追求社團整體的和諧。馬克思的思想一定意義上也傳承了古希臘的共同體主義精神,強調人與人平等的文化思想。但到了15世紀歐洲文藝復興以后,由強調集體的人突變為強調個體的人,人們開始強調個體人的自由解放,這種情況導致了歐洲的個體競爭,自由競爭出來了。這種競爭正好適應了工業革命的需要,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發展。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歐洲又逐漸重新回歸強調人與人的和諧、平等、自由、閑適的古希臘文化的基礎上,所以歐洲的共同體主義文化根基就形成了今天的福祉社會,或者叫福利社會,這就是歐洲文化。
現代美國文化主要是15世紀文藝復興以后的那一批歐洲人過去的,那批人的文化之根是個體主義。他們到美國去,剛好是歐洲強調自我的時候,所以美國的文化根源很強調自我,強調個體利益,強調追求物質。我們國內翻譯的一本書叫做《無快樂的經濟》,這是美國一個經濟學家在1976年寫的,他批評美國那種過度追求物質財富的文化,經濟發展了,但大家卻都不快樂。這事實上也成為美國今天金融危機發生的真正的價值根源。
很不幸,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主要吸收了美國的文化。中國要走向幸福社會,歐洲模式比較值得我們借鑒。
事實上,按照目前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已經完全能夠解決所有人豐衣足食的問題,只要我們從上到下切實轉變我們的發展理念,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完全能夠做到低增長,高閑暇,大部分人都會生活得非常幸福。總之,我希望上海的世博會成為一個幸福的世博會,成為中國確立幸福觀、處處體現以人為本的轉折點,不要過分追求表面化的奢華,一定要追求快樂的可持續性。
(作者為浙江財經大學教授。本文由本刊記者陳統奎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