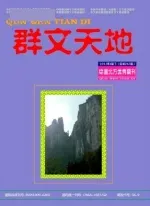“永恒的鄉愁”
肖連花
汪曾祺的研究者,一向不乏其人。可每次面對他的文字,總是為其中流淌出來的傳統氣息、古典韻味所吸引,更為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古典美學的津津樂道,不厭其煩的言說所折服。汪曾祺,這個看似平和而實則有著自己堅固操守的老頭,一直在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著樂此不疲的傳導,與堅定不移的守望。他有一副傳統江南文人特有的古典“神色”,對傳統江南文人的生命之“逸”進行追慕,對人生藝術的審美品格進行溯古。這一些關乎少時成長環境的耳濡目染,經前輩師長的循循教導和自己后來的成長蛻變。但汪曾祺作為一個當代中國文人,對于文藝品格的獨特選擇,總是聚焦于中國古典審美品格的自覺傳承和堅定守望。究其根源,我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考慮:民族文化的自覺認同、地域歸屬的追溯認同,以及性情氣質的鑒定認同。
汪曾祺總說:“我是一個中國人。”在他理解中,“中國人”是一個有著本民族文化傳統和歷史淵源的中國人。對于這樣一種身份的認同,汪曾祺始終充滿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他也說過,“祖國”很重要的成分是祖國的文化。沒有文化,就會像美國黑人那樣變成“懸空的人”,承受著沒有文化傳統、沒有歷史的悲哀。他認為,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化,是它的語言。他還指出,文學語言有味其實就是有文化。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標記。汪曾祺告訴我們,“一個人有祖國,有自己的民族,有文化傳統,不覺得這有什么。一旦沒有這些,你才會覺得這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貴”。他也指出,一個國家的文化思想也必定就會影響它的國民,中國人也必定深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而且,一個人不管走到哪里,也無法擺脫也不能脫離自己的本土文化。
汪曾祺認為自己就是一個深受傳統思想文化影響的人,在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中長大,從情感上接受儒家的思想,在精神人格上是“儒道互補”的、比較“皮實”的一個人。當遭遇“尋根”思潮,汪曾祺這樣理解“尋根”,他說:無非是說把現代創作和傳統文化接上頭,一方面既從現實生活取得源頭活水,另一方面又從傳統文化取得滋養。如果是這樣,我以為這是好的。一個中國作家應當對中國文化有廣博的知識和深刻的理解,他的作品應該閃耀出中國文化的光澤。否則中國的作品和外國人寫的作品有什么區別呢?
在中國現代化的巨大潮流中,在全世界存在著對中國文學不公正、偏見的環境中,汪曾祺有一些淡淡的哀愁,但是他除了憤慨地說“誰教我們是中國人”之外,他相信的仍是:文化可以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但是一種文化就是一種文化,沒有辦法和另外一種文化完全一樣。用他的話說:“我覺得一個民族和另一個民族無論如何不會是一回事。”對于民族身份及其文化認同的自然和自覺,汪曾祺一絲一毫也沒有改變。這是一種很深的民族情懷。難怪乎,有人說:“汪曾祺可謂是一個典型的漢文化中心地域中產生出來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汪曾祺的確是一個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著相當深刻的認同感的典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表現在文學上,他就說:“中國的當代文學含蘊著傳統文化,這才成為當代的中國文學。正如現代化中國里面有古代的中國。”對民族傳統文化深懷認同的汪曾祺,在文學上傳承著中國傳統的審美追求、美學理想,懷著一種執著而自信的感情。
其實,對于自我民族身份及其文化的認同,如果沒有一種認祖歸宗、地域歸屬的認同做心理基礎,那也就無從說起。汪曾祺當然不是這樣。在《皖南一到》中,他提到:歙縣是我的老家所在。在合肥,我曾戲稱我是“尋根”來了。我站在合肥歙縣的大街上,想,這是我的老家,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熱情。慎終追遠,是中國人抹不掉的一種心態。而且,也似無可厚非。
除此之外,早年外地求學,后來輾轉各地,在北京則生活了近五十年的汪曾祺經常回憶起的自己的家鄉——高郵:我的家鄉是一個水鄉,江蘇北部,運河旁邊一個不大的城市。他還一再聲明,“我的家鄉不只出咸雞蛋。我們還出過秦少游,出過散曲作家王磐,出過經學大師王念孫、王引之。”文風的確不可謂不盛。這種地域歸屬的情懷,正是汪曾祺對中國古典審美自覺傳承、堅定守望的另一個原因。在這樣一種地域身份歸屬的認同下,汪曾祺也始終有一種傳統江南文人的文化心態。江南是一個有著深厚中華文化底蘊以及強大民族文化規范力量的區域。特別是明清以來,經濟發達,澤被中華文明,深植民族傳統文化。汪曾祺的童年、少年生活就在江南的一個鄉間度過,年少時的他受到了傳統文化的種種教育和熏陶,其文化積淀在他的身上烙下來了。在這種文化積淀的影響下,汪曾祺獲得了最豐厚的傳統精神文化的滋養。他也始終以一個受到傳統文化滋養長大的江南文人自居,對傳統文化精神、古典文藝審美品格有一種天然的自覺性。汪曾祺堅持“高蹈古風”,經過江南文人多少個世紀磨洗的民族傳統文化、生命情趣、文藝審美品格在他身上自然而然地傳承了下來,成為了“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文人。
另外,汪曾祺對自己氣質、性情也有著清醒的認識。他不僅把自己歸為一個江南文人的范疇,更確信自己是一個只會寫“小橋流水”的小品作家、一個“調色盤里沒有顏色,只有墨”的畫者、一個追隨“疏朗清淡”的桐城古風的文人。他自認為有著“曾點”式的藝術人生追求,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人道主義者”,是一個平心靜氣、真誠可愛的人。汪曾祺鑒定和認同的這種淡泊平和、自然隨性的性情,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士大夫文人的“風骨”。正如他自己所說“文如其人”,文也應該如其人,他憑著自己的藝術感覺找到了一種真正適合自己的美學風格:含蓄淡雅、樸素自然、和諧。這也是汪曾祺在人生藝術形式上、審美理想追求中體現出中國“古風”的再一個原因。這也可以說是汪曾祺對于審美價值、民族精神文化的一種個人選擇和個性追求。他的個性偏于傳統古典的特征:仁愛瀟灑、寧靜自然、自適平和、樂天曠達。作為個人氣質的折射,汪曾祺自然認同這樣的民族文化形態,選擇了這樣的藝術情趣、審美品格。這其實可以說是他的的生命本色與民族特色相輝映而已。汪曾祺不愿意做,并也不是一個“文化守成主義者”。
綜上所述,汪曾祺作為一個對民族傳統文化有著深刻認同感,性情有著中國“古風”的江南文人,他的文藝思想中表現出他對民族傳統文化、中國古典審美品格的堅定守望就不言而喻了。這種“鄉愁”是汪曾祺表現出來的一種永恒的情結。推己及人,對僑居愛荷華二十多年的聶華苓,他就說:“我們是你的娘家人。”正如人所言,“他經歷著文化崩壞的歷史過程,以思鄉之作記錄著正在消亡的文化,以詩性的惆悵作了最后的回眸”。汪曾祺的這種守望,這種“鄉愁”有著人類普遍的價值。因為他表達了遠離自然的現代人共同的感受,對于精神家園的渴望。他這種永恒的“鄉愁”已經被不同文化的讀者接受,并且是真正地從鄉土走向了世界。對于中國、對于世界及其文化,這也正是汪曾祺的意義所在。
參考文獻
[1]汪曾祺著.汪曾祺全集[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2]胡河清著.靈地的緬懷·汪曾祺論[M].學林出版社,1994.
[3]汪曾祺精選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