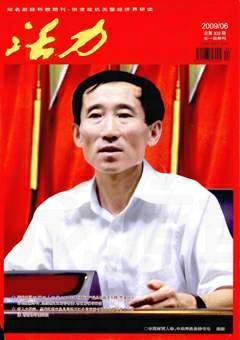淺談我國現行繼承制度中存在的缺陷
王 曦
我國現行繼承法采用的是限定繼承原則,又稱為有限責任繼承原則。其核心是限制繼承人對被繼承人債務的清償責任,即繼承人只需在繼承遺產的限度以內為被繼承人清償債務,不需以自己的財產對被繼承人的債務負責。這種制度符合現代社會家庭成員人格獨立、責任自負的理念,具有其積極的意義。但是它明顯是保護了被繼承人的利益,而忽視了被繼承人的債權人的利益。作為一種法律制度,必須對所涉及當事人的權利予以平等的保護,這是現代法律維護公平、正義精神的需要,也是評判法律之善、惡的標準之一。現行繼承法未給予繼承人和被繼承人的債權人的權益以平等的保護,是其存在嚴重的缺陷之一,其缺陷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沒有對接受和放棄繼承規定明確的期限,使得繼承關系長期不穩定
我國繼承法第二條規定:繼承從被繼承人死亡時開始。這意味著被繼承人死亡時,被繼承人的財產權利和義務就概括地轉歸繼承人,被繼承人的債權由繼承人享有,被繼承人的債權人只能向繼承人行使;債務由繼承人承擔。通常情況下繼承人不僅僅只有一個,這就需要在一個合理的期限使繼承關系確定下來,使被繼承人的所遺留下來的債權債務能得以盡快了結。然而,繼承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繼承開始后,繼承人放棄繼承的,應當在遺產處理前,作出放棄繼承的表示。沒有表示的,視為接受繼承。也就是說,繼承人的確定必須要到“遺產處理前”,在此之前繼承人實際上都不確定,繼承關系始終處于不穩定的狀態。此外繼承法沒有規定遺產處理的期限,使得這種不穩定的狀態有無限期存在的可能(現實中這種無限期狀態不乏事例)。這種不穩定狀態對繼承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都很不利。有的繼承人對遺產長期不聞不問,也不配合其他繼承人的管理或析產活動,使得遺產的管理或處分受到極大的影響。幾十年后,由于經濟變化等原因,遺產升值了,才出面主張繼承析產,遺產貶值了又糾纏其他繼承人。按照現行繼承法,他(她)的主張應予支持,但實際占有、管理的繼承人則認為繼承人長期對遺產不聞不問,應視為放棄繼承。因此這樣規定的弊端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中來看是明顯的:一是不利于遺產的管理和利用,有礙財產的利用和改良;二是繼承關系長期處于不確定狀態,遺產也難以確定,影響債權人行使權利;三是埋下繼承糾紛的隱患。
二、死者的債權人缺乏救濟手段,其利益難以得到保護
一個人死后,有兩個方面的財產關系需要處理,一是什么樣的人有權取得財產,以及在他們之間如何進行分配;二是死者的債權人的利益如何進行保護。現行繼承法對第一個方面的問題規定的較為清晰、完備、合理,對第二個問題則只有一個原則的規定,即第33條規定:繼承遺產應當清償被繼承人應當繳納的稅款與債務,但以繼承遺產的價值為限。因此在我國現行法律條件下,缺乏相應的制度來保障債權人的債權在債務人死亡后,其債權能得以順利實現。同時也缺乏制度來約束繼承人對債權人的欺詐。現實生活中,繼承人將遺產轉移、隱藏、揮霍、浪費,或者不善經營而導致毀損,或者擅自將遺產由于清償自己的債務等危及債權人利益的情況屢屢出現,債權人常常遭受嚴重損失。但是債權人除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62條規定的因遺產被分割而未清償債務而享有的追奪權外,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的權利救濟措施。這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交易的安全,破壞社會經濟秩序,敗壞社會道德風尚。法律在這種時候已經不應當保持沉默了。
三、不利于維護交易安全,妨礙物質資料的流通
按現行制度,遺產可以長期不予以分割。這樣,必定會產生兩個人、三個人甚至于許多人對同一個財產共有所有權,按共有制度的原則,在處分這些財產時需要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勢必影響財產的流通速度;更為嚴重的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約束,前列的共有常常處于產權登記長期維持于被繼承人死亡時的狀態,即只是法律上、事實上的共有,卻沒有予以登記公示(不動產及需要予以登記的其他財產),這必然會十分不利于交易安全的維護。
四、模糊了繼承關系和共有關系的界限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77條規定:“繼承開始以后,繼承人未明確表示放棄繼承的,視為接受繼承,遺產未分割的,即為共同共有。訴訟時效的中止、中斷、延長,均適用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這一規定不僅進一步暴露了現行繼承法存在的前面1、3個缺陷,而且模糊了繼承法律關系和共有法律關系的界限。共有是指兩個以上的人對同一項財產共同享有一個所有權的一種法律關系,即一物所有權同時為數人共同享有的法律狀態。共有的客體是特定的同一項財產。共有人對作為客體的財產享有的是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共有的內容包含對內、對外雙重權利義務關系,共有人無論對內或對外行使權利時,并非完全獨立,要受其他共有人利益的制約,須體現全體共有人的意志。繼承是規定將死者生前所有的個人財產和其他合法權益轉歸有權取得該項財產和權益的人所有的法律制度。繼承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我國《繼承法》第3條)。按我國現行《繼承法》的立法精神,《繼承法》是采用的概括繼承原則,即是對死者生前財產權利和義務的全面承受,接受遺產的繼承人,在接受遺產的同時,負有清償被繼承人生前所欠稅款和債務的義務。對比兩者的客體,可以明確看出其區別:共有的客體是財產所有權,是一種對世權,不包括義務,而我國的繼承權不僅包括權利,還包括義務。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49條規定;“繼承人放棄繼承的意思表示,應當在繼承開始后、遺產分割前作出。”第51條規定:“放棄繼承的效力,追溯到繼承開始的時間。”即,在遺產分割前,繼承人放棄繼承可以不受其他繼承人的限制,是繼承人享有的一種單方權利,不須承擔義務。這以共有關系中共有人對內對外雙重權利義務關系,受其他共有人的制約、體現全體共有人的意志有著巨大的不同。這種模糊帶來的不僅是理論的混亂,而且使繼承糾紛人為地增加。
綜上所述,隨著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人們不斷日益增長的物質財富的需求,如果相關的配套法律不能適應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那么勢必會對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轉起不到促進作用。作為一個執法者來說,在實際執行法律的時候,操作起來就很難,也不能做到以人為本,不能以科學的發展的手段去處理法律上的問題。所以筆者認為,我國法律界的研究學者應該根據現今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和人文道德思想,重新修改我國的繼承法律制度并大膽吸收先進國家的先進法律制度,取別國之長,補己之短,使我國的繼承制度既適合我國的國情也能與國際接軌,為我國社會經濟建設提供更有利的服務,為能最大的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提供最有效的法律保障。(編輯/穆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