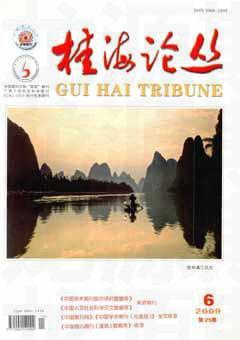20世紀30年代何干之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問題的理論探索
楊舒眉 崔中華
摘要:20 世紀30 年代,何干之立足中國內部、結合中國民主革命實踐,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不同的視角以及它們間的相互關系出發,對中國的社會性質、革命性質、革命動力、革命發展前途等重大的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提出了精辟的見解,對中共制定新的革命政策和策略,形成科學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其理論研究凸顯出強烈的現實關懷精神和民族意識、濃郁的意識形態話語色彩等特征。
關鍵詞:何干之;新民主主義;中國社會性質;新民主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09)06-0104-05
一
何干之(1906-1969) 是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歷史學家和教育家。20 世紀30 年代是何干之一生中理論著述最豐碩的時期,先后出版了《中國經濟讀本》、《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后易名為《轉變期的中國》)、《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等著作。他對中國社會性質、革命性質、革命動力、革命發展階段等新民主主義革命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理論探索,提出了精辟的見解,作出了科學的論斷,為中共制訂新的革命政策和策略,形成科學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奠定了他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研究史中的重要地位。
20 世紀30 年代,中國社會急劇動蕩,政治格局不斷變化,何干之秉承儒家的“入世”精神,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現實關懷,積極探索國家富強、民族獨立的雙重時代主題。這一時期他的學術研究和理論探索呈現以下三個特點:1. 強烈的現實關懷精神和民族意識,以探索民族的歷史命運為歸宿。他研究和探討的中國社會性質、中國革命性質、社會史問題、中國農村經濟性質等重要命題,既是關于中國社會和革命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又是中國共產黨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同時也是探索中國未來發展前途的重大課題。他的學術研究著眼于中國實際,服務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因而他將新民主主義革命視為中國革命道路的正確選擇。他注重從“今天”的角度分析和解決問題。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一書中特地加上“國防經濟”一章,專論這個“今天”的課題。2. 濃郁的意識形態話語色彩,奉唯物史觀為圭臬。他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中國革命實踐提出的種種問題,以唯物史觀構筑其學術理論體系,因而他的學術研究和理論闡述完全納入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中。他以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階級”、“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生產方式”、“封建社會”、“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亞細亞生產方式”等話語和范疇來研究、分析和注解中國社會和革命中的諸種問題。3. 由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入手,研究中國革命理論問題。他關于革命問題的理論探索牢牢建立在對中國社會經濟狀況和經濟水準的客觀估計的堅實基石之上。德國學者羅梅君指出,“何干之的早期著作主要是關于歷史的。但他本人自稱是經濟學家,因此他十分重視政治經濟學問題。”[1]18“在一般的歷史著作中,何干之總是賦予由政治經濟學決定的社會史觀以優先權”[1]43。
二
20 世紀30 年代何干之積極參加了思想文化界關于中國社會和革命諸問題的探討,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理論成就:
(一) 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選擇
何干之從過去、現在和未來相統一的宏闊視角出發,科學地把握了中國近代以來社會的變遷,劃分了社會發展的階段,指明了民族和社會解放的方向和路徑,向彷徨中的中國人民就“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問題做了科學有效的解答——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革命道路的必然選擇。鴉片戰爭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地位,20 世紀30 年代學者們取得了共識。何干之認為鴉片戰爭是“新舊中國的轉折點”,是八九十年來中國社會一切動亂和變遷的出發點,此后依次相繼、環環相扣的洋務運動、戊戌新政、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推動了中國社會的不斷地發展和進步。但歷次社會變動在路徑選擇上和社會推動力量上存在著較大差別,歸納起來主要有兩種——自上而下的改革或改良和自下而上的革命,據此把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歷史發展也劃分為這樣兩個階段。鴉片戰爭失敗的后果之一是中國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在平定內亂之后,封建統治階級在19 世紀60—90 年代發動了一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但“自強”、“求富”之夢被甲午戰爭所粉碎,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口號的戊戌維新乘勢登上歷史舞臺,進行體制內的政治改革,僅僅百天即宣告失敗。自下而上的義和團運動失敗后,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何干之進而指出,辛亥革命由于思想相對滯后而變成了不倫不類的“反正”,五四運動啟蒙運動的缺陷使得先進的中國人認識到喚起下層民眾,以求得民族和社會的雙重解放。可以看出,在社會發展的路徑選擇上,何干之把改革(或改良) 和革命作為劃分社會發展階段的標準,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新政屬前一階段,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屬后一階段;在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上,自上而下的改革(改良) 階段以上層統治階級為主體,自下而上的革命階段以下層民眾為主體。他對上層統治階級的改革或改良否定多于肯定,認為總會歸于失敗;對下層民眾的暴力革命持肯定態度,認為是推進中國發展和進步的根本路徑。中國社會的變遷和發展表明,中國社會的發展正是在自上而下的以上層階級為載體的改革(改良) 受挫失敗后,邁入自下而上的以下層民眾為載體的革命階段。正是遵循這一邏輯,何干之把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視為近代以來一系列變革、奮斗、追求與探索的繼續,視為中國經歷了一系列失敗后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道路的必然選擇。歷史證明:中國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掃清了障礙而邁入嶄新的階段。只要我們認識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也就認識到何干之所探討的中國革命道路及其選擇問題的重要學術價值。
(二) 關于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性質
中國的社會性質問題是在中外比較中產生的20世紀新問題,也是中國革命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毛澤東認為,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性質“是解決中國一切革命問題的最基本的根據”[2]。20 年代末至30 年代下半葉,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展開了關于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這場論戰包括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中國社會史問題、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問題三個方面,何干之說:“社會史,社會性質,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可說是關于一個問題的多方面的探討。”[3]186這三個方面與中國革命進程緊密銜接,因而使論戰呈現出鮮明的為現實斗爭和革命服
務的政治訴求色彩,如何干之所說,這場論戰不是“書癡子的玩意兒”,而是“實踐上的緊急要求”,因為只有“認識了中國社會,才配談改造中國社會”。何干之作為“新思潮派”中的一員,積極參與了這場論戰,和潘東周、王學文、劉蘇華等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一道批判了以陶希圣、李季為代表的“新生命派”的“先資本主義社會”論,以嚴靈峰、任曙、劉仁靜為代表的“動力派”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論,以及陳獨秀的“封建殘余”論,以及李立三的“商人統治社會”論等,科學地論證和總結出中國社會性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了解中國社會的經濟性質是認識中國社會性質的關鍵。何干之認為“不單是歷史上未解決的理論問題,同時又是目前實踐上的緊急問題”[3]128,“其主要問題是:應當把中國社會的方位定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或一般的世界歷史進程的那一點上?現階段的中國社會性質是封建的還是資本主義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1]72 他從剖析近代中國經濟狀況及其性質、揭示中國革命的現狀和前途,以及總結十年論戰的歷史等方面,對近代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根本特點作了深入的闡發。
經濟是政治理論的測量器,通過分析經濟關系來研究各種社會政治關系是一條捷徑。1934 年,在何干之最早參加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著作《中國經濟讀本》中,確立了要“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這個主題為經”的宗旨,并“以真實的材料為緯,使理論與實際縱橫交錯把中國經濟的真相和盤托出”[4]。他從翔實的經濟資料入手,緊緊抓住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三者在中國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進行分析,精辟地指出“中國問題的癥結在于對帝國主義、民族資本和封建勢力那三種社會勢力的相互關系的了解”,“對于這三種社會勢力的了解,可以歸納為兩點:(一) 帝國主義對封建勢力究竟發生了什么影響,是破壞它還是維護它?(二) 帝國主義對民族資本是阻滯它還是推進它?是打擊它還是幫助它?”[5]92-93他總結出中國經濟的三大特點:“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死路一條的民族資本”。“半殖民地性”關系到如何看待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半封建性”關系到如何認識封建制度沒落的程度,“死路一條的民族資本”則明確地表示了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中國民族資本沒有發展的空間。他說,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已經“不是封建社會,因為封建制度已經瓦解了,只有封建勢力卻還存在;也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因為雖有資本主義的要素,但不能占領導的地位。在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勢力在社會經濟中又居著左右全局的作用,中國的政治機構,只有半獨立的性質”。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已經“由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期,但這個過渡期,因為有民族的與國內舊制的壓迫,卻非常艱苦,應死的不急死去,應長的卻很難生長”,因此,此時的中國社會正處于“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會”階段[5]144。但是何干之此時沒有將“半殖民地半封建”看作一個完整概念,沒有就二者的結合及統一性展開論述。[6] 《中國經濟讀本》的第二章為“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地性”,第三章為“中國經濟的半封建性”,如此分別論述,使他對中國社會性質做整體概括時,說中國是“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會”。1936 年在《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明確地提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觀點,中國現階段革命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的民主革命”,這標志著“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在他那里已經形成。1937 年在所出版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中,他關于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觀點愈加明確,直接用以作為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概括。
(三) 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動力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務是反帝反封,如何實現這一任務,依靠的社會力量來自哪里?首先,何干之結合具體國情,指出中國民主革命有自己的特點,有“時代的新內容”,與法國、普魯士等歐美國家,土耳其等亞洲國家的民主革命相比,是“新的民主革命”,在世界上是沒有的。中國革命的擔當者和執行者不是上層資產階級,而是下層的民主主義者。其次,何干之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對當時國內外各種政治力量的立場和態勢作了深入分析。敵對的一方,首先是帝國主義,其次是在其庇護下的國內封建勢力,二者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對象;“工人和農民,是解放運動中的基本力量”,工人是處于領導地位的階級,“是民族革命的組織者”,也是中國民主革命中革命最堅決、最徹底的階級,工人聯合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處在中間的,是最富于妥協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和改良主義者,以及總在動搖悲觀和害怕的小資產階級。市民階層“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前進”,此外,下層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則是“革命的忠實同盟者”[7]. 177。
隨著日本侵華戰爭逐步升級,民族危機、民族矛盾日益嚴重,何干之寫了一系列評論中日戰爭的文章,如《中國的資源問題》、《中國的財政問題》、《中國的軍備問題》、《中國的國際關系》,闡述中日戰爭中建立“全民族大聯合的抗敵戰線”的重要性。在“大聯合”狀態下,內部矛盾應暫時緩和,不兩立的態度不利于中國當前的情勢,因此在中國已由“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轉為日本的全殖民地”的時刻,全國各個階層,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富農,乃至地主、軍閥、敵人以外的買辦,都是可以爭取的對象,只有“上層和下層人民都漸漸站在統一戰線上”,從而有可能結成廣泛的“抗敵統一戰線”。不僅如此,政黨之間也應改變相互間的關系,聯合抗日、共同抵御外侮。他批評了幾種反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左”傾關門主義。
(四) 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
對中國社會經濟性質、階級狀況做了深入分析后,何干之獨創性地提出了“新的民主革命”的觀點,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的階段和前途做了系統闡述,這集中反映在他于1936 年11 月出版的《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書中。他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矛盾和階級關系,指出中國革命與歐美各國的差異,論證了中國不會走西歐民主革命后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而是有自己的特點,中國的特殊環境是“不容許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的天堂”[7]166,中國的革命將“不通過資本主義而和平地轉入社會主義階段”。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是普通的民主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的民主革命”,進而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分兩個步驟進行。“先來第一著,再來第二著”,“在第一著中就準備著解決第二著的前提”[7]165。第一著即民主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第一著”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是工人階級,革命的主體是工農民眾,革命政權是“工農民主主義”。第二著即在完成民主革命的同時,同時解決社會問題,即實行社會主義,這就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的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何干之關于如何
建設社會主義也有了朦朧的規劃,他認為民主政治和農業改革是中國工業化的前提,處理好向社會主義過渡與發展資本主義的關系是進行新的工業經濟建設的關鍵。由此可以看出,他關于中國革命發展前途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出中國革命發展的態勢,又反映出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問題探索的歷史足跡。
三
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并取得勝利的基本革命理論,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的產物,是一套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革命問題的完整的理論體系。在新民主主義理論形成過程中,就其思想和文化的來源而來,既有域外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也有本土的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果,還有這一時期思想文化領域取得的積極成果。20 世紀30 年代何干之關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一系列問題的理論研究和探索,為中國共產黨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比較典型的是他的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現階段革命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的民主革命”的正確觀點,直接為毛澤東所吸納。1936 年何干之正式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而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理論中有關“半殖民地半封建”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加以表述的,則是1938 年11 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報告。1939 年10月4 日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明確地稱“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而體現這一概念經典表述的,則是1939 年12 月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1940 年1 月的《新民主主義論》。何干之關于中國革命動力、革命發展前途、革命的雙重任務等理論觀點,與毛澤東的觀點不謀而合,在之后形成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中得到系統的闡發和理論升華。他的理論貢獻得到當今學術界的認可與充分肯定。如王思瑞在《新民主主義的由來和歷史命運——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三次思想交鋒》中指出:“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第一次論戰,對陣雙方的主將是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托派認為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1928 年中共六大確認‘中國現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現在的中國經濟政治制度,的確應當規定為半封建制度。這實際是斯大林派的觀點。后來,斯大林派的觀點被毛澤東、劉少奇、何干之等創造性地正確地改造為新民主主義理論后,在20 世紀40 年代獲得巨大成功。1936 年11月,何干之在《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采用了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說法,并提出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新的民主革命。毛澤東1940 年1 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時吸納了何干之的上述正確觀點”。[8]李洪巖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論的來龍去脈》,指出:何干之正式提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現階段革命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的民主革命”的觀點,客觀上為新思潮派的工作做了圓滿的收尾。何干之1937 年秋到延安,毛澤東曾有意請他做秘書,故一般認為,何干之的研究對毛澤東發生過直接影響。”[6]何干之關于社會性質的科學把握,“在中國共產黨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過程中,起著有益的探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