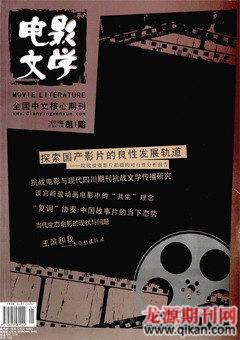電影《立春》縱橫談
許海燕
[摘要]電影《立春》是顧長衛(wèi)導(dǎo)演的第二部作品,該片入圍第二屆羅馬國際電影節(jié)競賽單元,女主演蔣雯麗獲電影節(jié)最佳女演員獎。顧長衛(wèi)與張藝謀,同為西安人,又曾是北京電影學(xué)院攝影系的同班同學(xué)。相似的經(jīng)歷,反映在各自的電影作品中又各有各的精彩。正是通過顧長衛(wèi)與張藝謀作品的橫向比較,我們對《立春》的人物性格塑造和影片黃色基調(diào)有了更深的體悟。在對顧長衛(wèi)自己的西部作品《孔雀》、《立春》的縱向比較中,既看到了其中的共同之處,也驚喜地發(fā)現(xiàn)顧長衛(wèi)個(gè)人風(fēng)格的日漸成熟。
[關(guān)鍵詞]《立春》;張藝謀;《孔雀》;個(gè)人風(fēng)格
《立春》是顧長衛(wèi)擔(dān)任導(dǎo)演的第二部作品,之前該片作為唯一華語電影入圍第二屆羅馬國際電影節(jié)競賽單元,影片女主演蔣雯麗同時(shí)獲電影節(jié)最佳女演員獎。顧長衛(wèi)2005年執(zhí)導(dǎo)處女作《孔雀》,受到業(yè)內(nèi)外人士的廣泛關(guān)注與熱捧,并獲得第55屆柏林電影節(jié)評委會大獎銀熊獎。顧長衛(wèi)導(dǎo)演的《立春》、《孔雀》,劇本同出自編劇李檣之手,同樣講述底層小人物為夢想而歷經(jīng)苦難的故事,也都在國際電影節(jié)上載譽(yù)而歸,人們難免將兩者拿來比較。顧長衛(wèi)和張藝謀,他們同為西安人,且是北京電影學(xué)院攝影系同班同學(xué),他們的從業(yè)經(jīng)歷也很相似,先后由攝影師轉(zhuǎn)為專職導(dǎo)演。他們導(dǎo)演的首部作品《孔雀》、《紅高粱》,也即他們的成名作,皆受到柏林電影節(jié)的青睞。種種相似處使人們不油然地把他倆相提并論。解讀電影《立春》,把它放到與《孔雀》的縱向比較,及與張藝謀電影作品的橫向觀照中,也許能夠有較新鮮的發(fā)現(xiàn)。
《孔雀》、《立春》是顧長衛(wèi)“時(shí)代三部曲”系列電影的前兩部,探究兩者間的諸多同與異有助于深入理解顧長衛(wèi)的導(dǎo)演風(fēng)格。作為一位擁有國際知名度的優(yōu)秀攝影師,顧長衛(wèi)的攝影技藝得到普遍贊賞。但電影畫面主要傳達(dá)的是導(dǎo)演對影片的理解,攝影必須服從于導(dǎo)演的總體構(gòu)思,因而留給顧長衛(wèi)個(gè)人發(fā)揮的空間相當(dāng)有限。只有在顧長衛(wèi)執(zhí)導(dǎo)的《孔雀》、《立春》里,可以展現(xiàn)他極強(qiáng)的場面調(diào)度能力,并形成了屬于顧長衛(wèi)個(gè)人的風(fēng)格,這一風(fēng)格在《孔雀》中初露端倪,延續(xù)到《立春》里并被強(qiáng)化、固定下來。張藝謀電影熱衷于使用大紅大綠的鮮亮色彩對觀眾進(jìn)行視覺“轟炸”,顧長衛(wèi)電影畫面卻經(jīng)過特別的“做舊”處理,藍(lán)、灰、黑等深色系是銀幕的顏色基調(diào),觀看顧長衛(wèi)的電影,恰如打開一本年代久遠(yuǎn)、顏色褪盡的陳年相冊。記憶深處的件件往事、幕幕畫面都被重新翻撿出來,不由得令人欷歔、讓人感慨、催人淚下。一種既溫暖貼心又悲涼凄愴的復(fù)雜情緒在人們心底糾纏久難平復(fù)。
《孔雀》的顏色主調(diào)是藍(lán)色,這與二十世紀(jì)七十年代的故事發(fā)生背景相吻合,藍(lán)色正是那個(gè)時(shí)代的主流色。影片中的各色人物出場一律以深藍(lán)色服裝為主,這使導(dǎo)演輕而易舉地營造出典型的時(shí)代氛圍,藍(lán)色又是一種憂郁、壓抑的冷色調(diào),顧長衛(wèi)由此暗示出小人物的熱切追求只能以失敗告終。《立春》以深灰、黑的冷硬色為影片主調(diào),這與《孔雀》的情緒保持了一致,但對色彩的使用更見導(dǎo)演本人功力。“立春”位居二十四節(jié)氣之首,宣示了萬物復(fù)蘇的春季正式開始。然而,桃紅柳綠的春天還遠(yuǎn)未到來,尤其在遙遠(yuǎn)北方的閉塞小城里,“立春”時(shí)節(jié)滿眼還是暮冬的景色,雖然希望的種子已經(jīng)在某些年輕人的心中萌芽,人們?nèi)员唤d在幽暗蒙昧的世俗生活中。這就是顧長衛(wèi)以“立春”為片名,卻又執(zhí)著于在畫面上偏愛深色的緣故。
《立春》中黃色的運(yùn)用可謂是導(dǎo)演的“神來之筆”,黃色的數(shù)次出現(xiàn)對應(yīng)著女主角王彩玲命運(yùn)的幾起幾伏。王彩玲首次出場穿著一件明黃色毛衣。盡管王彩玲長得不漂亮,但毛衣襯托出她蓬勃的生命朝氣和女性的溫柔品質(zhì),引來周瑜一見傾心。如果王彩玲和周瑜能“老老實(shí)實(shí)過日子”,她也許能有一份平淡的幸福,不會遭遇后來的波折,但她決然地放棄了這個(gè)機(jī)會,王彩玲留宿黃四寶的第二天清早,戴了一條嫩黃色絲巾。這時(shí)的王彩玲正值人生的高潮期,愛情與藝術(shù)的夢想似乎都將唾手可得,嫩黃絲巾是王彩玲“蠢蠢欲動”青春激情的象征。嫩黃是脆弱的色彩,王彩玲的幻夢只持續(xù)了一個(gè)早晨,黃四寶的打罵徹底摧毀了所有美夢,高蓓蓓身著橘黃色高領(lǐng)衣,婚介所阿姨穿著棕黃色上衣外套,她們本來有機(jī)會給王彩玲的生命注入新的希望,最終卻被證實(shí)都是精心策劃的謊言與陷阱,她們是把王彩玲推向俗世的兩股重要力量。王彩玲床頭燈射出的黃色柔光,不時(shí)為四處碰壁的王彩玲帶來心靈的慰藉,可和無邊無際的灰暗相較,這點(diǎn)溫暖又是那么渺小。《立春》的黃色只是“靈光閃現(xiàn)”的幾個(gè)瞬間,短暫的出現(xiàn)后很快就會被灰色吞沒。幾經(jīng)沉浮后王彩玲不再相信夢想。她回歸了庸常的世俗生活軌道。正如王彩玲所說,“每年的春天一來……我心里總是蠢蠢欲動,可等春天整個(gè)都過去了,根本什么也沒發(fā)生……”黃色只是王彩玲生活的異常狀態(tài),灰黑色才是她的宿命,她“在劫難逃”。
顧長衛(wèi)《孔雀》、《立春》的燈光使用精細(xì)、考究,通過光線明暗區(qū)域的對照,重要布景的外形被清晰勾勒出來。窗戶、房門、窄巷、欄桿、廊柱、臺階、墻洞、鏡子、電視機(jī)等成了電影構(gòu)圖里最主要的布景:棱角分明的長方形、正方形或菱形的窗框、房門、墻洞、鏡子、電視機(jī),將空間切割成條條塊塊的冰冷的鐵柵欄,筆直延伸至場景最深處的長長、憋促的陋巷;層層升高的數(shù)百級水泥臺階。導(dǎo)演迷戀于展現(xiàn)這些水平的、傾斜的、垂直的線條,以及線條構(gòu)成的四四方方的塊狀平面體。它們在向觀眾喻示著一個(gè)秩序井然、有條不紊、四平八穩(wěn)的理性世界。在這個(gè)充滿條條框框、清規(guī)戒律的世界里,對待那些大膽質(zhì)疑俗世生存法則的反叛者,卻是冷漠無情地打壓和不遺余力地扼殺。《孔雀》中姐姐的“空軍夢”、弟弟的青春沖動;《立春》中王彩玲“唱到巴黎歌劇院去”的夢想、黃四寶“考取北京美術(shù)學(xué)院”的追求、胡金泉對芭蕾舞十幾年的癡迷和“懸案”一樣的性取向;他們的夢想與堅(jiān)守各異,但共同構(gòu)成了對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巨大沖擊,因而他們也就招致世俗社會“不能承受”的重壓。導(dǎo)演通過強(qiáng)化構(gòu)圖中的線條元素,突出了環(huán)境對人們身心造成巨大壓力的主題。如果這個(gè)意圖在《孔雀》中尚屬自發(fā),那在《立春》里卻全然是有意而為。《立春》幾乎每個(gè)鏡頭、畫面中都出現(xiàn)窗子、門框、鏡子等布景,從而觸目驚心地呈現(xiàn)出世俗社會的陳規(guī)陋習(xí)對個(gè)人生活的嚴(yán)重侵襲,它們成為扼殺青春、夢想、激情的頭號罪魁禍?zhǔn)住?/p>
《立春》中“鏡子”的功能被發(fā)揮到極致,在《孔雀》中顧長衛(wèi)仍未發(fā)掘“鏡子”的意象。鏡子能夠準(zhǔn)確呈現(xiàn)事物,借助鏡子可以使銀幕畫面容量和空間得到擴(kuò)充、豐富。小張老師發(fā)現(xiàn)老公攜款潛逃,來找王彩玲哭訴的場面中,小張老師背對鏡子而坐,王彩玲面對鏡子包餃子。攝影機(jī)對準(zhǔn)小張老師,通過鏡子可以同時(shí)看到王彩玲的即時(shí)表情動作。鏡子的使用,能夠最經(jīng)濟(jì)地在一個(gè)鏡頭里從容不迫地完整表現(xiàn)了兩個(gè)人物,顧長衛(wèi)導(dǎo)演的“鏡子”也被賦予了象征含義。鏡中物象與實(shí)際物體有著本質(zhì)區(qū)別,它只是光線反射產(chǎn)生的幻影。注定是一種不現(xiàn)實(shí)的、虛假的幻象,鏡子和藝術(shù)、夢想有著某種契合,面對它們?nèi)藗?/p>
找到一個(gè)完美的超我,可過于依賴、沉迷它們,現(xiàn)實(shí)的自我形象就會發(fā)生變形,甚至再也無法找到自我。王彩玲和胡金泉,兩入迷戀于藝術(shù)理想,始終游離在現(xiàn)實(shí)與鏡象的亦幻亦真的世界里:王彩玲面對鏡子投入地邊彈邊唱《為藝術(shù)為愛情》詠嘆調(diào),胡金泉忘情地在大鏡子前跳扇子舞、芭蕾舞。鏡子容易破碎,破損鏡子里的形象是變形、丑陋的。王彩玲輔導(dǎo)高蓓蓓唱歌劇,在劃破的鏡子里王彩玲和高蓓蓓的形象扭曲而不真實(shí),這預(yù)示著高蓓蓓事件是一樁徹頭徹尾的騙局,而鏡中人都扮演了丑角。胡金泉故意猥褻了一名婦女,當(dāng)他再次走到大鏡子前跳起芭蕾舞,他的臉、身體在鏡子接縫處有了微微的變形,這其實(shí)是他心靈扭曲的一種外在表現(xiàn)。
《立春》、《孔雀》塑造了一群執(zhí)著于夢想的小人物,雖然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最終不得不向現(xiàn)實(shí)屈服,但他們的形象仍極富人性的光彩。具“偏執(zhí)”性格的人物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張藝謀導(dǎo)演的電影中,但張藝謀、顧長衛(wèi)電影的人物之間卻有著實(shí)質(zhì)性差別。在張藝謀電影的人物譜系中,無論是魏敏芝實(shí)踐“一個(gè)都不能少”的諾言,還是秋菊堅(jiān)持“要個(gè)說法”而不停告狀,以及楊天青、高田等人物,他們一旦決定去實(shí)踐某種想法或某件事,就會毫不猶豫地施行,人物的固執(zhí)己見必然與社會、他人發(fā)生尖銳沖突,但這類人物絕不遲疑、勇往直前。他們內(nèi)心沒有困惑,只需全身心對付來自外界的阻力。張藝謀電影人物性格是扁平的,而顧長衛(wèi)電影塑造出復(fù)雜、立體的“圓形”人物。《立春》女主角王彩玲,她對藝術(shù)、愛情的高遠(yuǎn)理想確實(shí)和平庸生活形成一對深刻的矛盾,但這種沖突只是“無形之陣”。除被小張老師婉轉(zhuǎn)諷刺為“心理陰暗”,王彩玲并沒有與周圍的人發(fā)生實(shí)質(zhì)性對抗,她的沖突來自內(nèi)心。一方面她堅(jiān)持忠于自己的夢想,并為理想在腳踏實(shí)地奮斗著,另一方面她心知肚明夢想遙不可及。她“一貧如洗。又不好看,老天爺就給了我一副好嗓子,除了這,就是個(gè)廢物”,她并不是“與世俗水火不容”,她“不是神”,王彩玲能夠清楚地看到現(xiàn)實(shí)與夢想間不可逾越的距離,她的痛苦在于始終徘徊在兩者之間,找不到調(diào)和彼此的方法。一個(gè)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不會痛苦,一個(gè)徹底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者會自甘沉淪,王彩玲兩者都不是,她游離搖擺著,所以她擁有了超平常人的苦痛。《立春》中王彩玲的兩難局面也在胡金泉、黃四寶、周瑜的身上存在,但他們四個(gè)人做出了不同抉擇。王彩玲回避平庸的夫妻生活,通過抱養(yǎng)殘疾女孩小凡,用母性之光照亮未來長路,胡金泉自投監(jiān)獄,為自己贏得狹小私人空間;黃四寶成為徹底的懷疑主義者,沉淪于自欺欺人的世界不能自拔。周瑜心甘情愿過起平淡的家庭生活。張藝謀電影人物的結(jié)局只有兩種,成功或失敗,生存或毀滅。顧長衛(wèi)電影的人物性格是多層次的,這為他們帶來了各種各樣的不可預(yù)測的命運(yùn),讓觀眾體味到人生的諸種可能性。
從《孔雀》到《立春》,顧長衛(wèi)電影的個(gè)人風(fēng)格已漸形成。顧長衛(wèi)一直堅(jiān)持稱自己拍攝的是商業(yè)片,但不可否認(rèn)。兩片的票房收入并不盡如人意。顧長衛(wèi)在今后的導(dǎo)演生涯里,如何拍出既為評論界首肯又有高票房的電影,在商業(yè)片與文藝片中尋找到某種平衡,這將是一個(gè)很大的課題。《孔雀》、《立春》顯示了顧長衛(wèi)不可小覷的導(dǎo)演實(shí)力,他為中國電影界貢獻(xiàn)了迥異于張藝謀的另類風(fēng)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