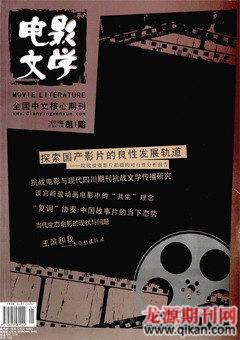尋找失落的自我
彭應擁
[摘要]用弗洛伊德的人格構成理論,解讀兒童影片《寶葫蘆的秘密》,影片中的寶葫蘆和宇航員分別是主人公王葆人格結構中“本我”和“超我”的象征,該片正是通過“本我”與“超我”的沖突,展現主人公尋找自我的歷程。這也是電影文本與童話文本在主題方面的重要差異所在。
[關鍵詞]《寶葫蘆的秘密》;自我;本我;超我
在2007年的中國電影市場中,《寶葫蘆的秘密》無疑是最閃亮的兒童影片。張天翼的同名童話誕生于近半個世紀之前,改編影片在原作基本的故事框架中,融入了許多具有時代精神的新元素,使觀眾在重溫經典的同時,亦產生了對當代生活的新思考,而這些思考仍以寶葫蘆的秘密為出發點。
寶葫蘆的秘密是什么呢?不論在童話還是在電影中,寶葫蘆都要求王葆把它的存在作為秘密加以保守,否則它就會失靈。這就是表象上的寶葫蘆的秘密。那么,這個秘密又有什么深層的意味呢?關于這一問題,童話和電影的答案是迥然不同的。
原作與改編劇本在情節方面存在一個顯著差異,那就是對秘密的處理方式——即寶葫蘆的結局——不同:原作結尾,王葆說出了秘密,于是寶葫蘆成了一個普通的葫蘆,王葆又回復為正常可愛的孩子,而電影中的王葆在歷盡挫折后仍保守著秘密,結尾處,寶葫蘆打算云游四方、繼續修煉,出發前它與王葆約定要一起為未來努力。很明顯,童話和電影對“秘密”真正含義的理解是有所差別的,這也直接導致了二者主題的差異,童話文本講述的是一個懶散少年吃盡苦頭之后改正缺點的故事,說出葫蘆存在的秘密也就意味著擺脫了不良念頭對心靈的制約。而電影文本力圖講述的是一個迷惘的男孩尋找和確立自我的故事,保守秘密實際上顯示了在成長歷程中對自我意志與尊嚴的發現和守護。
影片中的王葆盡管保留了原作主人公不愛動腦筋、費力氣的懶惰特征,但從更深一層看,他是一個對自我才能沒有清晰認知、對自我發展缺乏明確思考的少年。影片開場處,王葆夢見自己作為宇航員英勇營救身陷險境的太空站工作者。這一情節說明,像許多孩子一樣,他也擁有一個幻想世界中的英雄夢。然而另一方面,他卻不知道該如何在現實世界中書寫屬于自己的傳奇,所以,他可以眉飛色舞地談論自己的偉大夢想,可一旦被問及功課,他頓時啞口無言。王葆并不認為現時的學業與未來的夢想之間存在任何關聯,也沒有意識到每一分努力都能拉近自己與理想之間的距離,在內心深處,他似乎隱約地期盼著未來的某一天,光榮與夢想能夠突然降臨——不用付出太多努力,也不用經歷太多挫折。這樣的景況使他一方面對自身的才能沒有足夠的認識,另一方面也使他不可能從實際出發確定努力的方向。所以,這位了不起的空想家只能寄望于一個神通廣大的寶葫蘆實現他的超人夢。
然而,具備神奇能力的寶葫蘆真的能完成這偉大的使命嗎?
影片中,可愛的寶葫蘆果真盡忠職守地滿足王葆的一切要求,但結果卻總是弄巧成拙。金魚事件、機器人事件、游泳事件,都是王葆在同學們面前展示他“超人才能”的絕好時機,葫蘆的幫助也的確令他贏得了同學們的贊揚,但短暫的掌聲過后卻總出現對其能力的更長久質疑。所以考試作弊被發現后,王葆才會惱羞成怒地譴責葫蘆,“你害我吃棋子,你讓我在同學面前出丑,你給我偷書,還偷蘇鳴鳳的答案,大家以為我是小偷,現在連劉老師都不相信我了”。寶葫蘆的唯命是從不但沒能為王葆收獲一個眾人仰慕的英雄形象,反倒使他出盡洋相,嘗盡苦頭、屢屢陷入難堪的境地,那么,這個被寄予厚望的、傳說中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寶葫蘆,在現實中為何如此不濟呢?
影片中有一段非常耐人尋味的臺詞,當王葆把考試作弊的責任推給葫蘆并譴責它是妖怪時,葫蘆委屈又激憤地辯白“你說我是妖怪?是你自己心里想歪了,我才去那么做的,主人,我就是你心里的欲望,你怎么想我就怎么做,為什么是我的錯呢?”這段話實際上道出了影片中寶葫蘆與王葆之間的真正關系。盡管寶葫蘆有呼風喚雨的本領,但它的神奇能力始終被王葆的個人意愿所左右,它的所有作為都顯現了王葆的不合理欲望。因此,從這個層面上,我們可以認為,寶葫蘆與王葆實為一而二、二而一的形象,葫蘆正是王葆內心中不夠好第二自我的外化。
這個不夠好的第二自我,又可借用弗洛伊德的人格構成理論加以解讀,弗洛伊德將人格結構分為本我、自我與超我三個層面,遵循“快樂原則”的本我與遵循“道德原則”的超我之間存在激烈沖突,而自我則憑“現實原則”在兩者之間不斷進行調節,從而保證人精神的平衡。
寶葫蘆作為王葆內心欲望的象征,更近似于人格結構中的“本我”部分:沒有腦子,完全按照本能和“快樂原則”行事,缺乏是非善惡觀念。所以我們看到,影片中為數不多的未惹麻煩的靈通——如滿足王葆的口腹之欲和翱翔天際的愿望——都與人類的生存本能與原始的生命沖動有關。然而一旦涉及社會性問題,單純憑王葆內心欲望行事的寶葫蘆就會使主人陷入困境(如偷書和作弊)。
除“本我”之外,王葆人格結構中的“超我”成分亦非常明顯。他期望在學業上名列前茅、在興趣愛好方面出人頭地,期望得到同學的崇拜、老師的肯定、父母的贊揚。在內心中,他儼然為自己構筑了一個毫無瑕疵和缺點的“超我”形象,開場處的宇航員便是這一形象的具體化。
王葆希冀通過葫蘆的神通使夢想中的“超我”成為現實中的可能,卻忽略了本我與超我之間存在根本性的沖突,那就是作為“本我”的寶葫蘆沒有任何道德觀念(所以它會為偷書和作弊洋洋得意),而“超我”的建構絕對不能離開深厚的道德基礎(如王葆不斷被要求對自己的“超常才能”做出合理解釋)。依弗洛伊德的理論,“自我”本可以調節“本我”與“超我”之間的矛盾,然而,影片前半部分的王葆根本沒有明確的自我意識,他只是沉醉在不切實際的幻想中,不了解自身的缺點和長處,因而也就不可能從現實出發,對現狀作出準確判斷、對未來進行合理規劃。所以,這個失落了自我的迷惘少年只能夠聽命于“本我”與“超我”的左右。既為擁有寶葫蘆沾沾自喜,又為考試不及格耿耿于懷,從未打算為實現夢想付出努力。他企圖借助不恰當的手段達到不切實際的目標,過程中又完全省略了個人意志的介入,結局自然屢屢事與愿違。
直到王葆扔掉葫蘆,他才真正開始思考自己的理想應該是什么以及如何實現的問題,對王葆來說,考試作弊被發現事件,既否定了“本我”的可依賴性,又否定了“超我”的可行性,使他初次意識到,正確認識自我對人格發展機制的重要作用。如果說,在扔掉葫蘆之前,王葆迷失在不合理欲望與不現實幻想編織的迷霧中,使他看不到自身的獨特性,那么,扔掉葫蘆之后,他終于開始了尋找以及確立自我的辛苦歷程。扔掉葫蘆,既是對“本我”的不合法性又是對“超我”的不合理性的摒棄。實際上也意味著立足現實的“自我”開始執行調節功能。這種調節的順利完成是以王葆獲得游泳比賽冠軍為標志的。在對快樂的追尋與對榮耀的渴求之間,他終于找到了一個能憑自身的才華與努力使其理想合情合理地實現的支點。也只有從這時開始(影片接近結尾處),這個少年時常充滿困惑的目光才變得清晰而堅定起來,那是因為他終于認識到了自身的力量與價值。此時,人格結構中的本我、自我與超我也終于達到了平衡狀態。
如果說,在童話文本中,寶葫蘆是以對立的姿態與王葆交流的,那么,在電影文本中,二者更多地呈現出一種彼此依存的關系(這一點在葫蘆被趕走后仍暗中關注王葆及王葆贏得比賽后尋找葫蘆的情節中明顯的體現出來)。正如前文所述,作為“本我”體現物的寶葫蘆其實也是王葆自身的一部分,因而,對王葆來說,泄露秘密實際上是對“本我”的以至于是對人格完整性的傷害,而保守秘密則意味著守護成長中來之不易的對個人才能、理想、價值、尊嚴的正確認知。
所以說,相比于主題單純的童話文本,電影《寶葫蘆的秘密》講述了一個更為復雜的故事:一個關于成長中的迷惘的故事,一個關于尋找自我的故事,一個透視出更濃郁的人文關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