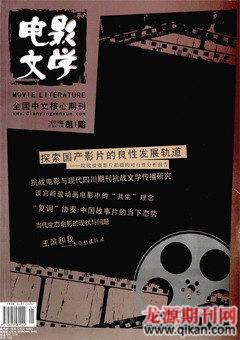不公平的天平
余 權
[摘要]《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這三部影片所反映出的倫理思想,很大程度上體現著張藝謀本人的倫理思想。張藝謀思想中存在著一個不平衡的倫理天平:右邊是對自生自發的倫理秩序的認可,左邊是對“人造”的政治秩序的自覺地維護,并且,張藝謀總是下意識地向左傾斜。他認為,個體的倫理秩序的追求應該建立在(而不是破壞)一定的政治秩序的基礎上。
[關鍵詞]倫理秩序;政治秩序;欲求;自由
根據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中對倫理的界定,“倫理是自由的理念”,一般體現為人的自由意志的具體實踐活動。同時,黑格爾的“理念”是一種“主觀的環節和客觀的環節的統一”,即,一方面是它在主觀的自我意識中有知識和意志,并通過行動而達到它的現實性,即個體自由意志的實踐,一方面它又在客觀現實性,即倫理性的存在中有其絕對的基礎和善的目的追求。因此,倫理是“客觀的東西”,但又滲透著主觀意志,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是自由和自律的統一。因此,倫理秩序原本就是自由的秩序,是在人與人的實踐交往中,在社會、歷史和文化積淀中逐漸形成的符合人的心理需求和理應這樣的秩序習慣,它體現出秩序的倫理性。在不同的領域,倫理秩序就體現為不同的倫理內涵。在思想及行為意識領域,倫理秩序就體現為道德,在政治領域,倫理秩序就體現為政治秩序和體制、制度,在經濟領域,就體現為一系列的經濟運行得以可能的規律和法則。等等。我們知道,不論政治、經濟和道德領域,都有一定的形式來表現其有規則的存在方式,即事物的存在秩序。但是,這樣的話,又會產生人的主觀意志,即倫理秩序與規范要求之間的錯位現象。這時候,就需要我們來調整。
目前,張藝謀導演了三部武俠電影。從倫理角度考察,不難看出,張藝謀武俠電影中所表現出的倫理秩序一直處于一種自覺的悖論當中。一方面他肯定個體欲求的表達和個體自由追求的合理性,即對自身自發的倫理秩序的肯定;另一方面,張藝謀又在潛意識中將這種屬于個體欲望的表達置于由權力監控和道德規范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秩序網絡之中,并且,這種秩序的力量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它被認定為人類幸福和安定的必要條件。
一
電影在表達作為主觀自由意志的倫理秩序時,主要從肯定個體欲求和對自由的追求兩方面來表現。首先,我們來看看個體欲求的表達,電影中的主人公的個體欲求主要表現為兩方面:愛與恨。愛,這里主要是人類普遍情感的體現。《十》中,“飛刀門”的小妹與縣府金捕頭情投意合,并最終決定私奔。劉捕頭也對小妹愛慕有加,當得知小妹已傾心金捕頭時,他痛心不已,“我就不相信,我等你三年,比不上他陪你三天。”此外,在《英》中,飛雪與殘劍的愛情也頗讓人感動,兩人視同知己,彼此深愛對方,最后彼此殉情,感天動地。《滿》中大王對前妻的復雜情感,對太子之死的痛心等,都表現出人間的骨肉之情。愛同時還表現為對天下蒼生的關懷。《英》中的殘劍不顧一切地阻止無名刺秦,他在地上寫了“天下”二字。“字同我心,望你三思。”殘劍的這種大愛感染了無名。以致其最終放棄刺秦,秦王得知后也將殘劍視同知己。電影里除了愛以外,也闡釋了另一種情感:恨。《英》與《滿》的故事都由“恨”而生。秦王殺了飛雪的父親,無名、長空皆因秦王殺戮而家破人亡,仇恨刻骨銘心。《滿》中的仇恨就更復雜了,王后對國王的恨,蔣太醫的妻子對國王移情別戀的恨,三太子元成對哥哥元祥的恨,等等,并因此產生出一系列的復仇行動。其次,便是對于自由的向往。影片中的主人公都體現出對自由的向往。《英》中,當飛雪得知殘劍已經成功阻止無名刺秦時,惱怒萬分,在打斗中誤傷殘劍致死,飛雪痛心不已,摟著殘劍,嘴里念著,“我們再不會浪跡江湖了,我現在就帶你回家,回我們的家”,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家”是人的避風港,也是自由的象征。《十》中小妹與金捕頭的自由意識更加自覺,為躲避“飛刀門”的追究,小妹不惜自己的生命,要和金捕頭去過“風一般的”、“非官非民,無門無派,來無影去無蹤”的日子,《滿》中的王后聯合杰王子反叛宮廷,也是為了獲得自己身體的自由,而杰王子在失敗后因無法忍受大王的拘禁而刎劍自殺。也表現出其追求自由的自覺。
不論個體的欲求還是對自由的向往,皆產生于人的欲望,也是人的自由意志在實踐中的反映,儒家是肯定人的欲望的,孔子在《禮記》中曾說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并提出“先義后利”的義利觀,墨子對此做了揚棄,提出了“義利并重”的觀點,但同時,墨子將儒家的個體利益放大為“天下之利”。在中國,儒家思想在很長時間是占主流地位的,因此,我們一般還是持“先義后利”的思想,這種現象被宋代二程(程顥、程頤)理學推向了極端,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倫理思想。二程提出天理為宇宙的本體,萬物都是從這里出發的,建構了唯理主義的倫理思想體系,并認為“天理”與“人欲”之間存在著對立關系,從而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倫理思想。這種倫理思想對人欲的壓制自然要引起人們的反對。清代戴震在反對“存理滅欲”的基礎上,提出了“欲根于血氣,故曰性也”(《孟子字義疏證·性》)的命題,論述了人是有生理心理要求的感覺實體,而情欲就是這個感覺實體的自然之性。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電影中的主人公的主體意志的表達了,這也是他們尋求自由的一個表現。但是,有一個問題,即影片中的大部分主人公都選擇了死亡。從劇情來看,他們是可以不死的,例如杰王子,但他最后還是自殺了,他還是為了獲取個體的自由。那么,這種以身體的消亡作為通往自由之路的思想又是從何而來呢?
與儒家人世的倫理思想不同,道家崇尚“自然無為”與“超脫義利”的倫理觀。在《莊子·齊物論》中,有一段影子的影子和影子的對話。影子之外的影子(罔兩)質問影子為何停停走走,沒有獨自的操守?影子認識到自己是有所“待”才如此的,“吾有待而然者邪”,莊子認為。只要有“待”,都是不自由的,所以才造成了人生中的許多愁苦和悲哀,所以,莊子要求人要超脫現實,看透名利,才能快樂。但是,生命會消失,這樣人類就感受不到快樂了,也引起很多人的恐懼,于是莊子又給予了解釋。在《莊子·至樂》中,莊子通過“髑髏見夢”的故事,闡明了人死了以后反而沒有生時的憂愁的道理。因此,在妻子去世后,他反而“鼓盆而歌”。莊子認為,一個人超脫名利,可以達到此生的快樂,但難免活著的痛苦,而一個人死了,則可以獲得永生的快樂,從而達到自由的境界。莊子把回歸自然當作個體自由的理想狀態,他不輕生,但他也不畏懼死亡。因此,影片中的主人公,無淪是他殺還是自殺,都沒有產生畏懼之感,我們看到的,并非僅僅是人物的悲劇性結局,更有一種自覺的超脫之后的愉悅。
盡管肯定個人的欲求在傳統倫理中是被明確肯定的,但這并未成為中國倫理秩序的主流,像電影中所表現出來的如此普遍和強烈的個體欲求和對自由的向往,顯然是張
藝謀本人注入的時代符碼,有著較強的現代性意識。
二
現在我們來探討,是什么力量促使這些人物選擇死亡(自殺或被殺)?我們只能從道家思想中找到他們選擇死亡的文化依據。但真正的心理動因到底會是什么呢?其實,細心的觀眾可能會觀察到一個細節,那就是在《十》中,劉捕頭和金捕頭在最后廝打的時候,電影曾閃過一個一秒左右的鏡頭,這個鏡頭是一群官兵已經構成包圍圈的場景。這實際上是告訴我們一種體制力量的存在,這種力量產生于政治秩序。也就是不論你們誰打贏了,最終都逃不過官府的追兵。政治秩序是一種“人造的秩序”,最先,它是倫理秩序在政治中的體現,后來,隨著統治者自覺意識的產生,便通過恰當的方式將其中的一部分固定為社會的制度性安排,從而實現統治者對自然人外在的自然界和內在的本性的有限度的控制,在張藝謀的武俠電影中,所有的人物都生活在(政治)秩序之下。《英》中的殘劍極力制止無名刺秦,理由便是:國家的統一是百姓蒼生過上好日子的唯一前提;《十》的金捕頭要和小妹私奔,但他們都觸犯了各自階級的規章制度,《滿》則展示了秩序的雙重破壞的后果:一是道德,一是政治。影片中,大王嚴肅地對杰王子說,“天地萬物,朕賜給你,才是你的,朕不給,你不能搶。”“朕”就代表著政治秩序。另一面,王后和太子私通,兄妹亂倫等,都表明對道德秩序的破壞。影片通過將家國糅合,將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擠壓到一塊,體現出不可觸犯的政治威嚴。
中國傳統政治與道德秩序源于儒家的“禮”。孔子認為,“克己復禮”,才能培養“仁”心,這就需要用一整套政治制度、禮節儀式和道德規范作為“克己”的標準。為了讓“禮”更具有規范意義,提出將“禮”法制化,使“德治”與“法治”相輔相成的政治倫理思想。后來,以《儀禮》、《周禮》、《禮記》為代表的“三禮”標志著儒家倫理思想在封建時期統治地位的確立,它們都強調“禮”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要維護封建的等級制度。這樣,“禮”就由原來的規范禮儀,轉化為統治階級賴以統治的政治手段,于是,道德要求與法制制度相結合,“禮”不僅成為中國人的思想,也同時成為中國人的文化積淀和思維習慣,由“禮”所產生的“秩序”自覺也成了中國人的一種心理自覺。
因此,張藝謀對政治秩序的要求非常強烈,非常自覺。影片反映出,無論是政治秩序自覺地維護還是破壞,都需要付出血和生命的代價。此外,維護政治秩序的權威感,需要統治者的強勢手腕和法治思想。《英》中的秦王并沒有因為無名放棄刺秦而放他一條生路,這實際上體現了法家的“勢”的統治策略。
張藝謀認為,要無條件地保持政治秩序的穩定,在這樣的框架下,國家才能公平地分配民主和正義。然而,在封建政治秩序下,帝王分配的是基于統治階級利益的正義和民主,這必然要取代滲透個體的欲求和自由的“自生自發”的倫理秩序。另外,我們看到,電影中的主人公認為只有結束自己的生命才是通往個體自由的唯一出路,顯示出了道家思想消極避世的弱性。在西方哲學中,尼采的“唯意志論”極力強調個體意志的體現,薩特則通過后天的個體選擇來重新確定人的本質,這中間,有一種很強的抗爭意識,也并不強調主動的個體消亡。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貌似灑脫,實則悲觀。
結語
不難看出,張藝謀武俠電影中所表現出的倫理內涵一直處于一種自覺的悖論當中。在他的倫理天平中,一直是向左傾斜的。在由權力監控和倫理規則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龐大的秩序面前,張藝謀選擇的是繳械投降。張藝謀從不打算質疑或消解政治秩序,也一直都對既定的政治秩序懷著一種宗教式的崇拜。對于自然的倫理秩序。張藝謀總是停留在心靈層面的追求,也因為這樣,我們總是看到影片中強烈的悲劇意識。難能可貴的是,影片對自然的倫理秩序的展現與肯定已經非常自覺,這顯示了張藝謀較為強烈的現代性意識,在這樣的前提下,他還是認可體制與政治秩序的巨大力量,這也表現出他在后現代語境下的試圖重構的自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