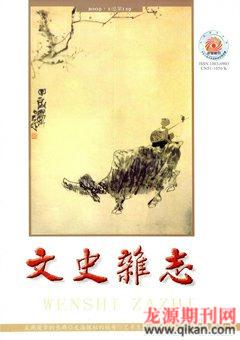“麻鄉約”考辨
鄧經武
一
“麻鄉約”是1852年(清咸豐二年)四川省綦江縣人陳洪義在重慶創辦的“麻鄉約大幫信轎行”的簡稱,主要從事轎子、滑竿等客運、貨物搬運以及信件傳遞業務。在尋根大潮涌蕩的今天,它卻被一些研究“湖廣填四川”的人,引用為四川(包括重慶)的湖北麻城縣孝感鄉移民后裔與故鄉聯系專業機構的重要證據。其主要表述有:
樓祖詒的《中國郵驛史料》(人民郵電出版社,1958年)說:“據四川人傳說,‘麻鄉約起源于明初。當時四川省的移民,多是湖廣麻城縣孝感鄉人。移民思念家鄉甚切,每年約集同鄉,推出代表,還鄉一次,攜帶家鄉產品回來,久久成為習俗,建立了固定組織”。
王文虎、張一舟、周家筠編的《四川方言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15頁,1987年)中“麻鄉約”詞條解釋是:一,麻指湖北麻城縣。麻城鄉約的簡稱。舊時,四川境內的湖北麻城移民每年推選辦事公正,講守信義的人作代表回老家探親、送信,這種人被稱為“麻城鄉約”。二,麻鄉約大幫信轎行的簡稱,是清代末葉至民國期間西南規模最大的一個民間運輸行業,經營客運、貨運、送信三種業務。清咸豐二年,四川纂江人陳洪義創立,至1949年行務結束,延續近一百年,影響甚大。因陳洪義熱心公益事業,辦事公正無私,加以臉上又有麻子,當時人尊之為麻鄉約。后即以此為其企業名。
陳煥彪、翟寬的《簡明集郵詞典》(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第255頁,1987年)“麻鄉約”詞條:在我國東南各省出現民信局的同時,西南各省出現的民信局,稱為“麻鄉約”。相傳湖北麻城縣孝感鄉被遷往四川開墾的農民,由于想念家鄉,相約每年推同鄉回鄉幾次,來往帶送土產和信件,后來就形成專業的民信局。它是清代西南地區一家規模較大的民間郵交企業。
《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麻鄉約”:麻鄉約是由纂江縣號坊鄉陳家壩出生的陳洪義(又名陳鴻仁)個人艱苦奮斗創立的運輸匯兌行。相傳清初湖北麻城孝感鄉大批移民來川定居,因懷念鄉里,每年推選人員回原籍探望鄉親,往返帶送土產信件。由于擔任送信送物的人辦事負責,遵守信義,人民稱之為“麻鄉約”。麻表示麻城;鄉約,是當時農村中負責調解糾紛的人員。陳幼時家貧,二十歲左右在纂江、重慶間下苦力,以抬轎謀生,后在川黔道上當伕子。因他肯賣力,常與人義務挑東西;在同伙中又愛排難解紛,辦事公正,墊錢墊米,亦所不惜,猶如鄉約一般;他的面部恰有麻子,群眾遂稱他為“麻鄉約”。陳后來聲望日高,逐漸成為封建把頭,大約在咸豐二年(1852)組織起以“麻鄉約”為名的運輸行(當時又叫“腳店”)。
一本談論“湖廣填四川”的書的作者說:“后來從麻城市委辦公室的凌禮潮手上,我們得到一張明信片,上書‘麻鄉約三字。原來,相傳在明代永樂年間,就有移民從這里遷往四川,由于思念故鄉,相約每年推選同鄉代表回鄉幾次,來往帶送土特產和信件。久而久之,建立了固定組織‘麻鄉約。它開創了中國民間通信的先河。”
這些公開出版的論著,依據的都是“據說”、“相傳”,卻又被許多人引用為真實的史料,這難免有捕風捉影之嫌。既然是移民思念家鄉甚切,每年約集同鄉,推出代表,還鄉一次,攜帶家鄉產品回來,久久成為習俗,“建立了固定組織”,那么在四川、重慶(還有云南、貴州)眾多的家族譜牒中,就應該有明確的記載,各地湖廣會館也應該有碑刻等文字證明。因為這類家族大事,每家出資多少,哪個出資重點捐助,都應該有確鑿的文字記錄。如果真的有這樣的緊密聯系,我們今天看到的許多家譜,就不會在移民時間、原居住地的地名、移民原因等記載上,如此混亂和矛盾百出。筆者翻閱過一些家譜,沒有見到過四川人到麻城縣去尋根的記載,而“麻城縣孝感鄉是中國十大移民圣地”、“四川人都是麻城縣孝感鄉移民后代”等說法的堅持者們,也至今沒有提供過這樣的證據材料。
這里順便說一下,清代嚴如煌的《三省山內風土雜談》說,明末清初的戰亂,對湖北地區造成嚴重災難,涌入湖北西北地區的移民“北則取道西安、鳳翔,東則取道商州、鄖陽,西南則取道重慶、夔府、宜昌,扶老攜幼,千百成群,到處絡繹不絕。”清人說:“此地從來無土著,九分商貿一分民”;并注“一分民亦別處之落籍者”,“本鄉人少異鄉多”(《文獻通考》)。也就是說,湖北西北部的麻城、孝感、黃安等縣,正是移民遷往“填充”的地方。康熙版《安陸縣志》說:“聞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得城東老戶灣數戶而無其人,烏兔山之陰空土以處者幾人而無其舍,徙黃麻人實之,合老婦孺子僅二千人,編七里”。時有人記道:“湖湘之間,千里為墟,騷馳十余日,荊棘沒人,漫不見行跡”。因此,湖北省麻城縣自身荒蕪的問題尚待急需解決,怎么可能移民去四川填充人口空缺?
二
我們先從中國郵遞業的發展和稱謂說起。中國屬于大陸農耕型國家,在漫長的封建時代中國的根本經濟都是農業,土地問題是歷代統治者、地主和農民所關注的第一要務。祖祖輩輩安守在一塊土地上,循環往復;“安土重遷”成為中華民族的最基本的價值意識。除了人口比例極少的商人商旅、讀書士子的游學、官員的仕途遷徙外,絕大多數的人終生死守在一塊地方。河南因為黃泛災難的外出逃荒、安徽鳳陽的外出逃難,是極少的歷史現象,但災難過后他們還是要返歸故里的。現在50歲以上的人都知道,至少在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農村和小鎮,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都沒有向外界發出過、也從未收到過一封信件。因此,中國近代以前的郵遞業,基本上是政府專設為公文、軍事情報傳遞服務的。
據甲骨文、金文及其他出土文物記載,夏朝設立了“牧正”、“庖正”和“車正”等與交通郵傳有關的官吏;商代已經建立了“驲傳”郵傳制度,有專門的郵局“驲置”;“烽火”亦是一種傳遞信息的補充方式。孔子的“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墨子·雜守》的“筑郵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詩經·公劉》中的“于時廬旅”、“于豳斯館”等句,就記載著當時的郵遞業情況。秦代統一后實行“車同軌”的交通制度,設置驛道和郵驛,并把原來的“遽”、“驲”、“置”等各種稱謂統一為“郵”。從此,“郵”便成為通信系統的專有名詞。在漢朝初年,中國的郵遞業稱為“置”。東漢人應劭寫的《風俗通》說:“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置之也。”說明驛和郵已經開始分開。政府中的尚書令和符節令,便是專管政府公文收發的官吏。《后漢書·西域傳》說當時“列郵置于要害之路”。中國第一部郵政法是曹魏政權頒布的《郵驛令》。唐代郵傳業有專門組織“明駝使”和專門設施“郵筒”。杜甫有詩記載在蜀中看到的景象:“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岑參在《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中說道:“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威陽,暮及隴山頭。”《新唐書·元稹傳》中說“役郵子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高適《燕歌行》詩云“校尉羽書飛瀚海”。沈括《夢溪筆談》記載,宋代郵遞分三等,即步遞、馬遞、急腳遞。元代的郵傳稱為“站赤”。《大明會典》卷一四五記載明代郵傳業盛況:“自京師達于四方,設有驛傳,在京曰會同館,在外曰水馬驛并遞運所,以便公事人員往來。其間有軍情重務,必給符驗,以防詐偽。至于公文遞送,又置鋪舍,以免稽遲,及應役人員各有事例。”清代又將郵、驛合并,并發展了“縣遞”基層郵政,有驛、站、塘、臺、所等不同地區的郵站稱謂。晚清朝廷設置“郵傳部”后,中國近代郵政事業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概而言之,中國的郵傳業,在不同的時代,先后使用過驲、置、驛、傳、信使、驛馬、郵驛、驛傳、傳驛、館驛等稱謂。
古代私人信件一般是自派專人遞送,或者委托外出的友朋順便捎帶。地位較高的官員和社會名流,常常違規地借助政府郵傳體系傳遞私人信件。晚唐蜀中高僧貫休詩云“尺書裁罷寄郵筒”,宋代歐陽修的“郵筒不絕如飛翼”,王安石“郵筒還肯寄新詩”,清代蒲松齡《聊齋志異·自敘》說他愛收集鬼狐故事,于是“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由此可知,“郵筒”是古代私人寄送書信的代稱。古人常用尺素、魚書指代通訊郵遞,傳遞者為“信使”或指代為“鴻雁”。非官方郵政業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的“養士”,需要有自己的郵傳人員。漢代初期諸侯王曾經設立私人郵傳,但迅即被取締。魏晉時期商業發展引出“逆旅”、“邸店”等私家旅店和民間郵傳事務,卻遭受政府重稅高壓。唐代有民間“驛驢”郵傳組織。明代商人開始正式經營“民信局”。這種民間郵傳組織在清代道光、咸豐年間已經發展到幾千家。同時在沿海一帶還出現專門辦理對外郵政事務的“僑批局”。1834年英國在廣州設立郵政局,西方列強在中國的郵傳業“客郵”于此開始。
再說“鄉約”,這是對封建社會社會底層負責調解糾紛、具有一定威信的人員的稱謂,其作用是獨斷地方爭訟,可以施用刑法。其對基層社會的控制主要體現在:操縱宗族、保甲組織;通過舉辦社會公益事業控制地方;掌握地方教化等。
《周禮·地官·族師》說:“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這就是先秦時期對最底層的社會組織的設置。中國最早成文的鄉里自治制度,大約是北宋學者呂大鈞、呂大臨等于北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制定的“呂氏鄉約”,其四大宗旨是使鄰里鄉人能“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到了明代,朝廷大力推行鄉約制度,“嘉靖間,部檄天下,舉行鄉約,大抵增損王文成公之教。”如文伯仁的《棲霞新志》的主要條目就有“倉場、坊表、郵遞、鄉約、保甲、祀典”。明代發展的一套以鄉約、保甲、社學、社倉為整體性的基層自治系統,開始被清王朝沿襲下來。這種鄉村和基層社會管理制度的執行人就是“鄉約”。
《辭海》(1979年版)解說為:“鄉約,舊時奉官命在鄉中管事的人”。(清)劉登科修,謝文運、王芝藻等纂的康熙版《溧水縣志》卷三《建置志·鄉約》就記載:每鄉設鄉約所,置約長、副約長,鄉約堂內藏朝廷諭牌等,常集里人于此講解,并置有二簿冊,登記善惡,間行勸懲。
在文學作品中也有關于“鄉約”的描寫。元代睢景臣《般涉調哨遍·高祖還鄉》描寫的“社長排門告示……王鄉老執定瓦臺盤”,這里提到的“社長”、“鄉老”都是鄉約一類人員。前面說到,宋、明以來“鄉約”制度正式形成,在文學作品中也就得到反映,如《儒林外史》第六回:“族長嚴振先,乃城中十二都的鄉約”。20世紀中國最杰出的短篇小說作家、“中國鄉鎮人生”最優秀的刻畫者沙汀,其成就多數建立在“鄉約”形象的描寫上。20世紀30年代,標志沙汀創作轉向的“一個道地的四川故事”就是《鄉約》(1935年,后改名《丁跛公》)。因此,我們應該按照《辭海》的定義來解釋“鄉約”。
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同意麻城的某官員自稱“麻鄉約”——以地名(麻城)、權力(地方小吏)、行狀(盛氣“凌”人)為界定,這倒是最恰當不過的。
但是,用“麻”作為人稱代指,在四川民間極為普遍。一般是由于所指代的對象患天花(出麻疹)的后遺癥導致臉上凹凸坑洼而獲得的綽號。四川民間戲稱某人為張麻子、李麻子,甚至直接戲呼對方為“麻子”,背后稱呼某領導為“麻科長”、“麻主任”等比比旨是,而不管對方是否臉上光鮮。這已經是一種極為常見的現象,猶如四川名菜“麻婆豆腐”的得名一樣。這其實更多地是一種語言的機趣、幽默或四川話所說的“涮壇子”。筆者當年在農村、在工廠的最底層生活經歷,對此感受極深。著名作家沙汀帶著一種巴蜀地域民俗習慣觀察對象,他眼中的胡風就是:“個子高大,臉上微微有幾粒麻子,不太明顯”(吳福輝:《沙汀傳》,十月文藝出版社)。在其他地域的作家筆下,我們很難見到這樣的觀察視角。也由于川菜“麻辣燙”的特點,“麻”在四川話中的應用極為普遍,如酒喝多了為“喝麻了”,感覺被人糊弄為“你麻我?”“你麻哪個不懂”……如果凡是帶“麻”字,都與麻城縣聯系起來,那就真正成了天大的笑話。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中國歷代郵遞業決無“鄉約”之說,而自從明代開始,社會基層組織“鄉約”已經明確地呈現于史籍記載、文學作品中。四川民間人士用自己的某種生理特征為自己的企業命名,如“耗子洞張鴨子”、“痣胡子腌臘店”等,在今天的成都街頭還可以看到。“麻鄉約”準確地解釋,應該是《四川方言詞典》的第二個釋義:“大幫信轎行的簡稱,是清代末葉至民國期間西南規模最大的一個民間運輸行業,經營客運、貨運、送信三種業務。清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四川纂江人陳洪義創立,至1949年行務結束,延續近一百年,影響甚大。因陳洪義熱心公益事業,辦事公正無私,加以臉上又有麻子,當時人尊之為麻鄉約。后即以此為其企業名。”所謂“麻鄉約”“開創了中國民間通信的先河”的說法,是一種缺乏基本歷史常識的無稽之談。
最后,我們用一個個案來談談“據說”、“相傳”的真實性問題。早在周朝,就有“五月五日,蓄蘭而沐”的習俗。端午節門口掛陳艾、菖蒲的習俗,唐代就有,殷堯藩《七律·端午》有描繪:“少年佳節倍多情,老去誰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趨習俗,但祈蒲酒話升平”。而在所有的四川(甚至西南地區)人們的口中,這種習俗被與張獻忠聯系起來。說的是張獻忠在圍剿四川人的途中,看到一個婦女背著一個稍大的孩子,卻牽著一個更小的孩子逃難,覺得該婦太偏心,下令手下捉來嚴處。審問時方知,小的孩子是該婦親生,大的孩子是侄兒,其父母雙亡,所以給予額外照顧。張獻忠聞后很是感動,要該婦不必逃難,回家去在門楣上懸掛一把草作為記號,士兵不得進入騷擾。該婦回家后在屋旁隨手扯了一些陳艾、菖蒲,掛在門口。鄉鄰們得知后紛紛效法,從而獲得平安。后演變為禳災祈福的習俗。
(題圖選自《成都日報》)
作者:成都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