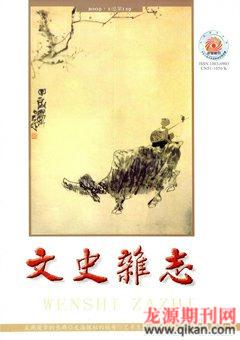重新評價農民起義
李殿元
近幾年,曾經是史學研究熱門的農民起義研究陷入沉寂,幾乎看不到這方面的論著。究其原因,是有關農民起義的研究陷入誤區,走入了死胡同:由于過去片面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行農村包圍城市,農民作為主力軍,在革命的進程中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因而我們的歷史研究一反歷代史書將農民起義定性為“亂匪”的慣例,對農民起義予以了充分的歌頌和贊美。在這種錯誤比擬思想的指導下,歷史教科書將歷史簡單地描繪成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迫使農民起義——建立新政權,減輕剝削——貪婪的地主階級又加重剝削和壓迫——又爆發農民起義……的不斷循還,農民起義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唯一動力。這種形而上學的論點當然是不能正確解釋歷史發展的。撥亂反正以后,有人從根本上否定過去對農民起義研究的成果,認為農民起義是“造反有理”,但是“造反無功”,農民起義的客觀效果“是使千百年創造的文化精品和社會財富毀于一旦”[1]。不過,這種對農民起義進行全面否定的“新見”似乎并未被史學界所接納,應者寥寥。農民起義研究在此后竟處于停頓,這無論如何也是不正常的。有鑒于此,本文認為有必要對農民起義進行重新研究。
一、對農民起義要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
必須承認,在對農民起義的研究中,我們過去有形而上學的傾向。由于對農民這個受壓迫者對地主階級反抗“造反有理”的全面肯定和歌頌,史學界長期認為,農民反抗地主階級的斗爭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甚至是唯一的動力;農民起義、農民戰爭是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因而對所有的農民起義均進行了充分的肯定,認為凡是農民起義均是“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而沒有考慮過應對每一次農民起義的作用進行具體考察和具體評價。十年動亂結束后,史學界雖然圍繞農民戰爭是否是封建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展開過討論,但對全部農民起義仍是持肯定的態度。而持農民起義“造反無功”的“新見”者,雖然一反史學界的傳統觀點,全盤否定了農民起義對社會發展有可能起推動作用,卻仍然未能考慮到應對每次農民起義的作用進行具體的考察和分析。
我認為,以上兩種對農民起義進行評論的觀點均可稱為“一概而論”派,都犯了觀察事物、評論事物絕對化的主觀主義的錯誤。試想中國歷史上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有數百次,背景、原因、過程、結局都有一定的差異,作用又怎能完全一樣呢?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2]
這段曾被廣泛引證的毛澤東同志關于農民起義、農民戰爭作用的論述,并不是“一概而論”的。毛澤東同志在這段話中加有兩個限定詞:“較大的”和“多少”。那么,可以肯定,“較小的”農民起義顯然是未包含在內的;即使是“較大的”農民起義,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推動作用也有“多”與“少”的區別。由此可知,毛澤東同志是主張客觀地對每次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的作用都進行具體的考察和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的。遺憾的是,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論述雖被研究者廣泛引用,而卻往往忽略了其中的限定。
既然農民起義有“有作用”或是“無作用”,作用是“大”還是“小”等區別,我們在研究農民起義時,應該對其具體分析,決不可以采取“一概肯定”或是“一概否定”的態度。
二、農民起義不僅有“失敗”,也有“成功”
傳統觀點認為,農民起義對社會生產力有推動,但農民起義本身要么是被統治者所鎮壓,要么是被“混入革命隊伍的地主階級篡奪”了去,因些“總是陷入失敗”。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
農民不代表新生產力,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權;即使有志建立,也必然迅速瓦解。毛澤東同志深刻指出:封建社會中的“農民革命總是陷于失敗”[3]。這是就“農民革命”的終極目的來立論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客觀規律。
就“農民革命”的終級目的而言,“總是陷于失敗”;就“農民革命”的作用而言,并不總是“失敗”。在中國封建社會大小數百次的農民起義中,有些農民起義確實“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即使像隋末農民起義一樣,被山西的地主階級人物李淵、李世民“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但仍然“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貞觀之治”。這應是相對的“勝利”,而不能說是徹底的“失敗”。如果農民起義的領導人自己做了皇帝,像秦末農民起義領導人劉邦、元末農民起義領導人朱元璋那樣,重新建立一個比舊封建政權稍好一些的新封建政權,“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從而較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就更是一種較大的“勝利”了,因為他走的是“歷史必由之路”。歷史只能是奴隸制代替原始社會,封建制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社會的,從來就沒有農民起義建立“農民政權”來代替封建社會的可能。
因此,在封建社會中的新生產力——資產階級還沒有出現以前的農民起義,要對歷史起到推動作用,就只能打倒一個極其殘暴極其腐朽的舊封建政權,重新建立一個“此善于彼”的新封建政權,走符合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歷史必由之路”。因為封建社會的農民階級,還不可能意識到他們受苦的根源在于封建剝削制度,他們并不反對一般的剝削,只是希望能夠減輕剝削。所以農民起義只是反對暴君而不反對“好皇帝”;反對貪官而不反對“清官”;反對惡霸地主而不反對一般“不劣”的地主。如果農民起義領導人,自己做了“好皇帝”,任用大批“清官”,打擊惡霸地主,輕徭薄賦,做到政簡刑清,安定統一,使農民生活比過去稍好一些,就更是對歷史的較大貢獻了。
相反,如果農民起義者不走“歷史必由之路”,執行了違反歷史要求的錯誤政策,或由于其他種種原因而遭到失敗,沒有摧毀舊的封建政權,不但自己人當中不能涌現一個“好皇帝”來建立新的“此善于彼”的封建政權,甚至也沒有給“利用”者提供一個較好的條件,戰爭失敗之后,帶來國家分裂、異族入居中原以及地主階級的反攻倒算,農民自然是很痛苦的,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說不上有多大的作用了。例如黃巾起義的失敗,使國家分裂成魏、蜀、吳三國,并且造成連鎖反應,使西晉王朝的統一也不能持久,混亂了好幾百年。又如黃巢起義的失敗,也帶來“五代十國”的分裂,趙匡胤后來雖然勉強統一了大部分地區,但因為沒有農民起義為他摧毀舊的封建勢力,他建立的這個封建政權,就不及唐朝那樣強大和鞏固,不能抵抗外來的侵襲。這當然也是對農民階級很不利的。還有更多的小規模的農民起義,很快遭到失敗,結果帶來了地主階級的“反攻倒算”。例如北宋末年的方臘起義失敗之后,宋徽宗立即恢復了“花石綱”,還增加了更大規模的剝削。這對農民階級就更沒有多少好處了。
所以,農民起義只要走的是“歷史必由之路”,摧毀了舊的封建政權,自己或由他人來建立一個“此善于彼”的新封建政權,就應當算完成了歷史任務,就是“成功”了的農民起義;反之,就是“失敗”了的農民起義。歷史客觀地證明,中國歷史上確實是有取得了相對“勝利”,“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成功”的農民起義。這樣的農民起義的領導人,即使當了皇帝,走的仍然是“歷史必由之路”,完成的仍然是農民起義的歷史任務,說不上是對農民起義的“背叛”。
三、農民起義對社會歷史推動作用的表現
封建社會在它發展的同時,它本身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也日益展開,并趨于尖銳化。封建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必然表現為占據國家機器并拼命維護舊統治的地主階級與廣大農民的矛盾,或者說生產過程中的個體性質與封建所有制的矛盾。矛盾的尖銳化必然導致農民起義。因而,從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開始,兩千年來爆發過無數次的農民起義,其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4]。由于農民不代表新生產力,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而建立資本主義制度,農民起義的偉大作用就只能是——對殘暴的封建統治給予沉重的打擊,迫使或促使新的統治者調整政策,使整個封建政治經濟諸關系發生相應的變化,為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
農民起義對社會歷史確實是有推動作用的。首先,推翻極其殘暴極其腐朽的封建統治舊政權,重新建立一個“此善于彼”的封建統治新政權,是農民起義的目的。而歷史上的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如秦、新莽、隋、唐、元、明,都是由全國性的農民起義所摧垮、推倒的。歷史事實充分證明,不摧毀這些殘暴腐朽的封建舊統治,貴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以致“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狀況就不能阻止,“此善于彼”的封建新政權就沒有建立的可能;那么,廣大農民連簡單的再生產都很困難,更不必說擴大再生產了,哪里還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及社會歷史的前進呢?因此,必須承認,是農民起義摧毀了封建舊政權的統治基礎及國家機器,才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掃除了障礙。
農民起義對社會歷史的推動作用,其次表現在迫使封建統治者“改造”或“調整”政策。封建國家的政策,在根本上是處理地主階級與農民之間關系的,當然是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封建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發展,起著加速或阻礙的作用;封建國家的政策,也是這樣或者是順應生產力的發展,或者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封建國家的政策不是不可變換的。特別是在大規模的農民戰爭過程中,由于農民起義者懲辦了一批剝削、壓迫農民最深,農民最痛恨的封建官吏、惡霸地主,從而教訓了封建統治者,使他們在以后剝削和壓迫農民的時候,有所收斂。在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后所建立的新的封建王朝所采取的政策一般都有特別顯著的改變,往往都能執行緩和階級矛盾、有利于發展生產、穩定政局、使老百姓能生活下去的“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這一政策與前一王朝“役重賦勤”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個變換不能不說是農民起義造成的。
大量事實證明,封建統治階級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不得不逐漸減輕對農民的剝削量。雖然隨著階級斗爭的起伏,剝削量時有升降,但總的是一個下降趨勢。例如:在徭役方面,秦朝時最高達到壯年男子的三分之一以上時間,到漢朝時減為“三年而一事”;唐朝規定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無徭役可納絹替代;明朝中葉實行“一條鞭法”后,農民可交納役銀以代替徭役。沉重的徭役負擔往往可使農民很快破產。秦末和隋末農民大起義,都直接反對徭役。所以每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之后,徭役的變化都比較明顯。再如賦稅方面,秦代“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西漢初年田租減為十五稅一,后再減為三十稅一;北魏開始實行均田制時,一夫一婦出帛一匹、粟二石;到唐代每丁納租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麻三斤;北宋初年,一般是畝輸一斗,但因為有“支移”、“折變”以及丁口雜變之賦,實際交納的遠遠超過一斗;明初大量實行屯田,民屯“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牛種者十稅三”;隨后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以及清初的“攤丁入畝”,都逐漸減輕了對農民的剝削量。如果再加上隨著生產力的提高使單位面積產量的增加,封建國家對農民的剝削量的絕對比率更有明顯的下降。這當然對提高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增加擴大再生產的投資,起了積極的作用。不用置疑,這與農民起義所顯示的威懾作用以及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打擊是不無關系的。
如果沒有農民起義對極其殘暴極其腐朽的封建政權的打擊,被抑制的社會生產力就很難迫使不適應的生產關系進行調整,那么,哪里還有社會歷史的前進呢?只有通過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對封建化進程中的一些腐朽沒落的東西予以堅決的打擊,才能將統治階級很難通過自我調節而在短期內加以克服的東西像秋風掃落葉一樣,一下子予以清除掉。而且也只有清除了這些腐朽沒落的東西,封建化的發展才能不斷深入。如果腐朽沒落的東西未予以清掃,封建化的發展常因包袱過于沉重而呈現出停滯不前的狀態;則只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才能減輕這一負擔,給停滯狀態以新的發展的動力。雖然農民起義之后建立的仍然是封建政權,但必定是相對于舊政權好一些的新政權。
四、推動歷史前進的不僅是農民起義
盡管農民起義能夠推動歷史的前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是它決不是封建社會能夠前進的唯一動力。
封建社會里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本身就是一對矛盾體,共存于封建社會。歷史上沒有由單獨的地主階級或是由單獨的農民階級組成的社會。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在封建社會里不僅共存,而且始終互相制約。他們之間不僅有斗爭性,也有同一性。[5]當農民階級尚能生活和繁衍下去時,他們就安于現狀;當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剝削、壓迫已使農民階級不堪承受時,他們就奮起反抗。“王侯將相,寧有種乎?”[6]反抗的目的正是要求實現階級的轉化。雖然兩個階級的對換是不可能,但卻不能否認作為兩個階級中的一些個體,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會因為各種原因而出現一些變化,并且各自朝著與自己原有地位相反的方向發展。例如,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盡管不可能改變封建制度,但是在農民戰爭風暴掃蕩過的一些地方,平時橫行鄉里、作威作福的惡霸地主必然被鎮壓,他們的財物必然被分配給貧苦農民或是充作軍用。這些地主的家屬們就必然因為家庭政治、經濟地位的突然衰落而被迫自食其力,逐漸演變為農民。同時,當農民起義者建立的新政權取代舊政權時,農民起義的領袖及其將領又必然會轉變為新的統治階級,成為新的地主階級。因為各種原因而出現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或升或降的情況,在封建社會里是普遍存在的。
如果只承認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有斗爭性而否認有同一性,那么就無法解釋這一歷史現象: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雖然爆發的農民起義的次數、規模,都是世界歷史上最多最大的,但無論是時間、影響區域等,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畢竟只是小部分。封建社會歷史的更大部分時間,雖然也充滿了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斗爭,但的確是以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沒有劇烈、尖銳的階級沖突,社會相對穩定,生產力能有較大發展的狀況居于主導地位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的作用、意義盡管是巨大的,但戰爭的目的并不是徹底打破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而是要求調整,要求建立一個相對減輕剝削程度的封建新政權。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7]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論述,無疑是正確的。所謂“人民”,即是指“一定社會的基本成員”。在封建社會里,這不僅包括農民階級,也應當包括那些對歷史發展起過推動作用的地主階級在內。盡管在那時處于被統治地位的農民階級是創造社會物質財富的主要力量;但是,社會歷史的發展和前進,不僅需要物質力量,還需要其他力量,如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等等。即使是物質財富的創造,也需要社會提供必要的環境和條件。而這些,就不是農民階級所能獨立完成的了。歷史發展的客觀事實就是:如果不承認“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些地主階級代表人物對歷史發展所作出的貢獻,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就無法闡述清楚;如果不承認像屈原、李白、杜甫等地主階級的大文豪們對歷史發展所作的貢獻,中國的文學歷史就幾乎是一片空白。還有許多對歷史發展所作出過卓越貢獻的大政治家、大科學家、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大軍事家等等,他們是屬于地主階級還是農民階級呢?我們總不能將他們劃在“人民”的范疇之外吧?
五、要敢于承認并正確評價農民起義的“破壞”
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在掃蕩殘暴封建舊政權的腐朽陳規時,必然會對社會財富、物質資源、文明成果乃至社會生產力造成破壞,這些是不容否認的。翻開史書,有關這方面的記載相當多。這其中除了地主階級的史學家有意誣蔑和夸大事實外,應該承認,農民起義必然要對社會造成破壞。問題是,我們應當如何對農民起義的破壞進行正確評價。
只要是戰爭,就必然要對社會的經濟、生產、生活等有所破壞,被壓迫農民所掀起的農民戰爭當然也不例外。但是,既然任何形式的革命戰爭都無法保證對社會不起破壞作用,那么,我們就沒有必要對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去進行類似“建設不足,破壞有余”[8]的責難。
戰爭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盡管正義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都必然會給社會造成破壞,但正義戰爭之所以要“破壞”,正是為了使社會今后減少破壞。這是為了消滅破壞而不得不進行的“破壞”。其性質是不同的。不區分性質而將戰爭對社會的破壞作用一概而論,是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的。如果不靠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去對舊的封建統治政權及其統治基礎予以“破壞”,那么,“此善于彼”的封建新統治就難以“建設”起來。可見,“破壞”和“建設”不能截然劃開,“破壞”正是為了“建設”,“破壞”之中本身就已經包含了“建設”。這種“破壞”是應當被肯定的。
其實,在農民起義的洪流中,必然魚龍混雜,一些散兵游勇和盜賊也廁身其間,利用農民起義過程中的“破壞”給社會造成更多的危害。所以對農民起義過程中的“破壞”,必須實事求是地看待。而且,認真研究起來,造成這一“破壞”的根源就在于封建剝削壓迫制度。在鎮壓農民革命中,諸如隋煬帝對起義者、曾國藩輩對太平軍的大肆屠殺,不勝枚舉。誠如唐代詩人韋莊在《秦婦吟》中所描述的那樣:“千間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后猶殘半。自從洛下屯師旅,……罄室傾囊如卷土。”官軍的“破壞”程度遠甚于農民起義。他們不僅對社會生產、經濟進行了大破壞,而且也阻礙了社會的前進。我們的史學家有什么理由根據農民起義的那點“破壞”而否定其“推動”作用呢!說到對社會財富的破壞,那些地主階級的荒淫奢侈生活,才是對社會財富的巨大破壞和浪費;尤其是地主階級之間爭權奪位的非正義戰爭,如西晉“八王之亂”這樣的社會大動亂,不知毀壞了多少文化精品和社會財富!
所以,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對社會經濟、生產、生活必然是有所“破壞”的,甚至是嚴重的“破壞”,這是用不著掩飾的。問題是如果沒有這些“破壞”,那么對殘暴腐朽統治階級的打擊又從何體現?因此,以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對社會歷史的推動作用和“破壞”作用兩相比較,只能認為“破壞”是難免的,是歷史前進所必然要付出的昂貴的代價。
注釋:
[1][8]見上海《社會科學報》1989年4月20日。
[2][3][4]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25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參見拙文《試論封建社會兩大對立階級的同一性》,《天府新論》2002年第5期。
[6]《史記·陳涉世家》。
[7]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單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