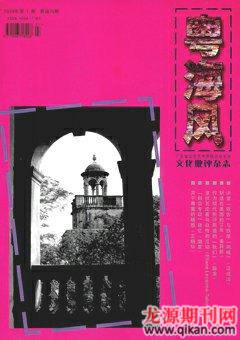胡適在美國的26年
姜異新
秋日的普林斯頓大學校園嫵媚多姿,爬滿常青藤的瓊斯樓,因為有愛因斯坦的研究所和胡適做過館長的葛斯德東方圖書館而成為名副其實的象牙塔。周質平談起自己“生在上海,長在臺灣,老在美國”的大半生,使話題自然過渡到生于上海,學于美國,老于臺灣的胡適。
姜:您著有《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譯有《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等書,使讀者清楚看到了胡適與韋蓮司之間的愛情是毋庸置疑的。韋蓮司是虔誠的清教徒,胡適也是很傳統的中國學者,這段情緣既奔放又節制,但表現方式又有所不同,您認為從中反映出了怎樣的中西文化心理?
周:胡適是把婚姻與愛情分開來看的。從胡適的角度來講,他之所以決定與江冬秀結婚,主要還是一個孝道的問題。他覺得自己不能和江冬秀結婚的話,他最不能面對的倒不是江冬秀,而是他的母親,也就是讓他母親怎么和江冬秀交待。他曾在信里說到,他其實不忍傷母親的心。毫無疑問,胡適是中國傳統孝道下的一個犧牲。他對傳統孝道的很多批判其實在他內心深處,是說給他的母親聽,也是說給自己聽的。就像他寫的《我的兒子》那首詩,“比如樹上開花,開落自然結果。那果便是你,那樹便是我。樹本無心結子,我也無恩于你,但是你既來了,我不能不養你教你,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并不是待你的恩誼。將來你長大時,這是我期待于你的,我要你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在胡適眼里,父母跟子女之間并沒有一種恩義的關系在里頭,他這些話更像是說給他已經死了的母親聽的。
很多人在講胡適的婚外關系的時候,都不免從一個道德的角度來判斷,這是一種很廉價的判斷。胡適難能可貴的地方是他始終沒有拋棄江冬秀,有的人會替胡適抱不平,覺得胡適好像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成了舊禮教的犧牲品,這自然有它的邏輯,但同時我們也別忘了胡適的清望,一種道德上的形象,正是舊禮教促成的,正是在那樣的舊禮教下,他才成了一個幾乎像圣人一樣的形象。如果胡適有立功、立言、立德的三不朽的話,倡導白話文是他立功的部分;他的哲學史、文學史是立言的部分;在立德的這一方面,其實是江冬秀幫了大忙的。所以,我覺得一方面胡適固然是受害,另一方面在受害的過程中他也同時受益。由愛情方面講,他后來在美國其實是很寂寞的,除了韋蓮司之外,他還有其他的女友,像哈德曼,羅維茨,這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不認為這是道德有損,值得批評的。
從韋蓮司的角度,我認為也不必看成她是為了胡適一輩子不嫁,犧牲了自己。實際上,對韋蓮司來講,自從她認識胡適以后,其他人都變得索然無味。在看過這么精彩的一個人之后,其他的人再也引不起她的興趣了。當然,在兩個人的關系里面,我覺得韋蓮司有她更不容易的地方。我從頭到尾看了她給胡適的所有信件,里面沒有一句抱怨的話。中國人常常會把一個愛情故事的悲喜分野看在是否終成眷屬上,希望“有情人終成眷屬”,只要不成眷屬,就認為沒有愛情的可能,而韋蓮司完全不這么看,她最了不起的地方恰恰在于雖不成眷屬而仍能一往情深。我覺得這一點是很了不起的。
姜:作為一個不凡的西方知識女性,韋蓮司以她獨特的方式出現在胡適的一生,對他的個性成長、思想成熟乃至后期的文化觀念都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您認為她對胡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周:胡適在美的女朋友不少,能夠在知識上有幫助的只有韋蓮司,其他的都遠遠不及。韋蓮司對胡適的影響,主要是在早期,也就是胡適剛到康奈爾大學的時候,她曾經介紹胡適看很多西方著作,對他有一種知識上的啟發,其中最大的一個啟發是什么呢?結識韋蓮司之前,胡適一直覺得婦女解放的目標是應該把女子塑造成所謂的賢妻良母。結識了韋蓮司之后,他發現婦女解放的最高境界應該是做獨立自主的個人。我覺得韋蓮司對胡適的這個影響是不能低估的。胡適后來回國提倡“易卜生主義”,就有很多韋蓮司的影子在里頭。當然在那個時候,中國婦女想要做易卜生《玩偶之家》里面的娜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國現代女性里有很多娜拉,丁玲可以說是個娜拉,還有胡適的表妹曹佩聲,她們都想走出家庭,做胡適“易卜生主義”的忠實信徒,可是結局并不是想象中的美好。
在胡適離開康奈爾大學之后,他的知識結構已經遠遠超過了韋蓮司,二人之間的影響就完全倒過來了,并發展成非常深厚的友誼。從來往書信就可以看出,他們早期主要談一些知識性的問題,文化、政治、宗教,等等,后來只是談一些生活上的瑣事,但仍可以看出,胡適有很多重大的事情要做決定時,總要去聽取韋蓮司的意見。其中之一就是1938年胡適將要出任駐美大使的時候。關于要不要做美國大使,他曾寫了封信給韋蓮司。韋蓮司給予了他大大的鼓勵,說他是個有外交才能的人,他這樣的人才不應該只屬于中國,應該屬于全世界。我想胡適出任大使是聽從了韋蓮司的意見的。胡適做大使四年期間與韋蓮司有不少書信,信件都是由我第一次把它整理發表出來,韋蓮司的信件多年來一直藏在臺北的胡適紀念館,包括她后來寄給江冬秀的書信。
姜:胡適在剛剛赴美時曾一度對基督教發生興趣,在費城度假的一晚甚至短暫認信了基督,后來又放棄了,他一直在從中國傳統文化視角來打量西方文化,比如認為基督的不爭與老子的無為、墨子的兼愛、非攻,是一個道理,這是否可視為其后來在美宣講中國文化的立足點?胡適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認為胡適在美國宣傳中國文化具有什么樣的特點?
周:胡適基本上是個無神論者,一直到老都說自己是個無神論者。美國有個叫Wesleyan的大學,1939年要授予胡適榮譽博士學位,可是因為那是個教會學校,他拒絕了;1940年再次邀請,胡適才接受。胡適年輕時幾乎成了基督徒的經歷,后來回想起來是很不愉快的。在留學日記里也說自己的感情被戲弄,因為那些現場講道、證道的方式,在他看來是一種非常煽情的過程。在跟韋蓮司的很多通信中,他還以一種嘲諷的態度談論基督徒的懺悔行為。后來胡適到美國來講中國文化,并沒有一種過分要比附西方文化的意思,這里有幾點可以提出來討論:
第一,他常講中國人的“三不朽”,幾次用英文發表中國人思想上的不朽概念。在胡適眼里,如果說中國人在宗教上沒有西方這么強的話,并不是說中國人沒有不朽的概念,而是說不需要通過西方這種宗教的方式來達成。后來他發表《社會的不朽》,副題就是“我的宗教”,指出相對于那些天堂地獄的觀念,我們有求得不朽的更理性的方式,而且更容易理解,而不是透過死后天堂這樣一種概念來達成的,這一點在中國文化里面很重要也是很值得驕傲的地方。另外,胡適有一篇英文文章,很少有人提到,他講到中國自然法的問題。從西方人看來大概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約束中國的皇權,在西方有所謂國家和教會的二分制度,但在中國,只有國家沒有教會,那么,對皇帝的權力有沒有任何制衡與約束呢?胡適認為有,中國人對經典,譬如對四書、孝經的崇尚,已經到了一個自然法的地步,一個無論怎樣暴虐的皇帝,他不敢違反圣人的話。如果有一個臣子,父母死了,要丁憂回鄉,大概皇帝不能說不讓他回去。可以看得出來,中國經典的地位實際上已經達到了可以約束皇權的力量。我覺得這是胡適很有創意的對中國文化的一種解釋,而且在這一點上他也是覺得很值得驕傲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陳獨秀曾經提到,我們現在既不講宗教,也不講美學,新文化到底要枯槁到什么程度?他們其實也是很有意識地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胡適幾次提到不朽和自然法這樣的問題。
在胡適早期博士論文里面大概還有那么一點比附西方文化的影子,比如說認為西方的哲學史是從方法論開始的,所以他也要從方法論方面著手講中國有中國的方法論,但是到后來他就漸漸地把中國的思想史獨立看待了。在海外講中國文化的人不少,但多多少少都帶些民族主義的色彩,我覺得胡適比較能夠把這兩個問題分開,不是說他完全沒有,在他的英文跟中文著作里,在講同一個問題的時候,往往在中文語境里是個缺點,而到了英文語境里面卻成了一個優點。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他講中國的三百年來的女作家。在中文語境里他對這個現象的分析是非常苛刻的,說中國明清兩朝出了不少女詩人、女詞人,實際上還是突出了男人把女人當作玩偶的一面,只不過這個玩偶又有了新的技藝,居然還會做點詩詞,這是了不得的,這和婦女地位的提高不相干;但在英文著作里面,同樣講這樣一件事情的時候,他是非常贊揚的。你不能說他完全沒有民族主義的成分,但這個成分與他人相比,畢竟是很有節制的,尤其是在他那篇《我們對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態度》的英文講稿里面,他對西洋文明的贊揚是很熱烈的。在講到這個問題時,胡適的一個基本取向是要打破中國所謂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的二分法。在中國人認為,西方是物質文明,中國是精神文明,接下來就是精神文明高于物質文明,那么胡適的基本態度是不能把貧窮落后說成是精神文明。貧窮落后只是貧窮落后,里面往往沒有精神,越貧窮的人往往越容易變成物質的奴隸,在這個問題上,胡適的民族主義情緒是非常淡薄的,甚至于沒有。當印度詩人泰戈爾來中國訪問時,胡適給韋蓮司寫信說道,我是不會像泰戈爾那樣,在洋人面前贊揚印度人的精神文明的,我決不走這條路。1927年,他給導師杜威寫過的一封信里,也表示在這一問題上,他比西方人更西方。所以,我覺得胡適是比較有意識地分開談論自己祖國的文化和民族主義的,盡管有時也很難完全剝離,在胡適那里,兩種情緒都有,但相對來講還是持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態度,他始終是用科學的方法來處理上述問題的。
姜:胡適是一個兼濟多重角色的學者,在美期間的社會活動最主要是演講,在美國影響很大。
周:我在《胡適未刊英文遺稿》里把能收集到的胡適演講稿都收集來了,大概占百分之九十,有六十多篇,這個量是很驚人的。我做了中文摘要,但還沒有全部翻譯。胡適在1938年—1942年做駐美大使期間的演講是很重要的,有關中國文化歷史的文章有幾篇,從中可以看出胡適對抗日的貢獻非常大。譬如,1941年在《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這篇演講中,他是那樣苦心孤詣地要把中國的政體在洋人面前描畫成是一種民主,目的是讓美國人對中國多一些支持。他講到在中國的歷史上有種種民主的基礎在里面,比如科舉制度、言官制度,至少在表面上,各個朝代都鼓勵官員向皇帝進諫,比如魏徵在向唐太宗進言的時候,由于唐太宗喜歡玩鳥,就只好把鳥悶死在袖子里頭了。這些無非是為了說明,中國最高的皇權對反對的意見是有一定的容忍的。他講到的幾點,我覺得真的是用心良苦,在1940年前后這樣一個風雨飄搖,受日本欺凌的時候,胡適在美國拼命地講中國文化的優長,盡管他在國內曾經那樣地批評中國文化,到了海外卻盡一切可能說中國絕對是屬于民主制度的。后來美國的輿論,從珍珠港事變后,完全倒向中國,與胡適的作用是分不開的,在外交戰場上胡適的作用是很大的。另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在1949年以后的演講,實際上,在1949年以前,胡適一直希望中國能有一個兩黨的政治,沒有正面公開批評過共產黨,可是1949年以后,尤其是在1957以后,他的演講針對人權和言論自由問題,有過很直接的批評。實際上,胡適所強調的自由和尊嚴是凡人都要的。
姜:胡適在美國學習、工作、生活了26年,您認為關于胡適在美國這段時間的研究是否還存在空白?
周:雖然國內近年來出了很多的胡適研究著作,以及有關胡適的傳記,但關于胡適在美國這一時段的研究還存在很多的空白。胡適在美時期可以分成以下幾個段落:1911年—1917年,是他在美國求學的7年,因為有留學日記和我后來整理的他與韋蓮司的書信,我們對他這一段的生活可以比較完整地了解;1926—1927年,他第二次回來共待了5個月。1927年,在胡適思想轉變上是關鍵的一年,在中國近代史上也是關鍵的一年,比如北伐的成功等。胡適這時在美國的一些演講,學者用的還不是很多;1933年胡適來美有幾次演講,包括在芝加哥大學的講學,期間比較短;1938年—1942年,是他做大使的四年,需要很多政府官方的檔案支持,做的人也還不少,但這一時段的研究需要相當外交史的訓練,比較難做。這期間胡適的檔案發表得不少,包括電文,國內發了一部分,四五年前臺北又發布了一部分。胡適大使卸任以后的1942年—1946年,由于材料比較有限,寫的人很少。這四年胡適住在紐約曼哈頓區東81街104號。1949年—1958年,他也住在這里。這十二三年的時間,胡適到底是怎么生活的?由于胡適在美國的材料都是英文的,國內的學者在處理英文材料上有一定的難度,使這些年的胡適在他的傳記里面呈現得還遠遠不夠。1949年至1958年這7年應該算是迄今為止對胡適在美國26年生活中研究最大的空白點。我把能收集到的胡適信件,盡量都做了處理,大略知道些他的狀況,甚至他每年的收入所得,但做得還很不細致。看了這些材料,你就會覺得,胡適其實是非常清苦的,沒有像傳說的那樣得到了國民黨的資助,把他說成是御用文人也是冤枉的。胡適是一個非常獨立自主而又清高的知識分子。
姜:2008年您的《胡適的情緣與晚境》出版,請問在史料方面有哪些新突破?
周:前面都是舊的,后面有不少新材料,包括最后的一封信。其中羅維茨的信都收在杜威的書信集里面,沒有人用過,后來我都把它整理出來。關于她與胡適的一段情,是余英時先生先在胡適的日記里面發現有一些蛛絲馬跡,然后我在杜威書信里找,得到印證,然后翻譯出來了。1949年以后的胡適書信許多是第一次發表出來。最近,美國有所大學要給我寄來新的胡適信件,據說還包括江冬秀的日記,我正在等。
姜:回顧90年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關于漢字的存廢問題,以及胡適關于“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的提法,您有什么新鮮的感受?
周:我認為,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在所有改革議題里面,最激進、最草率、最不負責任,同時又最受到黨和國家贊揚的一項改革,就是關于語文方面的改革。語文改革從晚清就開始了,1892年盧戇章提出切音拼字,后來王照制定了文字拼音方案。五四新文化運動后的192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里有一種狂熱的學世界語的傾向。世界語是荷蘭人柴門霍夫提出的一種人造語言,叫Esperanto,中國知識分子很為之顛倒瘋狂了一陣子,包括蔡元培、魯迅、錢玄同、陳獨秀,他們個個都認為應該廢漢字,以世界語代替漢字,我把20世紀20年代學世界語的這個熱潮叫做“春夢”。“事如春夢了無痕”,這實際上是一個語言上的烏托邦。其中受這一語言烏托邦影響最大,乃至致死都認為Esperanto 會成為世界語的人是巴金。1987年,巴金到瑞典參加世界語大會成立百年慶典,回來后說,相信世界語終有一天會成為一種人類共同的語言。現在我們再來看巴金的態度,其實是很幼稚的。1930年代,魯迅、瞿秋白、胡愈之都極力主張推行所謂拉丁化,當時還有南拉和北拉之分。魯迅曾經說,“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且介亭雜文·關于新文字——答問》)瞿秋白認為“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頁)1949年以后,毛澤東在《瞿秋白全集》的前面寫過一篇文章,贊揚瞿秋白這樣先進的知識分子。1951年,毛澤東講中國文字要走世界文字拼音的方向。有了這樣的人物在先,所有對中國文字負面的言論都沒有受到過任何批評。然而,我們今天反觀這一問題,會發現漢字不但沒亡,反而比百年前強盛得多了。至少應該回過頭來批評一下這些人的觀點。“五四”時候的知識分子常常有一個因果倒置的看法,好像要救中國,就必須從改革漢字入手,其實應該倒過來,漢字有賴于中國的復興,是中國救漢字,而不是什么以漢字改革來救中國。現在漢語在美國僅次于西班牙語,當然,我們也不能有一種沖昏頭腦的看法,認為中文馬上就會成為世界第三大語言,可是它的地位的確是在提高,事實上,是中國的地位在提高,不是漢字漢語的地位在提高。關于語文改革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出改革的方案一開始是非常激進的,完全低估了漢字的實力、穩定性,和中國語言環境的必然性,中文這樣所謂單音節有聲調的語言,只能采用漢字,漢字有不可取代的功能在里面,它可以解決同音字的問題,方言之間互相不能溝通的問題。這些在現在看來是常識,在當時好像沒有被那些知識分子們意識到。我寫過一篇《為漢字說句公道話》的文章,是強調漢字沒害中國,很多人說漢字落后,最主要的一個罪證就是進不了電腦,這個說法也是倒果為因,是電腦不夠進步,沒有能力處理漢字,而不是漢字不夠進步。改進電腦比改進漢字容易多了。漢字是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經過了多少億萬人的使用,而電腦只是個科技的問題。用黑格爾的話講,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漢字是一種不同的書寫方式,是漢語最好的搭配,它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為什么在廣袤的土地里,在眾多的人口里,在龐雜的方言里,最后出現了這樣一個書寫系統?是因為只有這樣一個書寫系統可以為方言、為眾多的人口服務,而其他的書寫系統不能為這樣龐雜的廣大的人口服務。
關于胡適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覺得很少有人認真地分析一下。首先,“國語的文學”的意思是指它不是方言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精義是說國語是有相當書面的成分的,是文學的,而不是日常生活里面的國語,不是“引車賣漿者流”或北京痞子說的話,是可以入文學作品里頭典雅的國語。從1895年到1920年,白話文經過25年的發展,實際上是一個逐步書面化的過程。我們先看陳獨秀辦的《安徽俗話報》,胡適辦的《競業旬報》中他們早年的文章,還有秋瑾的一些演講,再來看看《新青年》上陳獨秀和胡適的文章,就會清楚地發現,至少陳胡二人的書寫是從極端的口語慢慢走向書面的,到了《新青年》時期就非常書面化了,不是那么口語化的。白話文的書面化而不是口語化,正是白話文能夠在短期之內取代文言文的一個重要原因,它打破了白話與文言之間斷層的現象。所謂“引車賣漿者流”這樣的擔憂也都解決了,這讓人看到,白話并不是那么不堪入文的,也是非常典雅的文字。90年過去后,我們可以印證胡適“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句口號指出來的是個正確的方向,雖然胡適自己有時候也會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他看了魯迅的《阿Q正傳》,曾說要是魯迅當時用紹興話來寫,不知要增加多少生氣,我覺得這話是不負責任的,《阿Q正傳》之所以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著作,正是因為魯迅沒有用紹興話寫,而是用官話國語寫的。也曾經有人對此不以為然,比如非要用蘇州話來寫《海上花列傳》,現在還有誰能看得懂呢?結果張愛玲將之翻譯成國語還不夠,還要再翻譯成英文,這些都足以證明胡適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確實指出了中國語文發展的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