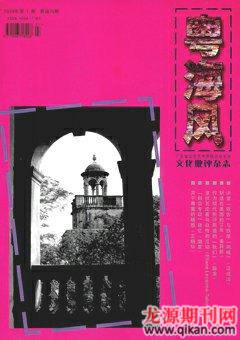“十七年”文學期刊的發(fā)刊詞
王秀濤
文學期刊的“發(fā)刊詞”雖然并不能代表實際文學事實,但它是對期刊的性質(zhì)、宗旨、要求、規(guī)范的聲明,“凡是一種報紙出世,必定有一種標明主義和趨向的話,叫發(fā)刊詞”[1]。“發(fā)刊詞”更為直接地顯示了文學期刊的操作規(guī)范和程序,對作家的創(chuàng)作起著更為直接和規(guī)范以及引導作用。因此,“發(fā)刊詞”是透析當時文學生態(tài)及其變化的重要的歷史文獻。
一、自我形象與期刊定位
“發(fā)刊詞”是確立自我形象的重要方式。這種自我形象不但影響著傳播者“在決定如何組織和控制他的信息時”,“如何進行選擇和制作”,[2]而且也是傳播者尋求社會生存資源,并確認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手段。只有自身定位與社會需求相一致,并取得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認可,傳播者才能有足夠的社會生存空間。由于特殊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1949年后的文學期刊都迫不及待地對自我形象進行確認,絕大多數(shù)的文學期刊在發(fā)刊詞中都一再強調(diào)、強化自身的機關(guān)刊物身份。由茅盾執(zhí)筆的《人民文學》的發(fā)刊詞中,開篇就是“作為全國文協(xié)的機關(guān)刊物,本刊的編輯方針當然要遵循全國文協(xié)章程中所規(guī)定的我們的集團的任務”,而耐人尋味的是在此篇發(fā)刊詞的最后,茅盾把這句論述重新強調(diào)了一次。如果聯(lián)系此時的文學格局,不難看出這種重復用心,既強調(diào)刊物對代表國家意志的全國文協(xié)章程的絕對服從,從而確認自身的合法地位,也是在強化自身作為最高級別的文學刊物的權(quán)威地位。
中國共產(chǎn)黨初期的文化規(guī)劃與政治、經(jīng)濟建設(shè)是一體化的,實行充分的國有化是其根本的目標。得益于左翼和延安時期的文學建設(shè)經(jīng)驗,尤其是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作為根本的指導政策的確立,中國共產(chǎn)黨的文學規(guī)劃得以快速實施,私人出版機構(gòu)和同仁刊物被逐步取消,全面的國有化使得國有體制之外的文學活動喪失了經(jīng)濟基礎(chǔ)和政治合法地位。而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確立了以各級“文聯(lián)”和“作協(xié)”作為推行黨的文藝政策的領(lǐng)導機構(gòu),從而以自上而下的科層化管理把全國的文藝工作者納入統(tǒng)一的文學機制當中。一切文學活動包括文學期刊的發(fā)行都被納入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操控之中。機關(guān)刊物作為文學期刊最為合法的存在形式,一再強調(diào)其正統(tǒng)身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人民文學》作為最高級別的文學刊物,它對自身全國文協(xié)機關(guān)刊物身份的強調(diào),就是以不可質(zhì)疑的權(quán)威性來確立自身的示范性,也就為下一級別的文學刊物的創(chuàng)建樹立了標本。許多地方性刊物也同樣強調(diào)自身的期刊身份,如《山東文藝》的發(fā)刊詞強調(diào)它是“作為山東文聯(lián)籌委會的戰(zhàn)斗號角而創(chuàng)刊了”;《上海戲劇》在發(fā)刊詞中也表明自己是“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上海分會的機關(guān)刊物”。
那些沒有明確表明其機關(guān)刊物身份的文學期刊,也在其發(fā)刊詞當中以對黨的文學規(guī)劃積極認同姿態(tài)和為黨的事業(yè)服務的積極態(tài)度來確認自身的合法地位,這也是文學期刊對自我形象的間接確認。這些文學期刊都是以文學媒介的服務中介角色來迎合中國共產(chǎn)黨確立文化領(lǐng)導權(quán)的目的,從屬于施拉姆所謂的“蘇維埃或社會主義模式”。文學期刊的發(fā)刊詞中包含了辦刊的終極目的和對來稿的要求,也是對這種媒介模式的確證。茅盾在《人民文學》發(fā)刊詞中提出全國文協(xié)的六大任務同樣是《人民文學》辦刊的最終指向。作為黨的意志在文學領(lǐng)域的體現(xiàn),六大任務也為《人民文學》確立了為國家政治服務的最高目的。茅盾在“發(fā)刊詞”中對文學工作者提出的四點要求,其終極要求就是“為建設(shè)新民主主義的文藝而奮斗”。《河北文藝》表示“它要為河北省人民的建設(shè)事業(yè)服務;為河北省群眾的文藝運動服務……用文藝的方法,來發(fā)揚河北省廣大人民在恢復和發(fā)展生產(chǎn)及各種建設(shè)中的新英雄主義,反映人民新的生活和新的思想;藉以啟發(fā)人民的政治覺悟,鼓勵人民的勞動生產(chǎn)熱情”。《山西文藝》希望“能夠在偉大的革命發(fā)展中,在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shè)中起一點作用,并逐漸求得自己的充實與進步”。《川西文藝》表示“我們要在人民勝利的基礎(chǔ)上,展開創(chuàng)作;我們要在人民事業(yè)的發(fā)展之中,加強創(chuàng)作!”《火花》則期待著“足以反映國家建設(shè)和山西人民在國家建設(shè)中所表現(xiàn)的沸騰的社會主義作品逐步出現(xiàn)!”《長江戲劇》則把“在黨的領(lǐng)導下堅持文藝為工農(nóng)兵服務、為政治為生產(chǎn)服務以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作為自己的任務。從中央級別到地方級別的刊物,都自覺承擔國家機構(gòu)所擔負的任務,即充分利用其作為媒介的特殊角色,以文學“守門人”和監(jiān)察者的角色,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引導和規(guī)范,從而實現(xiàn)其政治宣傳和教化的目的,也確認其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的隱形形象。《人民文學》以“……都歡迎來罷”的方式表達對符合規(guī)范的文學作品的認可;《火花》“歡迎那種新鮮獨創(chuàng)的東西。歡迎那種對人民生活不做機械和片面的了解的東西”……其他文學期刊的發(fā)刊詞都以相同的方式行使文學“守門人”的媒介角色。
機關(guān)刊物、媒介角色、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三種角色身份形象是統(tǒng)一的,其機關(guān)刊物的自我形象的定位,最終指向通過媒介角色行使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的職能,是“針對個人進行體制規(guī)訓與合法化生產(chǎn)的領(lǐng)地”,是“貌似溫和卻彌漫著神秘暴力的社會調(diào)控工具”。[3]
二、話語復制與辦刊模式的趨同
1949年后的文學期刊發(fā)刊詞存在著明顯的話語復制現(xiàn)象,除了語言風格的差異,“發(fā)刊詞”的內(nèi)容都極其相似:概括政治形式、闡明期刊的宗旨與任務,提出文學創(chuàng)作要求等,而且,其間充斥領(lǐng)導人權(quán)威言論和時下最流行的政治語言。而且,“發(fā)刊詞”所闡明的宗旨與任務以及對文學的要求,其最終的政治指向都是一致的,雖然,由于政治形勢的變化,以及撰寫人的不同,表述形式上存在差異。除了內(nèi)容復制外,這些發(fā)刊詞都充斥著濃重的政治說教氣味,都以黨的文藝政策的代言人自居。“發(fā)刊詞”的話語趨同現(xiàn)象也是辦刊模式重疊的直接反映。
從文學創(chuàng)作要求的角度,基本可以概括出建國初期文學期刊“發(fā)刊詞”中的幾點內(nèi)容:
1、文學體裁與形式。“詩歌、小說 、劇本、報道、雜文;外國文學、民間文學、兒童文學。
2、文學作品的內(nèi)容:反映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的;反映新中國建設(shè)和發(fā)展進程的;描寫新的英雄人物的;反映人民新生活和新思想的。
3、作品要求:為工農(nóng)兵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易于接受的。
4、直接目的:啟發(fā)人民的政治覺悟、教育人民群眾。
5、作者來源:在依賴老作家的同時,積極培育文學新人尤其是工農(nóng)兵群眾作家。
“一般說來,‘中央一級的(中國文聯(lián)、作協(xié)的刊物)具有最高的權(quán)威性,次一等的是省和直轄市的刊物,依此類推。后者往往是‘中央一級的回聲,做出的回應。重要問題的提出,結(jié)論的形成,由前者承擔。”[4]低等級的刊物基本參照上一級的文學刊物的辦刊模式,因此,“發(fā)刊詞”的話語復制也就在所難免。這種高度一致性的辦刊傾向,與“蘇維埃和社會主義模式”的媒介體系有關(guān),在這種體系中的媒介任務與社會政治任務高度一致,強權(quán)統(tǒng)治必然導致刊物被統(tǒng)一化。中國共產(chǎn)黨對文化進行全面控制,逐步把傳播體系納入國有,文學期刊只存在機關(guān)刊物這一唯一合法的形式,文學期刊的根本職責體現(xiàn)為作為黨的“喉舌”存在,其根本的辦刊任務和辦刊思路也被約束在極其狹窄而又極其確定的范圍。同時,黨對文化的領(lǐng)導采取的是科層化的管理方式,國家文聯(lián)、作協(xié)到省市各地的文聯(lián)、作協(xié)和各級黨的文化官員把作家、刊物納入層層管理機制中,縱向的管理模式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級制度,也造成了文學期刊的等級制以及文學期刊的層層復制。
發(fā)刊詞的話語趨同現(xiàn)象也實踐了大眾傳播所具有的“議題設(shè)置”功能,“大眾媒介只要對一些問題注意,對其他問題忽視,就可影響公眾輿論。人們傾向于了解大眾媒介注意的那些問題,并采用其給各個問題確定的優(yōu)先順序”。[5]文學期刊發(fā)刊詞的話語的重復闡釋使黨的文藝政策成為唯一議題,并不斷得到強化,從而對作家和讀者的創(chuàng)作和閱讀傾向變得單一化,并以一種無意識取得對黨的文化領(lǐng)導權(quán)的認可和追隨。符合文藝政策的文學創(chuàng)作規(guī)范在不斷的重復中成為強勢的話語壟斷,成為作家不可質(zhì)疑的創(chuàng)作規(guī)則。當各種刊物都是一種聲音的時候,作家已經(jīng)喪失了選擇的可能性,只有按照此種規(guī)范創(chuàng)作才有發(fā)表的機會。期刊一體化和國家統(tǒng)管狀態(tài),使刊物都沒有自己的特色,雷同的辦刊模式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競爭機制。文學期刊的自身特色也會被視為越級、不遵守政治規(guī)范的表現(xiàn),如《探求者》、《星星》等期刊的命運。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學期刊的單一化以及文學生態(tài)的失衡。因此,“發(fā)刊詞”的話語復制現(xiàn)象,不過是強制推行一種意識形態(tài)觀念,并以壟斷性的重復掩蓋其話語霸權(quán)性質(zhì),并釀成一種天然的合法性的假象。
三、文藝政策的風向標
隨著文藝政策和政治氛圍的變化,1949年后的文學期刊發(fā)刊詞也會在一定的限度內(nèi)發(fā)生變化。根據(jù)發(fā)刊詞的內(nèi)容可以窺見某一段時間的文學生存環(huán)境,以及最新的文藝政策的動向。“那一時代新創(chuàng)辦人文、學術(shù)和文藝刊物,在發(fā)刊詞上,都無一例外地要寫上最流行的政治語言,以表達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認同。”[6]“發(fā)刊詞”成為對文藝政策的轉(zhuǎn)述和闡釋。另一方面,50年代的文學環(huán)境處于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在政治氛圍較為融洽、形式緩和的時候,文學期刊的發(fā)刊詞一般比較輕松,更多地強調(diào)文學的內(nèi)在要求;相反,在階級斗爭比較激烈,形式緊張的年份,“發(fā)刊詞”都較為謹慎,表現(xiàn)出積極配合政治斗爭,嚴格遵循黨的文藝政策的政治態(tài)度,以配合黨的文學運動。這種話語方式的變化也是文學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劣與寬松的體現(xiàn)。
以下是不同年份文學期刊發(fā)刊詞的部分內(nèi)容,其中的變化是了解當時最新的文藝政策及其風向變幻的一個窗口:
例如,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協(xié)開幕詞里講到:“隨著經(jīng)濟建設(shè)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的將要出現(xiàn)一個文化建設(shè)的高潮。”七月間,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文學藝術(shù)工作者大會,這個勝利的團結(jié)的大會,表明了實踐毛主席文藝方針的決心:文藝要為工農(nóng)兵服務。并且一致認為:普及仍是第一(不要忘記農(nóng)村),在普及的基礎(chǔ)上求得創(chuàng)作質(zhì)量及文藝運動的逐步提高。(《河北文藝》,1949年11月)
我們一定也盡力使文字通俗化,大眾化,以至爭取做到通過干部和知識分子的朗誦,也可使不能閱讀的工農(nóng)兵大眾聽得懂。(《山東文藝》1950年6月)
事實證明,我們的文學藝術(shù)必須善于表現(xiàn)生活的矛盾和沖突,必須要嚴肅地反映新舊思想的斗爭,沒有矛盾和沖突,就不可能創(chuàng)造出典型任務的性格;沒有新舊思想的斗爭,文學藝術(shù)作品就會平庸、乏味。(《江蘇文藝》,1953年1月)
胡風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居。其實,他的這種“理論”正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胡風盡管愛玩弄些革命導師的詞句,但是,他的“理論”的基本精神確是反人民的。同是腐朽時期的資產(chǎn)階級文藝理論的一種變形物。(《民間文學》,1955年4月)
而為了使文化科學事業(yè)得到真正的繁榮,黨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來。《新港》作為一個文學刊物,正是在這個英明方針下誕生的。(《新港》,1956年7月)
要辦好這樣一個刊物,重要的是認真貫徹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政策。……一定為文藝的繁榮掃除一切清規(guī)戒律和各種人為的阻礙,推動一切積極要素為文藝的繁榮進行努力。(《北方》,1956年10月)
善于歌頌,勇于批評,這是我們創(chuàng)辦這個刊物的主要目標之一。“死樣活氣”的八股文章,不被讀者所歡迎,不容說的了。(《東海》,1956年10月)
還必須看到在戲劇工作中兩條道路的斗爭還沒有結(jié)束,資產(chǎn)階級的世界觀及其文學藝術(shù)思想,或多或少地殘存在人們的頭腦中,因之,尚需與之斗爭,進行反復的批判,刊物理論工作必須要承擔起這一戰(zhàn)斗任務。(《長江戲劇》,1959年6月)
1949年、50年代初期和1956年是文學期刊創(chuàng)刊的兩個高峰期,從它們的“發(fā)刊詞”的重心和話語風格的區(qū)別能明顯覺察出文學環(huán)境的緊張與寬松。建國之初的文學期刊,其發(fā)刊詞基本以1942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第一次文代會的會議精神作為指導思想,普及與提高、為工農(nóng)兵服務等文藝政策成為發(fā)刊詞的話語中心。而1956年文藝政策的寬松在發(fā)刊詞中就表現(xiàn)為,要求清除清規(guī)戒律,強調(diào)文學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成為發(fā)刊詞中頻率最高的主導性話語。1956年創(chuàng)刊的文學期刊的刊名也大多不再采用《××文藝》、《××文學》,而是采用《萌芽》、《新港》、《火花》、《北方》、《東海》等富有文學性的刊名,這同樣反映了1956年文學期刊發(fā)生的變化,這至少從形式上打破了原來文學期刊之間的地域分割,淡化了文學期刊以行政區(qū)劃命名所帶來的政治色彩。而事實上,1956年中國作協(xié)多次召開有關(guān)文學期刊的會議,11月21日到12月1日,在北京召開了有47個編輯部的代表參加的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這次會議集中討論的問題,是文學期刊如何貫徹執(zhí)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推動文學事業(yè)的發(fā)展和繁榮。“大膽放手地實行這一方針,敢于發(fā)表不同意見、不同觀點的文章,敢于發(fā)表不同風格、不同題材、不同形式的作品”。并且特別提出,尖銳地批評生活中的缺點的文章,“只要不是惡意的誹謗,就應該發(fā)表”——這是會議的普遍看法。圍繞這一中心問題,會上提出了幾項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張,一是主張從第二年1月開始,取消“機關(guān)刊物”這個頭銜,各刊物之間,去掉那種不成文的指導或領(lǐng)導的關(guān)系,而平等地展開競賽。二是刊物應有獨創(chuàng)性,有自己的特點。三是刊物的企業(yè)化管理和經(jīng)費實行“定期自給”,這是為了促進自由競賽,提高刊物質(zhì)量。[7]因此,發(fā)刊詞的內(nèi)容作為最新的文藝政策的轉(zhuǎn)述和再闡釋,并把它作為辦刊的指導思想,也就會在具體的辦刊過程中把它由潛在的“文學事實”變成真正的文學事實。透過“發(fā)刊詞”,可以也能預測到當時的文學創(chuàng)作情況。因此,“發(fā)刊詞”也是文學史的書寫者之一。
由于50年代黨的文藝政策處于不斷調(diào)整之中,形勢也時緊時松,在文學批判運動的間歇期創(chuàng)刊的文學期刊面臨的壓力相對小一些,其“發(fā)刊詞”風格也就輕松活潑一些,比如1956年到1957年期間。1957年3月創(chuàng)刊的《漓江》的發(fā)刊詞是以詩歌的形式寫成的,“刊物是苗圃,也是花園”,“刊物本身也是一朵花”,“每個花園應有它自己的特色”,“在花園里培植的總說是‘花,這是共通的;在花園里要有各種各樣的花,這是不同的。”同樣是同一時間創(chuàng)刊的《綠洲》的發(fā)刊詞,也用詩化的語言,具有抒情散文般意境。“這里有綠樹,這里有綠茵。率濤,率浪,像開拓者一樣堅忍不拔的綠色的生命。《綠洲》,正是綠色生命的一幅投影,強烈展現(xiàn)進取精神的一塊領(lǐng)地。”這都是用抒情的文學話語闡明刊物的宗旨和要求,其中雖然也包含了對當時文藝政策的闡釋,但話語方式是輕松的,透露出文學工作者的信心和喜悅,也預示著文學進入一種“常態(tài)”。相反,1954—1955年頻繁的批判運動造就了形勢的緊張,在這期間創(chuàng)刊的文學期刊就顯得小心翼翼,其話語局限在黨的政策范圍內(nèi),而不敢有自己的主張,而且在“發(fā)刊詞”中也追隨形勢,對被批判對象進行批判以表明自己的立場。1955年4月創(chuàng)刊的《民間文學》就在發(fā)刊詞中從民間文學的角度對胡風進行批判:胡風在文藝思想上,向來是瞧不起祖國偉大的古典作品和人民口頭創(chuàng)作的。……這些“理論”,實質(zhì)上就是否定過去人民的創(chuàng)造力,就是抹煞他們的進步意識和藝術(shù)成就。對于具體的作用就是堵塞我們作家寶貴的藝術(shù)富源,要割斷現(xiàn)在人民文化和歷史人民進步傳統(tǒng)的關(guān)系,簡單地說,就是要使具體的文化、藝術(shù)脫離人民和貧乏化。因此,“發(fā)刊詞”是文學環(huán)境的一面鏡子,其話語方式的變化,是文藝政策的風向標,也是文學生存環(huán)境優(yōu)劣的指示燈。
“發(fā)刊詞”作為一種歷史文獻的重要價值,包含了創(chuàng)刊時期最流行的文藝政策,也反映了當時文學生存環(huán)境以及文學期刊操作模式的大致情況。而其話語方式背后包含的深層含義,也是透析當時文學操作規(guī)范的一個途徑。“發(fā)刊詞”本身也參與了文學生產(chǎn)的歷史,也構(gòu)成了還原建國初期文學場景的一個側(cè)影,成為后人進入文學史的途徑之一。
[1]玄廬:星期評論發(fā)刊詞[M]∥張靜廬:《中國現(xiàn)代出版史料甲編》,中華書局1954年,第24頁。
[2][5][英]丹尼斯·麥奎爾[瑞典]斯文·溫德爾:《大眾傳播模式論》[M],祝建華 武偉譯,上海譯文出社1997年,第54頁。
[3]趙一凡等主編:《西方文論關(guān)鍵詞》[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773頁。
[4]洪子誠:《問題與方法》[M],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第208頁。
[6]孟繁華:《眾神狂歡——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化現(xiàn)象》[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第186頁。
[7] 洪子誠:《百花時代》[M],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