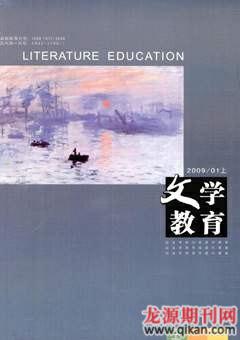一個罪犯的心理自白
張惠雯的這篇小說并不像它的題目那樣浪漫,《月圓之夜》實際上是講述的一個犯罪故事,主人公兩次行兇碰巧都是在“月圓之夜”,而在那種浪漫幽深的意境中卻透露出死亡的氣息。一切看似“都是月亮惹的禍”,其實還有著比“月亮”更復雜難言的非理性因素。不僅主人公的犯罪動機是一個謎,甚至他的整個人生都充滿了不可破譯的宿命。不僅主人公“當局者迷”,而且作者和讀者也無法做到“旁觀者清”。
其實每個時代、每個國家都會有罪犯。罪犯是人類社會演化過程中一種必然會出現的邊緣群體。在政治家和法學家的眼中,罪犯是對正常社會規范的越規犯禁者,需要加以監禁和懲罰,而在文學家和哲學家的心中,“罪犯”的存在正暗示了我們正常社會秩序里人類精神心理中潛伏的另一種沖動和可能,“罪犯”不能簡單地被理解為“非人”,他們是“常人”的另一個隱形自我的外在確證。也許正因如此,自古以來文學家對罪犯的命運非常關注,僅就西方文學傳統而言,古希臘三大悲劇全都是關于“罪犯”的故事。《被縛的普羅米修斯》講述了一個“政治犯”的故事,《俄狄浦斯王》講述了一個“殺父娶母”而后自殘的雙重犯罪故事,而《美狄亞》則講述了一個為了向夫復仇而殺子的女人的故事。雖然古今文學家對“罪犯”似乎情有獨鐘,但不能因此誤解文學家無情,實際上,真正的文學家是這個世界上最溫情的人,只有文學家(包括少數哲學家)才會去撫慰“罪犯”這種被主流社會拋棄的邊緣人的心靈,文學家的無情正是他們有情的表現。一個作家寫犯罪的故事,只要不是寫那種渲染兇殺的通俗偵破探案小說,而是把筆觸對準“罪犯”的精神世界和深層心理,那他(她)就堅守了一個文學家的良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張惠雯的《月圓之夜》贏得了讀者的尊重和理解。
小說以限制性的第一人稱展開敘述,“我”是一個被監禁的罪犯,在獄中“我”回想自己的人生之旅和犯罪軌跡,覺得處處充滿了玄機和迷惑。“我”的敘述是舒緩的,沉滯的,帶有常人難以理解的冷靜,有時候仿佛“我”敘述的不是一個關于自己的故事,而是講述的一個陌生人的遭遇,這種冷靜近乎冷漠,散發出絕望的氣息。由于選擇了第一人稱的限制性敘述,所以“我”無法像先知先覺的非限制性敘述者那樣掌握著故事的知情權和解釋權,恰恰相反,“我”對自己的命運和犯罪動機充滿了困惑,無語言表且無法理喻,這使得整個小說籠罩著一層神秘主義的面紗。實際上,這篇小說不僅通過選擇主人公來做敘述者,使這篇小說成了一個罪犯的心理自白,而且藉此把作者降到了和讀者同樣的位置,他們同樣對主人公的犯罪和命運之謎充滿了疑惑,換句話說,作者和讀者都是主人公或敘述者的傾聽者,這似乎是對作者話語權力的一種剝奪或放棄,其實體現了作者的藝術選擇和非理性主義的現代人生哲學理念。在這個世界上,人的命運和非理性沖動其實是無法用我們慣常所接受的理性主義思維來解釋的。理性主義視閾中的因果定律在豐富復雜充滿偶然性的人生命運中有時候并不具備必然的闡釋能力。所以在這樣一篇犯罪小說中,作者與其去充當那種全知全能的敘述者,對主人公的犯罪動機和人生宿命做出貌似合理其實牽強的解釋,不如選擇目前這種第一人稱的限制性敘述者,讓人物和作者乃至讀者一并陷入非理性的人生迷惘中。至于對犯罪心理和人生宿命的解釋權,一切都交給了讀者,這是對讀者也是對人物的尊重。
小說中的“我”入獄前是一個假煙販子,時刻都有人贓俱獲的危險,長期過著“隱身人”的生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呆著旅館房間里等人取貨,燈光對于他來說比陽光更為熟悉。等待的日子總是無聊、空虛和孤獨的,而他的等待還充滿了恐懼。就在這種難熬的等待中,他不經意地卷入了一場殺人案,而且一不小心成了案件的主犯。回想起來,仿佛旅館的老板娘從一開始就盯上了他,他一步步地淪為了她的獵物或棋子。他毫無覺察地充當了她的假情人,又在無意和恐懼中殺死了她的丈夫,事實上解救了她和她的真情人,而自己卻成了殺人的逃犯。在長年累月的逃亡中,他完全生活在殺人的噩夢里不能自拔,他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自己殺死了那個陌生的男人,他陷入了一個永遠無法確證的人生謎團。這種無法解脫的痛苦讓他不堪重負,他在惡性循環中越陷越深,終于再度行兇,淪落法網。獄中的他從瘋狂回歸冷靜,在無休止的思索中終于明白,原來自己陷入的是一個被神秘預設的命運圈套,他在劫難逃!
李遇春,評論家,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新文學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