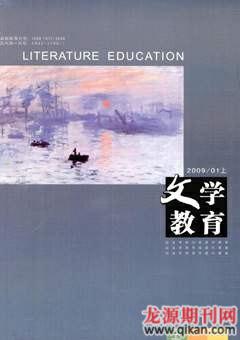重讀《三門峽——梳妝臺(tái)》
作為中國當(dāng)代杰出詩人、豪放派代表人物,賀敬之詩歌創(chuàng)作的數(shù)量雖云不豐,但名篇倒是不少,《回延安》《放聲歌唱》《三門峽——梳妝臺(tái)》《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車的窗口》《雷鋒之歌》等均為譽(yù)飛遐邇的杰作,其中《三門峽——梳妝臺(tái)》,因其墨色壯麗意格獨(dú)標(biāo)而常為人引稱。遺憾的是,對這首詩的解讀,許多文章還存在著隔的通病。本文投以藥石,試圖對詩歌文本作若干疏通,以正視聽。
解讀這首詩的一個(gè)基本前提是段落的劃分。本詩究竟以劃分幾個(gè)部分為宜?
各家?guī)缀跏潜娍谝晦o地篤定:寫三門峽往昔的1—4節(jié)為一部分,寫現(xiàn)狀和未來的5—9節(jié)為一部分。我卻以為,應(yīng)以第6節(jié)為切線,分全篇為兩部分:歷史世象部分(1—6節(jié),含往昔與現(xiàn)狀);理想憧憬部分(7—9節(jié),即遠(yuǎn)眺未來)。剴切而論,前者反映了以內(nèi)容色彩為標(biāo)志的劃分思路,其受一般理性的規(guī)約是明顯的。讓我們還是回到“這一個(gè)”具體文本上來,因?yàn)榻鉀Q問題的鑰匙秘藏其中,它主要由作品的藝術(shù)手法體現(xiàn)出來。
我發(fā)現(xiàn),雖然人們無一例外地指出了詩中蟬聯(lián)的修辭特色,卻又無一例外地就此打住了。為什么不追問下去呢?殊知某個(gè)特定的、復(fù)呈的修辭手段之于主題結(jié)構(gòu),往往總負(fù)有特殊的使命。誠然,這首詩特有氣勢。然氣勢并非散漫不羈,而是率由意脈運(yùn)載著“氣”,在掀蕩和起伏中造成“勢”,以作用于讀者的心理律動(dòng)。凡意脈又總會(huì)有詩人“故意”或無意傾露的若干端點(diǎn),本詩的蟬聯(lián)部位即是這種端點(diǎn)的顯示。我們知道,蟬聯(lián)一般表現(xiàn)為上句或上段末尾幾字,作為下句或下段開頭的幾字,首尾相咬銜枚而下,遂成奔暢氣勢。作品1—6節(jié)就盡在一個(gè)蟬聯(lián)區(qū)內(nèi),7—9節(jié)則構(gòu)成了又一個(gè)蟬聯(lián)地帶:一為歷史世象,一為理想憧憬。這既反映了詩人對作品內(nèi)容的理性態(tài)度,也透露了詩人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生理心理脈沖,即全詩一氣呵成,只是在對歷史事實(shí)的描抒結(jié)束后,適時(shí)中輟蟬聯(lián),換了一次較長的氣,繼而氣韻益足地將詩情推向峰巔。不如此把握和區(qū)劃文本,不僅會(huì)割斷意脈,更無緣窺得名詩結(jié)構(gòu)的妙諦。結(jié)構(gòu)決定功能。匠心獨(dú)運(yùn)的審美結(jié)構(gòu),當(dāng)然會(huì)產(chǎn)生不同凡響的審美效應(yīng)。
追問之二:這首詩為何不從眼前景寫起?
黃河之水天上來。它馳過潼關(guān),東流百公里許,便抵達(dá)豫地三門峽。在這里,鬼島、神島、人門半島兀立河中,河水便從這三島之間嘶嘯而下,頓成三門而沽禍千載。1958年詩人襟帶風(fēng)濤,觀瞻了正在興建中的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面對滔滔大作的黃河和建設(shè)工地的壯闊場景,他撫今思昔,感奮不已,現(xiàn)場感招邀靈感沛然而降,激情播揚(yáng)詩情喧豗傾出。然而,詩人是深刻的,他沒有浮面地掠取眼前的表象,而是沉宏而凝煉地把自己的見聞和感受加以融鑄與升華。從中讀者始則感受到歷史的深度,繼而置身于現(xiàn)實(shí)的恢宏,旋即登臨時(shí)代的高處,對世罕其匹的雄偉工程進(jìn)行鳥瞰,以激情和理想釀出真切瑰麗的浪漫主義境界。這就是為什么詩作既從現(xiàn)實(shí)出發(fā),又不停留在事物平面,雖產(chǎn)生于詩風(fēng)浮泛的年代而又精湛不磨的又一奧秘。
追問之三:詩人為什么選取梳妝臺(tái)與三門峽并寫?
三門峽怪石嶙峋,山水險(xiǎn)要。在這里,一石一溝都被冠以誘人的名字,如米湯溝、娘娘河、煉丹爐、梳妝臺(tái)等等,每個(gè)名字中都包含有美麗而詭奇的神話故事。眾象紛呈,詩人卻從中獨(dú)拈“梳妝臺(tái)”,并將它與“三門峽”組合配對,以一道波折號相與連接,可謂機(jī)鋒獨(dú)躍,用心深焉。以藝術(shù)價(jià)值論,這并不意味著后者對前者的附麗和注腳,而是置二者于平等地位;若自思維角度揣想,它們組合配對誰也離不了誰。也許詩人宿構(gòu)之初,從眾景點(diǎn)中發(fā)現(xiàn)了梳妝臺(tái),于是連鎖式地有了相對應(yīng)形象“黃河女兒”的誕生。這樣便使黃河的擬人化有了依托,而梳妝臺(tái)作為道具也有了背景。沒有“臺(tái)”的狀寫,“門”(三門峽和黃河的總指代)也就散泛無奇,不可能創(chuàng)造出如許鮮明動(dòng)人的“黃河女兒”的抒情形象;沒有“門”的描抒,“臺(tái)”的形象勢必顯得纖巧單薄。它們之間是一種相互補(bǔ)足、相互加強(qiáng)的互輔關(guān)系。詩人以這兩個(gè)形象作為端點(diǎn),拋出雙曲線構(gòu)思,從而獲致清妙而厚重、平易而獨(dú)特的審美效果。這是名詩的又一奧妙所在。
追問之四:是哪些因素促成詩人做出浪漫主義手法的選擇?
革命浪漫主義氣韻,在這首詩里有著強(qiáng)烈濃郁的存在。詩人采用什么創(chuàng)作方法,首先取決于他要表達(dá)的主題題材這一文本的內(nèi)在要求。追溯三門峽深痛巨創(chuàng)的往昔,反映新中國主人對它的改造,尤其是暢想其幸福妙曼的未來,實(shí)在是歷時(shí)久遠(yuǎn)、積淀豐富、場面宏闊、空前絕后的“重頭戲”。對此,革命浪漫主義所具有的開放、鮮明、激越等項(xiàng)功能正堪負(fù)載。其次,也還與抒情主體體察到的抒情客體有關(guān)。詩人“望”三門峽——梳妝臺(tái)之日,建設(shè)工程正值草創(chuàng)階段,舊貌仍斑斑可考。詩人的審美理想是要運(yùn)用夸張、想象、幻想的形式,將觀照對象“反映得神彩煥發(fā),給人以千里之目”,“有震撼人心的雷霆萬鈞的力量”(賀敬之語)。開篇下一“望”字,便將讀者與詩人一并托上現(xiàn)實(shí)的地基,在堅(jiān)實(shí)地完成必要的陳述后,進(jìn)而將所感通過想象之途,形象鷹揚(yáng)地與理想接通。于是,黃河上的這一門一臺(tái),在一種詩意的扭結(jié)中,成為中華民族世世代代意愿的象征結(jié)晶,可謂立意高簡,氣勢橫絕,盎揚(yáng)起浪漫主義的雄健氣息。從中亦可看到,詩人對以李白為幟識的我國浪漫主義傳統(tǒng)詩歌精神的有力的承傳與發(fā)展,從而創(chuàng)辟出一派新美的大境界。
追問之五:詩人何以提煉民歌和古典詩詞的表現(xiàn)形式加以操作?十分地考究于意境的創(chuàng)造和語言的錘煉,是這首詩在藝術(shù)上的一個(gè)顯著特色。“古典加民歌”等長處,如鹽入水地涵詠于作者賀敬之的全部創(chuàng)作中,但如此形式整飭的篇什似還鮮見。單說建行一項(xiàng),它與稍后的四川詩人陸棨的名詩《重返楊柳村》一道,對促進(jìn)當(dāng)代詩歌語言形式的民族化群眾化發(fā)生過積極影響。筆者以為,詩人的上述選擇,同這一時(shí)期關(guān)于詩歌形式的理論倡導(dǎo)有關(guān),同盛極一時(shí)的民歌運(yùn)動(dòng)的某些積極影響相涉;也更因?yàn)椋S河乃中華民族的象征,表現(xiàn)對象內(nèi)在地要求或規(guī)范著詩風(fēng)的走向。反轉(zhuǎn)來,謠曲式的詩風(fēng)用來抒唱民族形象,正是高度的適應(yīng)與契合。民族土壤開出屬于自己的名詩之花。
趙國泰,詩評家,現(xiàn)居湖北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