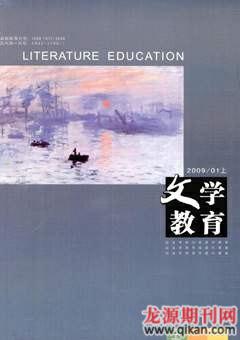談《詩經》之“興”義
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無論是在形式體裁、語言技巧,還是在藝術形象和表現手法上,都顯示出在藝術上的巨大成就。其中賦、比、興手法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征的重要標志,也開啟了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關于賦、比、興的含義,歷來學者說法眾多,而尤以“興”義最為復雜,這也給《詩經》作品的賞鑒增添了無窮的韻味。這里,筆者也想結合平時誦讀《詩經》的體會,談談對“興”義的一點認識。
要正確領會“興”義,我們有必要追根溯源,先去弄清楚《詩經》作者為什么要運用“興”這種手法。我們知道,人們在進行文學創作或交際時,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把思想內容表達得生動形象,使之具有更強的說服力和感召力。這樣,平直枯燥的表白就難以勝任了。于是人們就需要對作品進行藝術的加工,《詩經》時代的人大概也是如此,也就有了或賦之、或比之、或興之等表現手法的運用。再者,從《詩經》作品的來源上說,它們首先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春秋公羊傳》)的情感抒發或世事記錄。這樣,民歌作者的表情達意就往往與他們所從事的生產生活、眼前的風光景物有著一種密切的聯系,也就容易從眼前之景、身邊之事展開聯想,從而歌詠對象、抒發情感。這或許就是“興”這種手法產生的主要原因吧。所以,“興”的手法,往往先用鮮明的形象抒情發端,而這些形象絕大多數就取材于周圍的自然世界,詩人通過觀察和體驗,從形態、聲音、色彩以及動態等多方面對自然進行感受,然后再以富有韻律的詩句表現出來,有的非常生動或樸素,充滿了濃郁的生活氣息;有些則具有較高層次的藝術感染力。
如《周南·葛覃》首章“葛之覃兮,施于谷中,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即描繪了一幅葛藤枝繁葉茂、小鳥歡快鳴唱的生動畫面,作品以此起興來抒寫女子即將“歸寧父母”的喜悅心情。此外,《周南·樛木》、《王風·葛藟》、《唐風·葛生》、《邶風·旄上》等篇中都是以葛起興,并由此形成了一個系列,常常抒寫綿綿戀情、悠悠親思。這種從描寫眼前之事之景來托物起興的手法,在《詩經》中極為常見,從而大大增強了作品的表現力和感染力。朱熹在《詩集傳》中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即是對“興”義的精要解釋。
那么,“先言他物”與“所詠之詞”的關系何在呢?這直接關系到我們對《詩經》作品的理解與賞鑒。因為詩人托諸自然世界的山川雪月、花鳥草蟲來起興,或許它們并非詩人要表現的主要對象,也未必都介入人的具體活動,卻有可能是與詩人的生活太密切,被用來作為表情達意的輔助手段;也或許詩中人物難以直言,借此委婉道出。于是,人的情懷與外在世界的物象聯系起來,從而啟發了人們的豐富聯想和想象,也大大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具體地說,“興”在《詩經》作品中的表現,按“先言他物”與“所詠之詞”的關系,主要表現為以下三方面:
一、先言他物,喚起情緒
《詩經》中有少數作品的起興,只是在開頭起調節韻律、喚起情緒的作用,興句與下文在內容上的聯系并不明顯,而只是為了避免突然、直接地進入主題。如《秦風·黃鳥》:“交交黃鳥,止于棘”,“交交黃鳥,止于桑”,“交交黃鳥,止于楚”,以黃鳥在樹上鳴叫、棲息來起興,這些與下文“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寫子車家的三個兒子為秦穆公殉葬沒有直接聯系,“興”只是起到了調節音韻、提示下文,幫助我們完成從日常生活到詩歌欣賞的過渡作用。再如《小雅·鴛鴦》:“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首二句以鴛鴦棲息、收攏左翅來起興,而后面兩句寫的是祝愿君子享長壽,年年歲歲有福氣,兩者并無意義上的直接聯系。《小雅·白華》以同樣的句子起興,抒發的卻是怨刺之情:“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抒寫了被棄女子對男子的怨憤之情。這種與本意無關,只在詩歌開頭協調音韻,引起下文的起興,是《詩經》興句中較簡單的一種。
二、借物言事,渲染氣氛
《詩經》中更多的興句,與下文都有著委婉隱約的內在聯系,其中之一就是烘托、渲染環境氛圍,以引發情感。如《鄭風·野有蔓草》寫情人在郊野“邂逅相遇”:“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清秀嫵媚的少女與滴著點點露珠的綠草一樣可愛,這樣綠意濃濃、生趣盎然的景色,和詩人邂逅相遇少女的喜悅心情,正好交相輝映。再如《鄭風·風雨》首二句“風雨凄凄,雞鳴喈喈。”寫的是下著雨、刮著風的晚上,女主人公正在思念自己的戀人,此時又聽到了叫曉的雞鳴聲,于是風雨聲、雞鳴聲更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惆悵之情。興在這里就渲染了一種凄涼的氣氛,從而加深了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
而《秦風·蒹葭》運用起興,更是達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諧的藝術境界。作品每章首二句起興,由“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到“蒹葭凄凄,白露未晞”、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寫出了景物的細微變化,不僅渲染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濱的圖景,而且烘托了詩人由于時間的推移,越來越迫切地懷想“伊人”的心情。凄清的秋景與感傷的情緒渾然一體,構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尋味的藝術境界,對后世詩歌意境的創造有著直接的啟發。
三、興中有比,韻味深長
《詩經》中的很多詩篇,往往比、興手法連用,比附象征中心題旨,更給人以韻味深長、回味無窮的審美感受。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起興,茂盛的桃枝、艷麗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禮的熱鬧喜慶互相映襯。而桃樹開花(“灼灼其華”)、結實(“有蔶其實”)、枝繁葉茂(“其葉蓁蓁”),則是對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孫、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詩人觸物起興,興句與所詠之詞通過藝術聯想前后相承,是一種象征暗喻的關系。《詩經》中的興,很多都是這種含有喻義、引起聯想的畫面,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興中有比。它們通過聯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更給作品帶來無窮的魅力。
再看《周南·關雎》,作品起首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起興作比,河洲上雎鳩鳥的和鳴引起了君子對淑女的追求與思念,讓他不由唱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情思;而雄鳥雌鳥的一唱一和、情意專一又象征著君子淑女之間的情投意合。所以詩歌一開頭就給人們展現出了一幅溫馨和美的畫面,自然引起人們對人間美好愛情向往和追求的綿綿情思。然而美好的東西總是難以得到,也正因為求索的艱辛,更顯得其彌足珍貴。所以下文作者又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起興作比,反復詠嘆。以荇菜之流動無方來比淑女之難求;以荇菜之“采之”、“芼之”來比淑女之追求到而“友之”、“樂之”,從而將君子對淑女追求不得的痛苦和求而得之的喜悅之情形象鮮明地表現了出來。這種興中有比的手法,更是引人無限遐想,使作品寓意深遠,言有盡而意無窮,從而構成了詩歌藝術境界不可缺少的部分。
參考文獻:
1、費振剛主編,中國歷代名家流派詩傳——《詩經》詩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劉肖杉,從信天游“興”透視《詩經》“興”之本真形態,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
3、司馬慧瑾選注,中國古典名著精華——《詩經》,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尹愛榮,湖北仙桃職業學院中文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