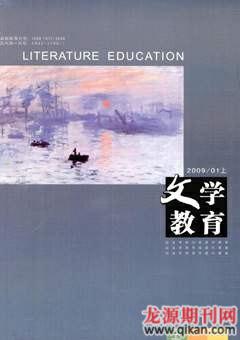“體用”思想的嬗變
“體用”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本源,是中國的元哲學。在倡導思想大解放、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今天,我們應該認真地學習、品味這一元哲學理論,準確把握其思想內涵以及其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的實踐運用和嬗變,并且結合自身的工作實踐不斷地加以運用、發展、創新。
“體用”見于體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易經·系辭》“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易經》中主要用來指占卜中的動卦和靜卦。其分別的準則是靜卦為體,動卦為用。因此,“體用”之說,其實質可以說是主次、本末之分的問題,也就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問題,或者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問題。《墨子·非命上》指出:“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于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這里的“本”、“原”就是指古代圣王和老百姓的經驗,也就是“體”;“用”就是在具體實踐中去行動、去驗證。可以說,墨子的“三表”說就是對“體用”哲學的具體發微。
宋代新儒學由于受佛教思維的影響,名實之辨不斷地向深層次推進和發展,“體”和“用”的區別也更受重視了。特別是儒學大師朱熹,更是嚴格區別“體用”。例如,周敦頤《太極圖說》中第一句話是“無極而太極”,就被朱熹理解為:“無極”是就“理”上說;而“太極”是就“氣”上言。一談到“太極”,就意味著“生陰陽”二儀的趨勢。“無極”與“太極”所指雖是一樣,但其能指卻各有差別。這當中其實就已包含著“體”、“用”之內涵意味了。胡五峰《知言》則明確指出:“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并且以體用來解釋儒家的中庸思想:“中者,道之體也;和者,道之用也。”北宋張載《正蒙·神化》提出:“德,其體;道,其用,一于氣而已。”認為“德”是氣之體,“道”是氣之用,更加明確地發展了體用的思想元素。
明代哲學家王陽明反復強調“本體”即是“一”,“本體”是抽象性最高、概括性最強的范疇。在談到“良心”的問題時,他認為,本體良心的具體的發用、流行、展開,就是良能。作為“體”的是良知,作為“用”的是良能。“良知者,心之本體。”并認為作為心之本體的“良知”是無所不包的,是無一物所能超然于其外的,“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傳習錄中》)。從哲學思想角度看,“良知”是理解問題,屬于認識世界的范疇;而“良能”則是運用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與實踐,屬于改造世界的范疇。它強調了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精神,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格物致知”的思想精神。例如“為老人折枝”而不為是屬于“知”的問題,“挾泰山以超北海”而不為就屬于“能”的問題了。再比如初到城里的鄉下人并不知道隨地吐痰是不道德的而隨地吐痰,這是“知”的問題,“不知者不怪”;有些官員明知以權謀私是不對的,但是禁不住金錢、美色的誘惑而喪失了行政道德人格,這就不是“知”而是“能”的問題了,必須嚴懲不貸!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的滲透,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不斷朝著深層進發,“體用”的問題再次被提了出來。洋務派鄭觀應(中山人)等人就從“體用”的深度對中西文化進行了比較闡發,中西文化的交融可以說達到了相當的深度和廣度。洋務大員張之洞更是明確地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著名觀點,將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始終作為“本體”、“本源”的東西;而將西學定位在“用”的層面上,這與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和精神是一致的,與魯迅先生所倡導的“拿來主義”思想以及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可以說,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的“體用”思想的發軔與濫觴,凝聚了我國歷代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一桌思想的盛宴。
古林松,廣東省中山市教師進修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