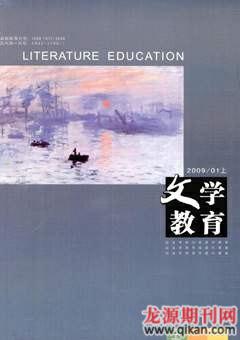《詩經·國風》與《圣經·雅歌》的意象比較
余 丹
《詩經》與《圣經》分別是東西方文化的源頭,無論是從思想內涵還是藝術形式上看,它們都對各自的文化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分風、雅、頌三部分。郭紹虞先生認為,風相當于抒情詩,雅相當于史詩,頌相當于戲詩。《圣經》包括舊約、新約兩部分,從文體上看,詩歌約占其總篇幅的三分之一,《雅歌》是其中最著名的抒情詩。作為中西抒情詩的經典,將《詩經·國風》與《圣經·雅歌》作一些對比當不是毫無意義的。當然,作為宗教經典的《圣經》與作為“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詩經》在終極意義指向上是不同的。
一
《國風》和《雅歌》都產生于人類社會早期,前者約成于公元前6世紀,后者約成于前4世紀。其時,社會生產力還很不發達,人類只有深深依賴于他們賴以謀生的自然環境,因之,對自然美善事物的歌詠就出現在早期詩歌中。《國風》和《雅歌》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通過自然意象表達一種原始生命意識的張揚。這種生命意識,又表現為對男女情愛和種的繁衍的推崇。
《雅歌》的第一首中有這樣的詩句:“我的愛人在男子中,如同蘋果樹在樹林中,我歡歡喜喜坐在他的蔭下,嘗他果子的滋味,覺得甘甜……”在這里面,“蘋果”的意象自然包含有性愛的成分。詩中還多次出現“紅石榴”的意象,它既指女性的美,也蘊含著對性和多子的期盼,這與中國詩歌是有共通之處的。此外,“泉、井、水、風茄、鳳仙花、玫瑰、百合花、香草、斑鳩”等意象在詩中也和男女性愛、生育有某種聯系。當然,這所有的意象與含義都統一于“愛人屬我,我也屬他”的愛的宣言中,如同《詩經》中的那句千古絕唱“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詩經·邶風·擊鼓》)
在《國風》中,“魚”意象出現得很多,這與原始人類社會盛行的生殖崇拜有關,聞一多先生的《說魚》對此有過精辟的論述。《詩經·衛風·碩人》、《陳風·衡門》、《衛風·竹竿》、《邶風·谷風》都有以魚或捕魚器具喻婚姻情愛的詩句。此外,《邶風·匏有苦葉》中的水、《周南·關雎》中的雎鳩、《召南·草蟲》中的阜螽、《邶風·靜女》中的彤管、《鄘風·蝃蝀》中的雨虹、《唐風·椒聊》中的花椒、《唐風·綢繆》中的束薪都是與男女情愛相關的意象。
《國風》與《雅歌》的第二個共同點是它們都沒有把意象創造當作最終目的,而是憑借意象營造優美的意境,既使情感有了很好的載體,又使意象本身獲得了更豐富的審美內涵。
關于意象與意境的關系,袁行霈曾有一段說明:“意境的范圍比較大,通常指整首詩、幾句詩或一句詩造成的境界,而意象只是構成意境的一些具體的細小的單位。意境好比一座完整的建筑,意象只是構成意境的一些磚石”。①由此可見,意象和意境有結構層次和審美層次的區別。在《雅歌》中,我們不難發現那些由眾多意象組合成的優美意境:“我的愛人哪/求你等到/天起涼風/日影飛去的時候/你要轉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這節詩見于詩中三處,這種類似于《詩經》的重章疊唱營造了一種一唱三嘆、回環往復的情感效果,還對詩歌的結構、節奏起了調節作用。
《詩經》中也不乏這樣的圖景。除了那首膾炙人口的《秦風·蒹葭》,還有很多唯美地詩作,我們試看《陳風·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首月下懷人詩,自此,月即與思念結下了不解之緣,開創了幾千年的對月抒懷傳統。除了這首詩,《衛風·竹竿》中的“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游,以寫我憂”;《鄭風·野有蔓草》中的“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都營造了極美的意境。
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國風》、《雅歌》作為人類童年時代集體智慧的結晶,表現了一種強烈的母體回歸意識,即多以自然意象創造優美的意境,并與詩中感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二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雅歌》是一首民間歌謠,但當它被放入《圣經》,成為這部神圣經典的一部分,宗教的光環就為它鍍上了一層特異的光芒。也正因為如此,《雅歌》與《國風》的異質性是不容回避的。
筆者認為,《雅歌》與《國風》意象的差異首先表現在:《雅歌》的意象復義性、模糊性更強;《國風》中的意象含義則相對單純。
阿恩海姆認為,所有的藝術都是象征的。這在《雅歌》中表現得非常明顯,詩中的“牧羊人”、“羊”、“葡萄”、“光”、“火”、“帳篷”、“幔子”、“沒藥”、“膏油”、“鴿子”、“香柏樹”等都有很豐富的象征意義。正因為有這么多的宗教意象,所以猶太教徒認為《雅歌》是在暗示上帝和選民的關系,而基督徒則認為是預表基督和教會的關系。我們不必把這種信仰角度的解釋完全指斥為謬誤,一如斯騰伯格在其《圣經的敘事詩學》中所認為的:“要把《圣經》的文學解讀建立在它的宗教使命、歷史文化和地域背景的基礎之上,也就是要把它置于一定的歷史政治環境中來進行解讀,并且要參考最早的經文學者包括猶太教教士提供的研究心得,否則純文學解讀只會歪曲圣經的原意,成為一種不負責任的文字游戲。”②
相對于《雅歌》,《國風》的意義要單純一些。如前所說,《國風》中也用了很多的隱喻、暗喻,但其意義一般較容易把握。開篇《關雎》雖也有過不同的解釋,但一般認為所謂的“詠后妃之德”是有局限的。其它的詩像《周南·桃夭》贊詠新婚夫婦的青春亮麗、愛情美滿;《召南·野有死麕》敘述少女與獵人的巧遇、私語;《召南·草蟲》寫女子和丈夫分離的苦痛及重逢的喜悅等都比較好理解。即便像《秦風·蒹葭》這樣的清峻朦朧之作,我們也不難感受到詩中主人公的憂思與惆悵。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講的“意義單純”并非否認《詩經》的豐富內涵,因為從“四家詩”到現在,關于《詩經》的闡釋也有很多不同意見。筆者的意思是,作為《詩經》中語言最曉暢明白的《國風》,它不像《雅歌》那樣有深厚的宗教背景,其內涵也相對單純。
《雅歌》與《國風》的第二個區別是:《雅歌》的意象有很濃的田園牧歌式的情調,有很強的超驗的彼岸色彩;而《國風》的意象多與生產勞動有關,有濃郁的生活氣息。
在《圣經》中,描寫自然主要是為了表現上帝,如勒蘭德·萊肯在《圣經文學》所說:“他們對自然的描寫是表現上帝這一更大主題的組成部分,在他們看來,代表其它傾向的自然詩都是空洞無物的,似乎忽略了最重要的內容”。①正因為這樣,來自民間的《雅歌》也難以與這種宗教情緒劃清界限。詩中的各種樹木、草地、佳果、香料、泉源,莫不與上帝的榮耀有關。因此,在我們讀《雅歌》時,那種激情的表白讓人身在塵世,而那花草茂盛、清水長流、佳果林列、牧羊成群的意境又讓我們遠離塵俗。我們就在這亦真亦幻之間品味著《雅歌》的甘醇。
《國風》則不同,它完全來自下層人民的生產勞動,因此,即便是情詩也多與勞動相關。如《周南·關雎》中“參差荇菜,左右芼之”、《召南·草蟲》中“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召南·野有死麕》中“野有死麕,白茅包之”等等。單就意象來講,伐柯、束薪、析薪、束芻、栗薪、捕魚、漚麻、紡織等勞作之事都被用來暗示男女婚媾,這就使《國風》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感情質樸而熱烈。
小結
開創了20世紀下半葉至今的圣經文學解讀傳統的猶太學者艾里克·俄爾巴赫曾得出這樣的結論:“《圣經》是同《荷馬史詩》比肩的偉大史詩,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②如此,《雅歌》這首“歌中之歌”的文學性自不待言。《詩經》是中國詩歌的源頭,其中的《國風》亦被后世詩家奉為經典。對興象玲瓏的境界的創造本是中國詩歌的傳統,但在《雅歌》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體現。這反映了文明初創時期人類的某種共同心理:對自然萬物的原始崇拜,對自己作為自然一分子的認同。當然,我們不能忽略《雅歌》作為宗教經典一部分的特質,不能忽略世俗情愛背后的宗教意味,因為,作為“偉大的代碼”的《圣經》承載了太多的對生存意義、對人世情懷、對彼岸世界的不懈探求。或許,在我們以羅伯·亞特所說的“閑適心情”來欣賞《雅歌》時,我們會獲得某種心靈的感悟,一如我們在面對《詩經》這個浩瀚的海洋時,我們似乎已看到了此后幾千年中華藝術的發展流變。
注釋:
①轉引自嚴云受:《詩詞意象的魅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47頁。
②參見劉意青著:《圣經的文學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頁。
①轉引自蔣述卓著:《宗教藝術論》,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頁。
②參見劉意青著:《圣經的文學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頁。
參考文獻:
1.袁梅著:《詩經譯注》,齊魯書社1985年版。
2.孫小平編選:《圣經抒情詩選》,三聯書店1989年版。
3.嚴云受著:《詩詞意象的魅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劉意青著:《圣經的文學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5.蔣述卓著:《宗教藝術論》,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版。
余丹,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06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