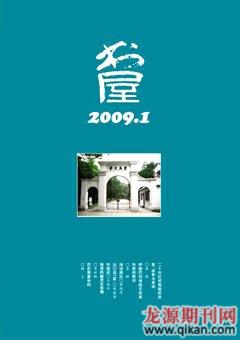職業、事業斷想
樊百華
佛教說業不說職業。我沒有看到有什么宗教怎么肯定職業對人生的意義。其實,既然人首先必須吃喝,必須生存下來,然后才談得上例如修行,那么,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也好,主持、方丈、教皇、牧師、喇嘛、班禪、活佛等等也罷,他們就都不僅是“先知”,也同時是一個社會角色,一個職業人。當然,各種職業對他人乃至人類的價值不同,這是另外的問題。這里只是說,任何人都首先要設法活下來。傳說釋迦牟尼七天不吃不喝,終于修成了佛,但本可以繼承王位的他成佛之后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很多底層人每天要做的:乞討!不能說他的乞討本身與乞丐的行為有何兩樣。
僅僅從“獲得生存資源的活動”這一點談論職業,那么,偷盜確實也是一種人類的職業。這樣說很多人已經覺得大逆不道。我剛剛說過暫時不考慮職業的社會價值。國王與托缽僧的價值怎么比較,寧肯上十字架也不跟敵人角力(耶穌)與驍勇善戰或者能征慣戰(穆罕默德)如何評價,需要作另外的討論。
我自己也常常脫口而出“事業如何如何”,徹底樸實地看,若是可持續謀生的就首先都是職業。為了與職業區分開來,我把事業定義為“一時或很長時間內難以換飯吃的活動”。這里面人們長期以來的一大流傳看法是“竊國是事業,竊鉤是罪業”。其實,皇帝、總統等等,其職業的最大特點,首先恐怕恰恰是“味道甚佳”。這樣說來,竊國與竊鉤本身都是“職業努力”。
近代以來,因為納稅人的“國家支持”或商人們的商業投資,求真的科學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成了謀利活動,事業的光環也愈益顯露出職業的品格來。創造美的文學藝術活動越來越成為“自由職業”——職業是實話實說,自由則是說不需要遵守勞動紀律,沒有組織規章的約束。
較為復雜的是“致善的活動”。教人向善在所有宗教團體那里曾經無不是神圣的事業。最突出的當然是中世紀。那時的教會,例如基督教的從教皇到牧師,是上帝與俗眾之間的中介和紐帶。但是,他們的世俗生活或多或少都是由仆傭、助手伺候著的。俗眾向教會納稅無不是神圣的義務,教會的各級教職無不為人們垂青。集權力、地位、榮耀、滋潤于一身,真是不賴的職業呢!今天這個時代很多政教合一的國家和地區,一個人生下來就入教了,但后來只有少數人甚至還是懵懂的孩子,就被選送到例如寺院,這對孩子所屬的家庭(族)可是一大喜事。為什么?在我看來,這孩子一輩子都不需要種地放牧了,不用干最粗最臟最累的活兒了,盡管進入寺院還得盡義務,例如少林寺的小和尚還得干很多勞累的活兒,但總算跳出了農門,進了“事業機構”,靠了念經打坐、劃拳劈腿,就能衣食無憂了。
所謂不勞者不得食,這里的“勞”當然指直接生產衣食的體力勞動,基本上落在經濟學說的“第一產業”。真要是不勞者不得食,從古代的祭祀開始的事業,就都不可能出現了。可是,從來都是治人者盡享榮華富貴,而“治之要者,唯祀與戎”。所謂一張一弛的文武二術而已。于是,古往今來無不是嘴皮子、筆管子、刀把子、槍桿子,比起釘耙鋤頭來魅力四射、神采奕奕。
生存既然是人類的第一需要,人類的第一個秘密也就必定發生對于謀生活動的關聯中。那就是:不是不勞者不得食,而是恰恰相反,不勞者得美食、先食。準確說,是不勞者如何通過種種手段贏得和分享到治權,而后把勞動者當成了自己的手足。
由此看人類的宗教,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一切宗教的操縱支配者們,無不是寄生的。真是很奇怪啊,寄生的靠著說教而贏得尊敬,而且人們不得不承認,說教者對人生萬象的觀與思、覺與悟,確實比蕓蕓眾生要豐富深刻得太多。這好比中國傳統的文人雅士,終身悠哉樂哉,吃香喝辣,但見識確實要比布衣農夫深廣。去年我在研究安利“直銷”與“傳銷”的異同時,看一本關于中國安利公司的書,那當中絲毫沒有讓我感到意外地說道:“傳教士傳教時,無論對方相信與否,他總是不斷地將福音傳播出去,不會因有人不信而動搖他傳播的意念。因此,做直銷事業不要因為幾位朋友不愿意加入就心灰意冷,應該學做傳教士,執著堅持到底”〔1〕。這里我想順便說到心理學:例如過去的中國,雖然長期沒有心理學,但卻有很豐富的勘察統馭人心的經驗。人類的各類宗教操縱,盡管教義經籍中間沒有任何心理學的探討,但在宗教的操縱實踐中,卻有對人性人心的最精明的把握。
回到“治之要者,唯祀與戎”。既然這是統治社會的最高事實,那么,一旦社會擺脫了種種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羈絆,祭祀階級(層)也就只能結束其實質的職業時代,而讓信仰回到人們的業余生活。是的,是業余生活。我認為,所有的職業本身都沒有信仰可言,因為——所有的職業都是謀生性的。宗教信仰有關于人生,但無關于謀生活動本身。正像原始巫術曾經是例如狩獵活動的重要環節,但實際上無用于狩獵,否則后來的狩獵就不會摒棄巫術了。
據說一些政教分離國家的現代基督教教會,已經從人們的“公共生活”剝離開去,就是說教會已經對人們的權利義務關系不再具有或軟或硬的壓力。信不信教、參不參加教會活動,純屬個人的“非職業偏好”。于是,教育、司法等公共領域,不再有教會的權威。不要說牧師不得進入學校的課堂傳教,就是任何教師在課堂上力捧某一宗教,也有違法之嫌。教會還有,教職人員也還有,但都成為人們的無涉于權力結構的安排,而且越來越重疊于慈善事業。而慈善事業中的專職薪給人員當然是一種職業人,是非盈利慈善業基于效率與責任而必須做出的職業安排。
從中我們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現代社會”的職業化。任何人都必須謀生而不可寄生,都必須有職業或者首先表現為一個職業人。在這里,人人都必須受制于凡胎肉身的糾纏,必須脫魅,而無法靠了神秘、魅力不受任何職業的羈絆。
尤其重要的是,例如教會的非職業性,只能出于公共安排;而其職業性歷史遺留只能出于非公共性安排。這種安排不是少數人,也不是某一團體或者某一政黨作出的,而是民主憲政社會所有公民都負有參與責任的一種基本制度。
這使人們從一些新維度看到了“職業化社會”對“事業”的擠壓——一切無效于實利的活動都必須“非職業化”,都不得成為獲得謀生性回報的職業性手段。
有些社會不是這樣的,大量的職業對人們的實利活動非但無效而且有害,但是卻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公薪”人員。這樣的社會在文明程度上,還處于宗教裁判所權力至上的中世紀。
職業化社會有高低階段之分。高級的職業化社會,是人類的事業得到鞏固持續的職業支撐的社會。例如科學研究當然是人類必須不斷加強的事業,一個社會發達的標志首先就是科學研究有高度的自由、熱情,人們對之有恰如其分的職業性支持;再如推動民主化轉型當然是一些落后社會的極重大的事業,民主化運動之開展的狀況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職業支撐的程度。事業非職業,但有賴于職業社會真實真誠、自發自由、持續有力的支撐,這樣的社會就是一個職業、事業相互涵養的好社會。
注釋:
〔1〕時驊編著:《安利直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