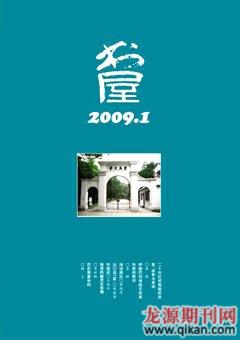可憐誤記戴東原
田 吉
《清國史·儒林傳》卷八中,我們找到了長沙人余廷燦的本傳。交代余氏的生平行事之后,撰者重點介紹了他的學術成就:“其學兼綜經史及諸子百家,象緯、勾股、律呂、音韻,皆能提要鉤玄。嘗與休寧戴震、河間紀昀相切劘。”對一名二流學者來說,這評價尚稱公允。不過,文中特意拈出的余氏曾經和戴震、紀昀二人相與論學之事,則不能不讓人心生疑竇。翻開他的《存吾文集》,確實可以看見和紀曉嵐的書信往還,但同樣是在集中的《戴東原先生事略》,余氏明明惋惜地追憶著戴震:“廷燦未識君面,而喜讀君書,后君之死十有二年來京師,從士大夫之后,日聞君之學與君之人。恐久就墜逸,因敘次其事略,以待史館采擇焉。”看來,廷燦當日交接的只是紀曉嵐,而對于自己崇拜的戴東原卻一直無緣結識,也就不存在所謂的“相切劘”了。
史官作傳,總得有所依傍。這篇傳記的來源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沅湘耆舊集》。集中第九十五卷有余氏小傳,編輯者新化人鄧顯鶴是這樣評論這位湖湘鄉賢的:“先生學有本原,其論天文律歷、勾股徑圍之學,與休寧戴氏東原往復辯難,具見《存吾文集》。”看起來鄧顯鶴似乎并未仔細閱讀余氏文集,難怪楊樹達先生后來給《存吾文集》撰寫提要的時候,也批評顯鶴此傳“傳聞誤記,多與事實不合”。
“傳聞誤記”自然不假,可我們是否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么這位嫻于學林掌故、被梁啟超稱為“湘學復興導師”的文獻大家,偏偏“誤記”了戴震呢?
乾嘉之際,樸學逐漸占據了學術界的中心位置。一大批樸學大師以治經學發端,精研文字音韻、章句訓詁,進而擴展到名物、典章、史地諸方面的考據,產生了不少可以傳世的學術成果。流風所扇,后進翕然,學者們紛紛為故紙堆吸引,不惜焚膏繼晷、皓首窮經。后人分別以惠棟、戴震為宗師,把當時眾多的樸學家劃作彬彬濟美的吳、皖二派。不久,以阮元為代表的揚州學派也悄然興起,足堪鼎峙于后。而作為一代樸學宗主,戴震無疑成為眾人崇拜的偶像。可以說,那個時代最耀眼的青年俊彥,大都選擇了樸學,競相以能蹤跡戴氏為榮——連那位自視甚高的章學誠,也和桐城派大師姚鼐一般,年輕時都免不了要仰視東原。
然而,正當這股樸學潮流風起云涌、蔚為大觀的時候,一向以“理學之鄉”聞名的湖湘大地卻如同被遺忘的角落,幾乎未受影響。“湘士治學大都以宋儒義理之學為依歸”,盡管剛才說到的余廷燦以及稍后的唐仲冕等人因為游宦京師而稍稍接聞戴氏學風,但直到道光年間,要在湖南找出那么一兩位純粹的樸學家竟是那么困難。這點已經為不少學者所注意,而以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說法最具代表性:“清儒考證之學,盛起于吳、皖,而流行于全國,獨湖湘之間披其風最稀。”這不過是一種客觀事實的線性描述,章太炎就沒有這么客氣了,被他諷刺“不知小學”的“三王”,就有王夫之、王闿運兩位湖湘學人。最直接的恐怕是那位狂放的李慈銘,當他讀到郭嵩燾的《禮記質疑》時,竟然徑直宣稱:“湖南人總不知學問。”盡管《越縵堂日記》一直以好逞雌黃、睥睨當世而名,但如此“裸斥”,輕蔑之甚卻也不多見。
當然,李慈銘是鄧顯鶴的晚輩,章、錢二位的評論,顯鶴更沒有機會看見。實際上在當時,樸學也處于上升階段,內部的“學術譜系”尚來不及進行清晰地追溯,而偏居“山國荒僻之亞”的湖南,在類似于今天的“學術批評圈”中更沒有占據什么耀眼角色。因此,我們不能貿然推斷顯鶴對余廷燦與戴震論學之事的“傳聞誤記”,就一定是因為受到外界譏刺“湘學不競”而做出的有意借重。但我們至少可以這么認為:鄧顯鶴應該承受了一定的心理壓力,在他看來,余廷燦能與當時的學界精英討論辯難,應該算得上是余氏的機緣,也是湖南學人的光榮。
這種苦心孤詣,在當時的湖湘學界,也決非僅見鄧顯鶴一人。嘉慶末年,湖南布政使翁元圻開局重修省志,恰逢清廷國史館也正在續纂《一統志》,后來成為兩江總督的陶澍急忙寫信告訴在長沙志局的好友黃本騏:“此時館中正在纂輯《儒林》、《文苑》列傳,湖湘自王夫之先生而外,得入者寥寥。弟雖極言之,而亦未能多收,正因無憑據之故。是省志不可不早成送館,以備采擇也。”為了能在國家層面多見著一些湖南人的名字,陶不得不催促省志早日成書,其一心表彰湖湘先正之情可謂亟矣。
不過外界的批評確也不是空穴來風,乾嘉年間的湖南,畢竟真沒有什么像樣的樸學家——當然也不否認一些學人受湖外風氣的影響。在《新化縣志》中,就記載著一位學者的有趣事跡,他叫唐世倜,是鄧顯鶴的同鄉好友,早歲“好學喜吟,為詩已裒然成集”,中年之后因向慕學術,又“為考據之學,不復措意聲律”。而晚年作客桂林,“見同人社集,復理舊業”。一生徘徊辭章與考據之間,這樣的尷尬狀況,是否也透露出當年真實的湖南學風?
回響往往要在聲音消失以后才出現。咸豐以后,作為一種學術潮流,樸學逐漸衰落。但作為一種評價標尺,是否精于小學、長于考據卻幾乎成了學與不學的惟一標準。這么看來,盡管培育過屈原、周敦頤二位巨子、有著悠久辭章與理學傳統的湖湘大地在其他方面不乏濟濟楚材,但對不起,偏偏少了些樸學人士,他李慈銘就有足夠的理由鄙夷整個湖南。鄧顯鶴以后的湖南學者自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正是那位讓李慈銘大發感慨的郭嵩燾,便自覺承認湖南“衣冠之盛,文章學問之流傳,不逮吳越遠甚”(《羅研生七十壽序》)。在他看來,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乾嘉之際,經師輩出,風動天下,而湖以南暗然無知鄭、許《說文》之學者”(《羅研生墓志銘》)。王先謙在編纂《皇清經解續編》時,也認為“江皖耆彥,學術紛綸;湘士卑卑,懷慚抗手”。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越到后來,湖南人對鄉先賢樸學不昌的尷尬似乎越發敏感,心理緊張感也日漸增強。《湘學略》的作者李肖聃就曾這樣惋惜:“假令硯仙(龍璋)生承平時,與王、段諸公為友,講明字例之條,湖南文字之學,不如是之未昌也。”(《星廬筆記》)
但是,比其他地方慢了半拍之后,湖南的樸學很快昌盛起來了。在道光年間鄧顯鶴、黃本驥等人的提倡下,中經鄒漢勛、何紹基,直到清末的閻鎮珩、皮錫瑞、王先謙、葉德輝(盡管他不是很愿意承認自己的湘人身份),一時間湖湘英才紛紜,儼然不讓吳越。進入民國,新學競爽,樸學失卻了那最后的光芒,日漸式微,但就在此時,往日沒有被人家看得上眼的洞庭之南,卻誕生了楊樹達、曾運乾、余嘉錫、馬宗霍、駱鴻凱、張舜徽等一大批樸學精英。歷史的循環,讓冷眼旁觀者難免唏噓不已。
可就算如此,這些湖湘學人仍然在為鄉先輩們感到遺憾。作為近代以來湘學的兩位代表人物,楊樹達和張舜徽的態度大概可以略窺消息。
楊氏不乏對湖南樸學歷史的清醒認識。1934年10月27日,楊樹達在日記里記載:“讀唐仲冕《陶山文錄》。陶山之學不主一家,然吾湘乾嘉前輩能了解漢學者僅陶山及余存吾廷燦兩人耳。”在《存吾文集》的提要中,他也感嘆:“乾嘉之際,其時漢學風靡一世,而湖湘學子大都猶專己守殘,與湖外風氣若不相涉。”而因為章太炎“不通小學”的諷刺,早年的楊樹達與曾運乾(星笠)甚至訂立過“雪恥之盟”:“余昔在北京,曾與星笠談及此;余謂此時吾二人皆游于外,他日仍當歸里教授,培植鄉里后進,雪太炎所言之恥。”日后楊、曾二位步入中年,學問文章,海內推服,所雪之恥自然不止“不通小學”了。晚年的楊樹達,還因為《積微居小說述林》出版的時候有人指責自己沿用乾嘉諸儒“常用之方法”,而特意總結出自己超出乾嘉樸學家的五個方面。學術自信心逐漸建立以后,他對來自樸學之邦的評判就有了自己的看法。浙江人張孟劬曾經這樣評價楊樹達和余嘉錫:“湘中學者自為風氣,魏默深不免蕪雜,王益吾未能盡除鄉氣。兩君造詣之美,不類湘學。”揄揚背后掩藏不住赤裸裸的地域偏見和文化歧視,楊樹達難免未愜于心:你張孟劬的文化優越感也太強了,先別說我楊某的學問,像余嘉錫這樣獨步天下的目錄版本學,江浙人士哪能做到?愛鄉之情,自得之意,均不難想見。不過對于張氏批評魏源和王先謙的“蕪雜”和“鄉氣”,楊樹達好像并未否認。
無獨有偶,張舜徽在評價乾嘉之際的湘學時,也表達了與“鄉氣”近似的判斷。本來當他看見李慈銘那句輕妄之言,自尊心也是大受傷害,借著撰寫《清人筆記條辨》的機會,把李氏狠狠訓斥了一番:“湘湖先正之學,本與江浙異趣,大率以義理植其體,以經濟明其用,使以李氏廁諸其間,只合為吟詩品古伎倆耳。孰為重輕,不待智者而自知。乃自困于尋行數墨之役而不見天地之大,遂謂湖南人不知學問,其褊狹亦已甚矣。”酣暢淋漓,令人神為之旺。但當讀到另一位鄉賢黃本驥的著述之后,張舜徽多少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黃本驥“其詩與文,皆不免有村父子氣”。同樣使用“鄉氣”這個概念,這話從張舜徽的嘴里說出,效果就大大超過了域外人士,頗有點切中湘學病根的味道。為此,他還不惜引用朱熹的話來作為印證:“岳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騁空言而遠實課。”(《朱子文集·與曹晉叔書》)看起來,湘學之弊由來已久,李慈銘的輕侮,也不是全無依據。
和鄧顯鶴相比,楊樹達和張舜徽當然更有資格評價湖南的樸學,也終于可以用更對等的態度與江浙學人往復辯難。不過正是透過楊、張二位,我們分明可以看見,鄧顯鶴曾經面臨的心理壓力,并沒有隨著湖南樸學的興起而消弭。
“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余波”。至今高懸于岳麓書院的這副聯語,道盡了湖南人的氣魄。只不過,此聯作者卻是那位被李慈銘譏為“江湖唇吻之士”的王闿運,或許這正是一種宿命的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