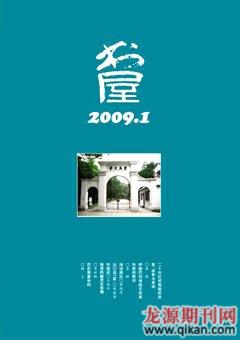錯把“舊夢”當“新夢”
賀越明
近日,讀罷李偉所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印行的《報人風骨——徐鑄成傳》,發現書中史實的“硬傷”頗多,相關的事理邏輯也較紊亂,因而未能如實記載和準確描繪這位杰出報人的思想和行為。這里,僅舉涉及傳主著述的一個史實為例。
該書第十四章第二節“摘帽還是‘右派”中寫道:“如果說,徐鑄成在屈辱的年月里,還有高興事的話,那就是1962年的次子徐福侖結婚,1963年他的著作《新金陵春夢》在香港出版與長孫女時雯的出生,他有了第三代。”(見第257頁)1963年,徐鑄成是有一本書在香港出版,但書名是《金陵舊夢》,而非作者所言的《新金陵春夢》。
《金陵舊夢》由香港致誠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收錄了二十六篇文章,題目有:從交易所到北伐時期的蔣介石、閻錫山軟禁馮玉祥、閻老西反蔣從假到真的內幕、蔣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領、內憂外患中的兩個“九·一八”、“十日主席”閻錫山、蔣介石湯山軟禁胡漢民、寧粵分裂的趣劇、何成竣養蛇弄笛,等等。其中,末篇“龍云事件補略”,是另一位作者所寫,系從事實上補充徐鑄成所撰的“蔣介石如何吃掉龍云”一文。或許因為這個緣故,該書的著者署名是“容齋等”,而“容齋”正是徐鑄成用過的筆名之一。
從1982年下半年起,筆者在徐鑄成先生門下攻讀研究生,知道他先后擔任過桂林、上海《大公報》總編輯和上海《文匯報》總主筆、總編輯和社長,所撰數以百萬計的文字中有許多是不署名的,也有一部分是用筆名發表的,我曾請他回憶用過哪些筆名、各有哪些含意。關于“容齋”這個筆名,徐鑄成當時說:“之所以取這名字,是覺得自己遭受如此重大的政治打擊,心里只有容忍而已。”當然,“容齋”兩字,應是移用自宋代學者洪邁的《容齋隨筆》。他還告訴我,上世紀六十年代在香港出過一本書,就用了這個筆名。正是借助這個線索,一年后,我趁赴京搜求論文資料之際,在國家圖書館港澳臺部訪得此書,并在館方幫助下復制一本帶回。徐鑄成見后頗為驚奇,但只粗粗翻閱一過,也沒有說什么,更沒有讓我把書留下,這多少讓我有些訝異:是這本書沒有留存的價值呢?還是容易勾起某些不愉快的回憶?
現在傳記錯把“舊夢”當“新夢”,也不完全是作者的過失,因為傳記基本上是照抄《徐鑄成回憶錄》,此處也不例外,采用的是回憶錄的說法(見第305頁):
1963年 年五十六歲
港友集我在《大公報》發表之佚事、掌故,在港出版單行本,并代取名為《新金陵春夢》。我僅得一冊,后且為市政協某領導索去,迄未歸還。
是年8月,長孫女時雯出生,歲月蹉跎,百事無成,我開始有第三代矣!
在徐鑄成的這部編年體回憶錄中,1963年這一年是寫得較為簡略的,寥寥數字,一筆帶過。而且,在見過我帶回并展示的復制書后,還是把書名寫錯了,可見對這本書的印象是如何的淡漠,又或者是如何的不看重了!
令人奇怪的是,傳記的作者卻別有描述:“前已述及,徐鑄成因經濟困窘,在石西民特批下,向香港報刊投稿。文章大都發表在香港《大公報》上。經香港友人搜集整理交出版社出單行本,取書名為《新金陵春夢》。取得一本樣書,后被人借去而不歸還。這同樣是高興事。”(見第257頁)這說明作者不光是照抄傳主的回憶錄而搞錯書名,而且對該書的來龍去脈也不甚了解,因而對事實的鋪陳捉襟見肘,表述上既不準確也不恰當。就石來說,在此事上用“特批”是言重了;對徐而言,以往昔《大公報》、《文匯報》之經歷和地位,講“投稿”是貶低了,且與事實不合。
整個事情的經過,我曾聽徐鑄成親口談過:
1958年,他被正式定為“右派”,撤去《文匯報》社長和總編輯之職,行政級別從八級降到十四級,二百七十元工資減為一百四十元。原來,他在華山路的枕流公寓居所,共五間正房和兩間偏房,由報社每月津貼房租一百元。這時他被調去出版局,不再享受房貼,只好退掉三間正房,讓報社分給其他職工入住。即使這樣,他仍要支付每月五十元的房租,家里還雇有照顧年邁母親的保姆。這樣一來,家計拮據,有時要靠變賣舊衣物維持。第二年國慶節期間,他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之后,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一位領導約他談話,詢問有何感想,他便訴告了經濟困難,希望能夠給予一定的補助,但領導聽后沒有下文。
過后不久,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石西民知道了這個情況,趁香港《大公報》副刊主編陳凡來滬時,特意關照其登門向桂林《大公報》的老上司徐鑄成約稿,有心讓他以稿酬貼補生活,不過限定文章只能用筆名刊出。從此,他應邀在《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上寫些民國時期政壇秘聞,每月可獲約五十元港幣的額外收入。除了“容齋”之外,他還用過“丁寧”的筆名,到第二個孫子時霆出生后,也偶爾用“時霆”作筆名。后來,他發表的這些文字,在不知情下被選編成書出版。
《金陵舊夢》一書看來銷量不俗,直到1973年6月還出了第六版,定價為港幣二元八角。當然,其時蝸居上海的徐鑄成對這些一無所知。對他來說,當初寫那些文章實屬為“稻粱謀”,又不能署真名,結集出版后僅得一本樣書,還被政協的官員“借”走不還。事實上,“右派”分子即便摘帽,頭上的帽痕猶在,在別人眼里還是戴罪之身,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的左派,有誰會尊重他的著作權呢?現在,傳記作者竟稱,徐鑄成“取得一本樣書,后被人借去而不歸還。這同樣是高興事”。如此“想當然”地曲解傳主彼時彼地的心境,真不知從何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