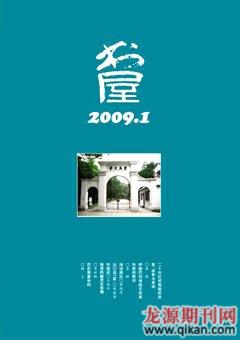出口成“臟”
陳漱渝
什么叫臟話?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并不容易回答。大體而言,“臟話”是相對于“凈語”的一個概念,多指羞辱、詛咒對方,以及涉及穢物、性行為或和人體器官的語匯。不過,對“臟”與“凈”的看法具有時代性和地域性。比如女性性器官常被當成臟字罵人,因為它除了具有隱蔽性之外,在男性視角中它還可能成為欺騙或背叛行為的發生地;在男尊女卑的社會,它既是生理發泄之處,同時又被視為穢物。但在十三世紀的英國,它卻被視為尋常物。比如1223年英國倫敦有一條街道竟以它命名,甚至在這個名詞之前還加一個動詞“摸”(Gropecuntlane)。這件事見諸文匯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臟話文化史》,作者為露絲·韋津利。同一書還舉例說,在《圣經》時代,拿國王的睪丸來宣誓忠誠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又說,胡須在伊拉克文化中占有神圣的位置,所以2003年在一次阿拉伯高層會議上伊拉克代表用“胡須”來詛咒科威特外交官。這些都說明對于“骯”與“不臟”,不同民族在不同歷史階段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中國關于性器官和性行為的古老描繪見諸《易經》。今人多不識古文字,以及某些古文字意義的轉化,并不將其劃入臟話的范疇。比如“運轉乾坤”,今天多用于表達改造大自然的雄心壯志,但在《易經》中,乾坤兩卦明明是兩性生殖器的符號。八卦的根底,即古代生殖崇拜的遺風。《周易》中的“云行雨施”,即古代性行為的術語。至于“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執其隨”、“咸其訆”、“咸其輔頰舌”,更把性行為的過程描寫得淋漓盡致,一般讀者并不以為污染耳目,只有像潘光旦這樣博學的人類學家才能破解其中的奧秘。
在一定條件下,臟話的含義還可以淡化或轉化。比如號稱中國國罵的“他媽的”,原由五個字合成——前面有一個動詞,后面還有一個名詞,借破壞對方母親的貞操侮辱、激怒對方,而使謾罵者一時獲得某種精神上的勝利。但它由五個字壓縮為三個字和兩個字的罵語之后,其攻擊性逐漸淡化,有時化為了口頭禪和感嘆詞。在特定場合,這個臟詞罵語還能轉化為一種愛稱。中國現代對臟字有獨到研究的魯迅在他的著名雜文《論“他媽的”!》中舉例說:“我曾在家鄉看見鄉農父子一同午飯,兒子指一碗菜向他父親說:‘這不壞,媽的你嘗嘗看!那父親回答道:‘不要吃。媽的你去吃罷!則簡直已經醇化為現在流行的‘我的親愛的的意思了。”
出口成章,這是很難達到的一種文化境界。即使有些妙筆生花的文人,口頭表達能力也未必能跟他的書面表達能力相稱。但“出口成臟”卻是一件難以完全避免的事情——尤其對于男權社會的男人。在中國現代史上,國共兩黨的主要領導人都動過粗口。蔣介石的那句著名的口頭禪就是浙江的罵人話“娘希匹”,當代觀眾已經在有關電影和電視劇中聆聽過了。毛澤東《念奴嬌——鳥兒問答》一詞的結句為“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也成為中華詩詞史上的一種壯舉。毛澤東說過,中國古代圣人是孔子,現代圣人是魯迅。但這兩位圣人也都動過粗口。孔老夫子刪削的《詩經》,其中的不少篇什就是當時的猥褻歌謠,其中保存著赤裸裸的性語匯。孔夫子還把自己那位“利口辯辭“的弟子宰予罵作“朽木“和“糞土”。魯迅是嚴詞反對辱罵和恐嚇的作家。但作為一個不但有七情六欲,而且愛憎之情特別強烈的人,魯迅的私人信件中多次出現過罵人話,比如致錢玄同信中,罵劉師培計劃創辦的《國故》月刊是“壞種”辦“屁志”,在致許壽裳等親友信中還使用過“仰東石殺”或“娘東石殺”這類浙東流行的罵人穢語,其侮辱性遠遠超過了紹興的常用罵語“小娘生”和“賤胎”。
外國名人也有愛罵人的。據說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就有罵臟話的習慣。他的太太不堪忍受,終于有一天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一大串臟話擲向丈夫,借此讓丈夫知道她平時是如何痛苦。不料馬克·吐溫彬彬有禮地聆聽之后,淡淡地對妻子說:“親愛的”,雖然你用詞都正確,但語調有些走樣。令妻子啼笑皆非。行文至此,又讀到一則新華社專電,說1997年英國女王的丈夫因首相府插手戴安娜王妃的喪事,出“粗口”呵斥首相府的工作人員,此時女王在旁,對丈夫的做法露贊美之色。可見在講紳士風度的英國,尊貴如女王丈夫者在情不可遏之時也用臟話傷人。
臟話既然在日常生活中頻繁出現,自然也會成為文學作品——包括經典名著中的常客。不但中國的《詩經》、《易經》中有所謂臟話,《圣經》“雅歌”中并不雅馴的內容也頗不少。西方的文學名著如喬伊斯的《尤里西斯》因有臟字被檢方控為“有傷風化”。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因有臟話一度被禁,作者也被送上了法庭。外文跟中文一樣,也有一詞多義的現象。比如“Congress”,普遍的字義是“國會”,但亦含性行為之義。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中就有一些這樣的雙關語,被選作教材時,常常在課堂上引起學生的竊笑。近些年來,為了糾正神化英雄人物的傾向,中國的“紅色經典”中常借助臟話表現人物的人性和個性。比如優秀電視劇《亮劍》、《狼毒花》中的主人公,都是名副其實的“出口成臟”。這是否會給中國的觀眾造成“聽覺污染”,頗值得作家認真考慮。還是魯迅說得好:“現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對話里寫上許多罵語去,好像以為非此便不是無產者作品,罵詈愈多,就愈是無產者作品似的。其實好的工農之中,并不隨口罵人的多得很,作者不應該將上海流氓的行為,涂在他們身上的。即使有喜歡罵人的無產者,也只是一種壞脾氣,作者應該由文藝加以糾正,萬不可再來展開,使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鬧得不可開交。”
在文明社會,當然不會放縱不文明的臟話肆意泛濫。西方國家的憲法中標榜保護個人的言論自由,但其中并不包括誹謗、中傷和隨意罵臟話。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英文俚語與非傳統用詞辭典》因為收入了臟話,在圖書館一直被控制使用,只有事先辦理特別申請手續才能借閱。2003年12月,美國搖滾明星波諾在金球獎頒獎典禮上出“粗口”,引起了輿論的譴責。加州議員道格·歐瑟特為此提出了一個名為《廣播電視清潔法》的議案,要求禁掉八個臟字,引起全球媒體的高度矚目。
不過也有人對臟話持比較寬容的態度,認為男人罵臟話跟女人哭泣一樣,能緩解壓力,宣泄情緒,對身體健康有益。還有人認為使用口語暴力,有時可以緩解乃至避免肢體暴力,壓抑肢體的攻擊性。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但對臟話的正面效應不宜估計過高,它至多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吐一時之快。中國古代的戰爭中,兩軍對壘,主將照例先對罵一番,然后開打,恰如斗蟋蟀,先要撩撥它的觸須一樣。在這種場合,語言暴力就不是肢體暴力的緩沖器,而是催化劑。用臟話以惡制惡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2008年秋天,在北京松榆里社區某一棟樓內,貼出了一張“臟話公告”,臭罵一周三次在樓道內隨地大小便的行為。“公告”下方注明:“誰撕就是誰干的!”因為不愿背黑鍋,無人敢揭這張“公告”。結果由居委會出面,表示要調查處理行為不文明者,同時批評“公告”作者對居民造成“視覺污染”,表示一旦查明,也要追究作者的行為負責。
作為臟話的清潔劑是委婉語。如果說臟話把語言帶進了陰溝,那么委婉語就可能將臟話帶出陰溝。比如用“排泄物”代替屎尿,用“例假”“大姨媽”代替月經,用“胸”代替乳,用“下部”代替陰部。最有意思的是上廁所,一般場合稱之為“去一號”,“去洗手間”,“去衛生間”,“去化妝間”。我在韓國餐廳如廁,看門前掛有卷簾,上書“解憂處”三字,頓時感到這個排泄穢物的場所詩意盎然。有人還告訴我,臺灣有一個地方的男廁稱為“聽雨軒”,女廁稱為“觀瀑樓”,那就更顯雅致。當然,還應配有其他圖案作為標志,如在“聽雨軒”畫上煙斗或禮帽,在“觀瀑樓”畫上高跟鞋或紅嘴唇,否則誤入“白虎節堂”,勢必會引起誤會,產生尷尬。用委婉替代臟話固然可取,但也不能走向極端。1926年10月2日,周作人在《語絲》周刊第九十九期發表《違礙字樣》,批評出版界對“違礙字樣”的刪削和不必要的避諱。比如,由于神經過敏,連“子宮”都不敢寫,避諱作“子X”,甚至創造出一個怪字(“子”旁加一“宮”字)作為替代。像這種做法,可以說是步入魔道了。
語言是社會的一面鏡子,也是心靈的一面鏡子。從古至今,既然臟話是一種普遍的語言現象、文化現象,就有必要從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的角度進行綜合研究,乃至進行跨文化研究,目的是了解臟話產生的歷史原因、社會原因、個人原因以及遏制和消滅臟話的有效途徑。1923年12月,周作人應北京大學《歌謠周刊》紀念增刊之約,撰寫了一篇《猥褻的歌謠》,文中強調了該刊的一個重要觀點:“在學術上是無所謂卑猥或粗鄙的。”
從社會學的角度對臟話進行深入研究的首推魯迅。他在《論“他媽的”!》一文中指出,晉朝大重門第,子孫即使是酒囊飯袋,依靠祖先的余蔭仍然可以得官,所以要攻擊高門大族堅固的舊堡壘,就必然去瞄準他的血統。“他媽的”一類的臟話,便是在這種社會心理的支配下產生的。當然,這只是魯迅的一家之言,別的語言學家、民俗學家也還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臟話文化史》的作者也是從特定的歷史情境中分析臟話產生的原因。該書認為,在戰爭中清一色男性環境,生理和心理壓力極大,造成大量咒罵也就不足為奇。有一句世界廣泛流行的罵人話,就是由美國海軍陸戰隊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傳播開來的,因為對于處境險惡、離鄉背井的美國大兵,有這個情緒字眼可用是一種無可比擬的福氣,尤其是除此之外他幾乎一無所有。
竊以為,世界各國的臟話語多以母親做標靶,是因為罵語必須有冒犯性,能犯禁忌,從而引起對方的震怒。在人世間母愛最為神圣,最為偉大。褻瀆母親就是褻瀆神圣,因而最能侮辱對方的人格,傷害對方的感情。當然也有人把辱罵的對象上溯到祖母、外祖母甚至祖宗,或旁及到姨媽(如保加利亞語)、姐妹、小舅子。這類臟話肯定降低了辱罵的刺激性。在有些場合,臟話罵語也施之于物。比如不小心碰了頭,惱怒之時脫口就是一句臟話,這時只是一種本能的宣泄,沒有社會政治和倫理的內涵,就如同打嗝和生理排放一樣。
在當代中國,臟話泛濫成災是發生在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紅衛兵運動的推動,“國罵”堂而皇之地進入了革命造反派的紅色文獻。一時間,“他媽的”、“放他媽的屁”、“造他媽的反”一類豪言壯語充斥于大街小巷。我當時在北京一所中學任教,曾奉工宣隊之命撰寫一篇批判“走資派”的稿子。送審之后,工宣隊找我談話,認為稿子毫無戰斗性,辜負了組織期望。結果我被迫在一篇千字文中加入了五至十句“國罵”,才最終獲得通過。我的這一親身經歷說明,在那個“人妖顛倒是非淆”的時代,罵臟話就等同于革命。人性的扭曲、語言的扭曲竟到如此地步,實為古今中外歷史所罕見。這也證明了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
總的說來,罵臟話是一種消極的語言現象。用臟話罵人的方式并不可取。但罵可罵之人的可罵之處,跟罵不該罵之人的不該罵之處,還是有原則區別的。據已故賈植芳教授回憶,在1955年全國文聯批判胡風的運動中,郭沫若曾用五個字的“國罵”痛罵胡風。這件事散文家柳萌可以證實,相關文獻也能證實(見王春瑜:《瑣憶賈植芳》,《芳草地》2008年第4期,第65至66頁)。作為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學者,像這樣的歷史教訓是應該充分吸取的。
既然“出口成臟”并不是一件體面的事情,因而發明臟話絕不可能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雖然“發明者確是一個天才——然而是一個卑劣的天才”(魯迅語)。有趣的是,竟還有人爭奪臟話的發明權。這個人就是狂飆社的主將高長虹。為了擁有“他媽的”這三個字的知識產權,他在《1926,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中說:“直到現在還很風行的‘他媽的!那幾個字,便是《莽原》第一期我在《錦袍的世界》里才初次使用。”查這篇作品,結尾確有“他媽的”三個字,不是具體罵某個人,而是罵愛國者反被人斥為賣國這種社會現象。《莽原》周刊第一期出版于1925年4月24日,而魯迅的《論“他媽的!”》作于同年7月19日。高長虹的上述表白看來是要跟魯迅爭奪“他媽的”的發明權或首發權。但魯迅講得很清楚:“無論是誰,只要在中國過活,便總得常聽到‘他媽的或其相關的口頭禪。”可見“他媽的”這三個字早已有之,任何人想擁有這個詞的專利都是辦不到的。
消滅臟話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有人把罵人比喻為一種跟抽煙差不多的惡習。戒煙很難,但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戒掉。一個人一輩子絕對不罵一句臟話也很難,但隨著人類社會的日趨和諧,文明用語的日趨普及,用臟話罵人的陋習是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的。前些年最壯觀的罵人場面多出現在中國男足的賽場上。那萬人齊罵“傻X”的聲音,簡直可以上遏行云,下斷流水。但在今年北京的“兩奧會”上,這種罵聲已經絕跡,而代之以掌聲、歡呼和加油聲。外國運動員也報之以“謝謝北京”、“謝謝香港”、“謝謝青島”、“謝謝中國”等熱情友好的話語。可見經過提倡、引導,任何陋習都可以逐漸得到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