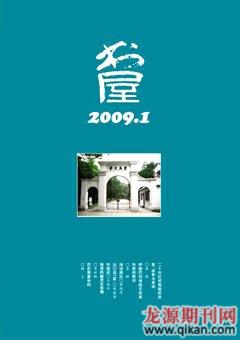過去教授的骨氣和底氣
肖燕雄
一
蔡元培先生為伸張大學的理想,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先后兩次公開發表自己的辭職啟事。一次是因抗議北洋軍閥政府干涉、鎮壓學生表達愛國感情的五四運動,蔡元培首先拒絕了當時的教育總長要其協助政府約束學生的請求,表示“學生愛國運動,我不忍制止”,然后于1919年5月9日,以“吾倦矣!……我欲小休矣”發表轟動全國的辭職啟事,之后不久(同年6月),蔡元培先生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中,陳述了三點理由:“(一)我絕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長:為了北京大學校長是簡任職,是半官僚性質……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無聊的照例的公牘,要是稍微破點例,就要呈教育部,候他批準……我是個痛惡官僚的人,能甘心仰這些官僚的鼻息嗎?(二)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的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哪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證法來干涉……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么?(三)我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北京是個臭蟲巢,無論何等高尚的人物,無論何等高尚的事業,一到北京,便都染了點臭蟲的氣味……難道還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嘗嘗這氣味么?”另一次是1923年1月19日,因目睹官僚政府的種種腐敗,蔡元培先生再次在各報端公開發表自己的辭職啟事:“……我自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以后,不知一天要見多少不愿見的人,說多少不愿說的話,看多少不愿看的信……實苦痛之極……不要人格,只要權力,這種惡劣的空氣一天天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1〕
1930年,光華大學政治系教授羅隆基在《新月》雜志上發表文章,主張維護人權。當時教育部飭令光華大學把羅隆基撤職。為此,張壽鏞校長于1931年1月19日呈文國民政府,文中說:“今旬奉部電遵照公布后,教員群起恐慌,以為學術自由從此打破,議論稍有不合,必將陷此覆轍,人人自危!”他還借蔣介石當時提出所謂“赦免政治犯”的言論,就題強調:“夫因政治而著于行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羅隆基僅以文字發表意見……略跡原心,意在匡救闕失。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擬請免予撤職處分,以示包容。”
抗戰期間,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遷至昆明,成立西南聯大,當時的云南省省長龍云曾給予聯大很大的支持。一日,龍云來校拜見聯大梅貽琦校長,說他兒子未考取聯大附中,請求破例收錄,梅校長稱不能破例,建議明年再考,他可以請老師為之晚上補習,但要收“家教費”。為維護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抗戰勝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的傅斯年也拒絕權貴子弟降格入學。為此,他特地在校長辦公室門上貼上一張字條:“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傅斯年!”維護大學理想和尊嚴的風骨,由此可見一斑。
過去大學里教授的權力之大和“敢言敢當”也是后人難以想象的。對于來自上邊的命令,如果感覺不合理,教授們要么據理力爭,要么就公開抗議,這一方面說明大學的民主空氣較濃,也說明廣大教師有很強的教育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1939年3月,陳立夫任教育部長后,為了加強對大學的控制,通過行政手段,對大學教育的很多方面強行統一管理。1939年至1940年間,陳立夫以教育部長身份三次訓令西南聯大必須遵守教育部核定應設的課程、統一全國院校教材、舉行統一考試等新規定。1940年,西南聯大教務會議就給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回了一封信,全信如下:
敬啟者,屢承示教育部廿八年十月十二日第二萬五千零三十八號、廿八年八月十二日高壹三字第一萬八千八百九十二號、廿九年五月四日高壹一字第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一號訓令,敬悉部中對于大學應設課程以及考核學生成績方法均有詳細規定,其各課程亦須呈部核示。部中重視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厭其詳,但準此以往則大學將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竊有未喻。
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日臻進步也。如牛津、劍橋即在同一大學之中,其各學院之內容亦大不相同,彼豈不能令其整齊劃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
今教部對于各大學束縛馳驟,有見于齊而無見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教部可視大學研究教學之成績,以為賞罰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孫中山先生權、能分立之說,則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設施,將使權能不分,責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師嚴而后道尊,亦可謂道尊而后師嚴。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之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準,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一科員之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學生尤啟輕視教授之念,與部中提倡導師制之意適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教部今日之員司多為昨日之教授,在學校則一籌不準其自展,在部中則忽然智周于萬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
然全國公私立大學程度不齊,教部訓令或系專為比較落后之大學而發,欲為之樹一標準,以便策其上進,別有苦心,亦可共諒,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請將本校作為第……號等訓令之例外。
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縱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若何之處,仍祈卓裁。此致常務委員會。
教務會議謹啟
廿九、六、十〔2〕
這封信由當時任文學院院長的馮友蘭起草執筆,但表達的是西南聯大校方領導階層的共識。這封信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至少說明了:自北大建校初期開創的兼容并蓄、學術自由、教育獨立的辦學傳統,至四十年代,已成北大、清華、南開等中國一流大學的基本辦學理念。而西南聯大能在抗戰期間艱苦卓絕的條件下成績斐然,人才輩出,成為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跡,也正是來源于對這一理念的堅守。
張奚若先生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專業是政治學,早年是很敢說話的人,后來雖然不大能說話了,但張先生的敢言還是很出名的。1949年后,張先生還勸過執政者不要好大喜功。西南聯大時期,有一次張先生去參加國民參政會,他發言抨擊國民黨的腐敗和蔣介石的獨裁,蔣介石打斷他的發言插話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離開會場回到昆明。下次參政會再開會時,他接到寄來的通知函和路費,當即回一電報:“無政可議,路費退回”,從此再不出席國民參政會〔3〕。1946年初,在舊政協開會前夕,張奚若應西南聯大學生會的邀請,作過一次演講,開講之前,他就說:“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這是客氣話。說得不客氣點,便是請他滾蛋。”
另一位張姓教授——張東蓀先生當年在上海光華大學教書的時候,在校務會議開會時,每次主席都要恭讀總理遺囑,有一次他即奪門而去,聲言:“下次如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真正是率真可愛。
二
以上這些可感可敬的言行史跡并不出自筆者的鉤沉功夫,國內外一些研究解放前大學和知識分子的學者陳平原、謝泳、傅國涌、薛涌等在他們的文章中都多多少少提到過這些事實。筆者不像他們,只激賞于或主要激賞于這些有骨氣的行為,而是在思考,為什么過去的教授那么有精神、有“士氣”,僅僅是因為個人的個性或人格使然?或者僅僅或主要因為——如謝泳所說,是當時教授的自由流動制度的原因?自由流動制度的本質又是什么?
謝泳統計過北大、清華、南開、北師大1949年前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動情況,“他們當中自由流動三次為一般規律,多的有流動四五次的,而流動的時間一般在三四年之間,最終落腳在一個自己比較理想的大學內”。他說,他之所以強調這種權利對大學教授的重要性,“是因為他們在謀生之外,有天然的關懷社會的責任,要主持公道,要批評政府,要通過寫文章辦報紙來伸張正義,這些特征決定了教授是一個主體性極強的群體……他們比其他階層要難于在一個固定的環境中長期呆下去,這時如果沒有自由流動的權利,對教授來說,實在太痛苦了……自由流動就成為他們最重要的生存方式”〔4〕。
的確,自由流動是教授錚錚鐵骨的淬火劑。但是,自由流動的保障機制是什么?謝泳說,自由流動的實現依賴于“整個社會的運行機制”,“還有教授的經濟地位”。前者說得太抽象,后者不好理解。具體而言,自由流動的實現端賴大學校長有聘用教師的實權、教授有管理學校的實權。如果老師的聘任權、管理權分散在社會各個職能部門,教師流動就不自由、不順暢。同時,校長要有經營大學的先進的理念和人格魅力,要以教授為大學發展的重心,不以“長官、老板”自居,最大限度地尊重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的大學核心價值觀。1929年7月國民政府制定的《大學組織法》第九條規定:“大學設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國立大學校長由國民政府任命之;省立市立大學校長,由省市政府分別呈請國民政府任命之。”
于法律制度的角度看,大校校長無疑均為“政府官員”,但從實際操作中觀察能明顯感到,不少人出任校長主要是基于教育理念和治校理想,不是為官而官,更不存在跑官要官之類,這一點可從當時一些人向政府當局提出的“任職前提條件”中找到不少佐證。1937年,云南省主席龍云聘熊慶來任云南大學校長,熊向龍提出的任職前提是:校務行政省政府不要加以干涉,校長有權招聘或解聘教職員,學生入學須經考試錄取而不憑條子介紹。這些都得到了龍的同意。1936年,蔣介石親自召見竺可楨,請他出任浙江大學校長。竺當時沒有表態同意,說要與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先生商量后再考慮。在征求蔡先生意見后,竺認為,若再不為浙大著想,而抱“明哲保身主義,則浙大必陷于黨部之手”,于是向當局提了三個條件:財政須源源接濟;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黨政干涉;時間以半年為限。除第三條外,都得到官方允準,竺可楨于是出任浙大校長。另外,不少校長主動限制自己既得的法定權力資源,不用政府機關行政命令的手段管理學校,也是過去這些大學校長贏得師生尊重的主要原因。過去的大學校長雖由政府任命,權力卻主動下放集中在由教授組成的評議會中,治校采取“無為而治”、“吾從眾”的謙虛態度(梅貽琦語)。1934年,國民政府下令取消當時一些大學設立的大學評議會、教授會、校務會等與《大學組織法》相抵觸的“土制度”,然而北大、清華及后來的西南聯大等大學卻始終堅持實行這一“民主治校制度”。朱自清先生有一段文字頗能反映當時的教授對校長的情感:“清華的民主制度,可以說誕生于十八年……但是這個制度究竟還是很脆弱的,若是沒有一位同情的校長的話。梅月涵先生是難得的這樣一位好校長……他使清華在這七八年里發展成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他使同仁覺著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
當時的校長是這樣,教育官員中也有極開明者。周炳琳(1892—1963),浙江黃巖人,1931年起長期擔任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兼法學院院長,抗戰時期擔任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教授,并一度兼任西南聯大法學院院長,還曾于1945年間一度擔任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會代理主席。1937年春,經蔡元培推薦,周炳琳出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在任期間,遇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強迫北京各大學解聘進步教授之事。他認為大學應有一定的學術自由,聘不聘教授的權力應歸大學校長,作為上級的教育部只能撤換校長,而不能解聘教授,頂住了黨部的這一無理要求。解放后,曹禺和巴金結伴來到北大教授宿舍看望周,對周執弟子之禮,十分尊敬。
大學是所有教授(師)的大學,教授(師)是所有大學的教授(師)。這就是教授自由流動的真正內涵。
有學者說,有錢,有自由流動的便利,過去的教授也就有了一個良好的精神狀態,也就敢怒敢言。此話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可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對魯迅的研究到現在,文獻資料可謂浩如煙海,但幾十年來少有人注意到他的經濟狀況。《魯迅全集》最后兩大卷是《魯迅日記》,七百多頁的《魯迅日記》中總共有幾千處是記錄他的經濟收入的。從1912年魯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職,一直到1936年去世,二十四年中,日記的主要內容就是記錄收入情況,魯迅總共收入十二萬多銀元,約合今天人民幣四百八十萬元。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庫門樓房的寫作環境。在殘酷無情的法西斯文化圍剿之中,魯迅能夠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堅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獨立人格,這得益于他殷實的收入。特別在生命的最后九年,魯迅在上海已經可以不要為幾個錢替“官場幫忙”或為“商場幫閑”,他完全靠版稅靠稿費生活,當時每月收入七百多元,相當于現在的兩萬多元。而當時上海一個四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費不到四十元。
1927年6月公布的《大學教員資格條例》二十條及《大學教員薪俸表》規定:教授一級月俸國幣五百元,約合今天人民幣一萬七千元;副教授一級月俸三百四十元,約合今天人民幣一萬二千元;講師一級月俸二百六十元,約合今天人民幣九千元;助教一級月俸一百八十元,約合今天人民幣六千多元。
顧頡剛1935年四十二歲時擔任北平研究院史學主任研究員,月薪四百元;仍兼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領取半薪一百六十元。月收入共五百六十元,約合今天人民幣兩萬元。加上他著述和編輯所得,年收入超過國幣一萬元(合今天人民幣三十到四十萬元)。1931年胡適之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月薪六百元,另外還有稿酬版稅收入。學者常有兼職,此項收入也不小,例如陳垣教授兼職所得月收入達一千五百元(合今天人民幣五萬元)。
國立清華大學提供給教授們的住宅是免費的。到了1935年初,聞一多、周培源、陳岱孫等教授遷入清華新南院,每人一棟,條件很好,有書房、臥室、餐廳、會客室、浴室、儲藏室,電話、熱水一應俱全。
前面分析的都是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的知識分子的經濟生活狀況,其中有一同也有一異。相同的是,過去的教授們都豐衣足食;不同的是,有人慷慨激昂,有人溫文爾雅。可見經濟寬裕并不是教授放膽進言的充分條件。不能保證,教授們有了很好的經濟收入就能堅持真理、鐵面“犯上”。換句話說,不能以此要求與魯迅同時代的有錢的知識分子都能夠像魯迅那樣成為“民族的脊梁”。同理,也不要寄希望于當今的某些善于走穴、敢于圈錢的經濟學教授能指斥權貴、秉公放言。那么是不是不同的性格使然?其實個人稟性也不是。有人說,魯迅在五十年代也無法生存。這說明,此時起關鍵作用的是外因,而不是內因。
三
以前學者說到過去教授的“犯上”,所舉事例集中于兩個時期,一是五四時期,二是抗戰時期。這兩個時期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亂世。所謂亂世,就是指分裂、分治社會,即統一政權行將解體或尚未建立之時。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次思想空前活躍、學術上百家爭鳴的局面,一次是春秋戰國時期,一次是在本世紀的五四運動前后。后一次發生在帝制取消但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共和建立但資本主義因素還相當微弱,世界各種新思想、新知識、新技術開始傳入但舊文化還根深蒂固的時候,對本世紀的中國帶來重大影響的種種思想基本都是在那時形成或開始傳播的,對政治、文化和思想起重大作用的領袖人物,大多也是從那時開始步入歷史舞臺的。
五四運動前后中國名義上存在著一個統一的中華民國,實際上北京的政府政令所及不過數省,其余則由各種勢力控制或占據,另外還有國中之國的列強租界和勢力范圍,數省甚至一省也不相統屬。在五四時期,儒家學說雖還有相當濃厚的基礎,但已經失去專制政權在法律上確立的特殊地位;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的思想都還處在傳播階段,沒有哪一種已經取得絕對優勢或為統治者所正式承認。各種意識形態擁有比較平等的競爭資格。抗戰時期,由于國家分裂,外敵臨門,國民普遍存在憂患意識,統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迫切需要尋求救國之道,因而風花雪月的游戲文字、鶯歌燕舞的升平頌歌無人欣賞,倒是國將不國的大聲疾呼會引起共鳴。
對傳統思想和制度的厭倦和失望使人們迫切尋求新的思想,向往新的社會。而且各政權、各地區之間在根本利益或具體利益上的矛盾,制度、政策上的種種差異,為各種思想學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不同觀點,客觀上提供了保護傘和庇護所。同時,統治者因忙于爭斗,或為了顯示其開明,對不直接危及其統治的思想言論往往不予置理或無暇顧及。
正是這種“疏于管理”的狀態釀成了一片放言“犯上”的現實土壤,催生了無數進步的大學理念和開明的教育人士。管理寬松才有活力,才出思想,沒有念緊箍咒念出來的思想家、學問家。正因為如此,著名電影演員趙丹說:“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此話推廣到其他領域也適用。
據坊間傳聞,大學本科教學水平評估開始之時,一些教育部直屬高校不以為然,壓根兒不把它當一回事,因為在它們看來,社會和公眾早已認同它們為“優秀”,而無需教育部多此一舉。但是,官方立刻明以事理、曉以利害,再牛氣的學校也就只好開門“納迎”。
2007年1月25日,教育部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透露,“十一五”期間我國將投入二十五億元,實施“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投資規模在新中國教育史上尚屬首次。教育部官員針對二十五億元的投入方向對在場記者解釋說,這些投入將通過公開招標、申辦等形式,建設一萬種高質量教材、三千門國家級精品課程和三千個特色專業點;遴選一千個國家級教學團隊;建設五百個實驗教學示范中心、五百個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和五百門國家級雙語教學示范課程;獎勵五百名國家級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等。有如此大的投入作指揮棒,所有的高校一律噤聲,紛紛趨之若鶩。
筆者想,如果過去的大學教授要面對當今這么多有誘惑力的“項目”和“工程”,而且它們還與教授定級、津貼掛鉤,他們肯定也沒了脾氣。
注釋:
〔1〕《蔡元培全集》,中華書局1984年版。
〔2〕參見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張奚若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4〕謝泳:《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