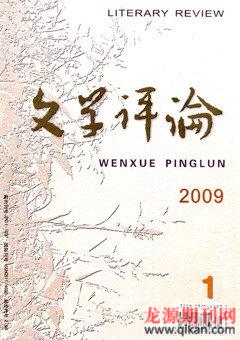宋詞中的雙城敘事
張文利
內容提要作為宋代依次出現的兩個都城,汴京和杭州曾經是演出過無數歷史悲喜劇的活動舞臺,一直為兩宋詞人所矚目。兩都的山川形勢、市井風貌、享樂休閑在宋詞中都有鮮活的描繪,不同詞人筆下的兩都亦具不同面目。兩都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投射出不同的文化映像,透露出國運的盛衰興亡和詞客的感喟嘆息。江山勝跡之助、文士詞客的飄零聚散、詞學風氣的嬗變,使杭州詞無論數量還是藝術特色,與汴京詞風貌迥異。從社會文化學和都城地理學的角度解讀宋詞中的雙城映像,可以看出政治氣運與文化軸心的移動如何造成城市映像與文化記憶的潛轉暗換。
作為國家政治文化中心的都城,其盛衰榮枯具有多種特別的象征符號意義,而城市的映像亦如森林中樹木的年輪,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積淀為復雜的文化記憶。《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筑,都日城。”《春秋·公羊傳》桓公九年:“京師者何?天子所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在前現代社會中,都城除流動與固定人口眾多、中央官署機構鱗次櫛比外,還有無法遷徙的帝王宗廟。法國地理學家菲利普·潘什梅爾說:“城市既是一個景觀、一片經濟空間、一種人口密度;也是一個生活中心和勞動中心;更具體點說,也可能是一種氣氛、一種特征或者一個靈魂。”美國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學派指出:“城市,它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各種禮俗和傳統構成的整體。換言之,城市絕非簡單的物質現象,絕非簡單的人工構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的各種重要活動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產物,而尤其是人類屬性的產物。”中西城市理論中有某些暗合處。汴京與杭州作為宋代先后出現的兩個都城,從都城發展史上看,具有明顯的東遷南移的特色。都城的遷徒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時代與社會的巨變,在宋詞中有何保留,有何積淀,如何被聚焦,又如何逐漸淡出?本文擬移形換步,調整視角,從小碎片看大歷史,追尋宋代兩都詞中錯綜復雜的文化映像和歷史記憶。
一
開封,曾是戰國時期魏國的都城,唐末五代時的后梁、后晉、后漢、后周等先后建都于此。公元960年建立的趙宋政權,仍以開封為都,稱為汴京、汴梁④。北宋是開封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盡管歷史學家對宋廷向來有積貧積弱的譏議,但它畢竟是經過晚唐五代幾十年戰亂后的嶄新的統一政權,百廢待舉,萬象更新。趙宋立國伊始,太祖為了防止大權旁落,杯酒釋兵權,推行修文偃武的政策,在“多積金、市田宅,歌兒舞女以養天年”的圣訓下,社會上興起普遍的享樂休閑風氣。經過一段時期的休養生息,北宋經濟得到極大的恢復和發展,汴京城水驛池亭,煙花柳巷,笙歌鼎沸,車水馬龍,呈現出繁榮奢華的帝里風光。文人騷客對于汴京的描述,不僅在于它的山川形勢、風土人情,更著重表現其經濟繁榮,奢華享樂的承平氣象。汴京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宋詞中有所體現,茲舉其著者如下:
宴飲。晏殊有一首《拂霓裳》詞:“喜秋成。見千門萬戶樂升平。金風細,玉池波浪毅文生。宿露沾羅幕,微涼入畫屏。張綺宴,傍熏爐蕙炷、和新聲。神仙雅會,會此日,象蓬瀛。管弦清,旋翻紅袖學飛瓊。光陰無暫住,歡醉有閑情。祝辰星。愿百千為壽、獻瑤觥。”詞篇選取詞人最熟悉的宴飲場面,極寫富貴生活,并不停留于表面的金玉錦繡,而重在表現閑雅富貴的氣象,那神仙般的雅會和歡醉的閑情,展現著一幅太平盛世的畫卷。如果說富貴宰相晏殊的宴飲詞表現了王公貴族酣酒沉醉的高華氣象,那么,市井詞人柳永的宴飲詞,則給我們提供了廣大平民階層的享樂情形:“玉城金階舞舜干。朝野多歡。九衢三市風光麗,正萬家、急管繁弦。鳳樓臨綺陌,嘉氣非煙。雅俗熙熙物態妍。忍負芳年。笑筵歌席連昏晝,任旗亭、斗酒十千。賞心何處好,惟有尊前。”(《看花回》二)由此可知,汴京城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士,都同樣享受著宴飲的歡愉和刺激。
游冶。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描述汴京城“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可知汴京風流恣肆的夜生活的一面。柳永青年時一度居住京城,風流倜儻的青年才子,出入于歌樓舞榭,倚紅偎翠,遍享風流,筆下的帝城風光,自然少不了溫柔鄉的氣息。多年后,詞人飽經宦途蹭蹬,遍嘗生活艱辛,回憶中念念不忘的還是當年的風流旖旎:“戀帝里,金谷園林,平康巷陌,觸處繁華,連日疏狂,未嘗輕負,寸心雙眼。況佳人、盡天外行云,掌上飛燕。向玳筵、一一皆妙選。長是因酒沉迷,被花縈絆。”(《鳳歸云》)“朝野多歡”,又值“九衢三市風光麗”,恣肆的冶游和放蕩順理成章。據史料記載,當時汴河沿岸,尤其是汴京城東南角一帶,歌館甚多,游客如云,文人士子與歌兒舞女的歡情屢屢在這里上演,城市變形為欲望的舟車,癲狂與放縱成了城市生活中的固定節目。
節令。宋人金盈之《醉翁談錄》中云:“都城以寒食、冬至、元旦為三大節。”非常隆重。事實上,除這三大節以外,其他如上元、端午、七夕、中秋、重陽等節日也相當熱鬧。尤其是上元節,在兩宋時期一直都是詞人們津津樂道的盛大節日。太祖乾德五年(967)下詔“上元張燈,舊止三夜,今朝廷無事,……具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太宗太平興國六年(981)又將“燃燈五夜著為令”。兩宋時期,除特殊情況外,舉辦大型燈會,演出百戲,成為上元燈節的習俗。關于上元燈節的詞作非常多,如柳永《玉樓春》(其三)詞云:“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風光盈綺陌。金絲玉管咽春空,蠟炬蘭燈燒曉色。鳳樓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鴆鷺客。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殺云蹤并雨跡。”描繪上元節之夜,京城張燈結彩,游人如織,通宵達旦的游樂情形。這種徹夜游歡正反映了宋代坊里禁宵制度被打破后帶來的城市生活的新變化。
周邦彥也有一首描寫汴京上元燈節的詞作:
風銷焰蠟,露澠烘爐,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香麝。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門如晝,嬉笑游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唯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解語花》(高平·元宵))
上元之夜,火樹銀花,星雨魚龍,都人往往傾城游賞,那些平日深閉閨門的女子也得以加入這傾城的狂歡。夜色掩映下,男女相會于柳陌花衢,風流歡洽在所不免,周邦彥懷念的就是這樣一場風花雪月的愛情故事。上元節是宋詞里的愛情多發時節,宋詞中愛情故事的背景或舞臺大多被放置于都城的上元燈節。
由以上數例可知,北宋詞人描寫汴京,多是從其作為大都市的繁華奢靡的角度人手,著重表現它作為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繁榮景象。部分詞人如柳永、周邦彥等,亦將自己情感生活的風流旖旎交織進去。與此相應,《東京夢華錄》記述北宋后期徽宗朝汴京的繁榮面貌,即側重經濟、民俗等方面,凸現了其作為都城特有的富麗堂皇和帝城氣派。王安石嘗云:“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
面內而依仿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揭橥了汴京之所以奢侈綺靡的原因,頗有道理。而關于汴京的自然形勝描寫,在詞中并不多見。汴京城里最著名的娛樂場所應是金明池,一如杭州之西湖。但金明池并非天然池苑,乃是宋廷在舊有教船池基礎上開鑿疏擴而成,本為教習水戰。開鑿之初,金明池水戰仍有一定的軍事演習意義,至北宋中期,才逐漸演變成表演性的水上游樂活動場所,但因其乃宮廷池苑,故只有王公貴族有機會經常賞玩,一般士庶惟有每年春季“開池”期間才能有幸目睹身歷。汴京地平野闊,農業發達,但北方之蒼茫遼闊實難與南方之清麗明秀相媲美,而人的本性中有著親近自然、樂山樂水的自然情結。徽宗朝的“花石綱”事件,禍國害民之甚已成定論,但如換一個角度看,它正從一定意義上反映了北宋君臣對于南方山水景致的喜好渴慕和以政權為后盾的強力攫取。
而文人對于杭州的描寫,則多一個角度,即自然名勝。吳自牧《夢梁錄》記述臨安情形,除像《東京夢華錄》中對汴京那樣的記載內容外,還專門描繪杭州的風景名勝,對西湖、錢潮及其他池沼苑囿,奇珍異玩等,都有所涉及。周密《武林舊事》亦有同樣的記載。杭州地理位置優越,氣候條件良好,嘉山秀水,引人入勝,從北宋起,詞人就多有詠寫杭州的優秀篇章,如柳永的《望海潮·三吳都會》詞,點面結合,縱橫捭闔,鋪陳揚厲,寫盡錢塘風光,幾成絕唱。范鎮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鎮在翰苑十余載,不能出一語歌詠,乃于耆卿詞見之。”
《夢梁錄》記載:“臨安風俗,四時奢侈,賞玩殆無虛日。西有湖光可愛,東有江潮堪觀,皆絕景也。”(卷四“觀潮”)西湖之陰柔靜美與錢塘之陽剛雄肆,構成杭州兩大絕景奇觀。北宋初潘閬有《酒泉子》組詞,其中兩首分別描寫西湖的春景和秋景:
長憶西湖,湖上春來無限景。吳姬個個是神仙。競泛木蘭船。樓臺簇簇疑蓬島。野人祗合其中老。別來已是二十年。東望眼將穿。(其三)
長憶西湖,盡日憑闌樓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里:白鳥成行忽驚起。別來閑整釣魚竿。思入水云寒。(其四)
前詞寫春天西湖無限風光,吳女競泛蘭舟,宛若神仙,亭臺樓閣亦仿佛仙境,使人愿身老其中而無憾。后詞寫秋天西湖垂釣,漁舟散落,笛聲悠邈,蘆花飛揚,白鳥成行。兩首詞一秾艷一清雅,寫出西湖春秋兩季的不同景致,堪稱圖畫。南宋楊無咎的《水龍吟》(趙祖文畫西湖圖,名日總相宜),則融化西湖典故及前人有關西湖的詩句入詞,給西湖美麗的自然景觀增添了醇厚的人文氣韻。
潘閬描寫錢塘觀潮,亦極有氣勢:
長憶觀潮,滿郭入爭江上望。來疑滄海盡成空。萬面鼓聲中。弄濤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別來幾向夢中看。夢覺尚心寒。(《酒泉子》其十)此詞寫錢塘江潮,驚心動魄。上闋寫錢塘百姓傾城而出的觀潮情景,“來疑”兩句,極寫江潮的壯闊氣勢。過片寫錢塘弄潮兒的過人膽量和高超技藝,鮮明生動,令人過目難忘。結兩句寫夢中錢塘潮,“夢覺尚心寒”一句,以夸張的筆墨,補足錢塘潮撼人心魄的雄壯氣勢。詞作波瀾壯闊,跌宕生姿,堪稱佳制。
總而言之,較之對汴京作為都城的繁榮奢華的較為單一的表現,宋代詞人描寫杭州,則不僅寫其繁盛氣象,而且大量描摹杭州的自然形勝。換言之,汴京詞多寫人事,杭州詞則除夸耀人事外,更注重對自然形勝的展示描繪。余杭佳麗,山水娛人,中原板蕩,恢復難期,南宋朝臣大多避世情深,匡時意少,雖為城市留下精美的詞章,也為歷史留下無盡的遺憾。
二
都城,是一國政治的中心,比其它地方更能反映出國運的盛衰興亡,誠如王國維所言:“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征也。”宋代詞人筆下的汴京和杭州,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投射下不同的映像,反映出不同的時代風濤和歷史變幻。
仁宗時期,經過內外修治,宋廷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盛世景象,所謂“隆宋”,常常得以與“盛唐”相提并論。這一時期的詞作中出現了較多描寫都市繁華氣象的篇章,其中汴京更為詞人所關注,如柳永、張先、蘇軾、王安石等都有佳作。徽宗朝時期,盡管宋廷面臨嚴重內憂外患,但表面上,社會經濟依然維持著盛世的繁華,朝野上下依然一派歡顏。關于此,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自序》中的這段話最常為人所征引:
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琦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游,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奢侈則長人精神。……
萬俟詠的《醉蓬萊》,則以詞的形式形象展示了汴京生活綺麗奢靡的一面:
正波泛銀漢,漏滴銅壺,上元佳致。絳燭銀燈,若繁星連綴。明月逐人,暗塵隨馬,盡五陵豪貴。鬢惹烏云,裙拖湘水,誰家姝麗。金闕南邊,彩山北面,接地羅綺,沸天歌吹。六曲屏開,擁三千珠翠。帝樂口深,鳳爐煙噴,望舜顏瞻禮。太平無事,君臣宴樂,黎民歡醉。
詞里一幅太平盛世景象。徽宗詞壇是汴京詞創作的高峰期,徽宗君臣是汴京詞的創作主體。他們權勢赫赫,養尊處優,其筆下的汴京詞帶有明顯的富貴氣和奢靡氣,諛頌之風更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南北之交,局勢動蕩,汴京風雨飄搖,徽宗君臣卻無視現實,繼續沉湎于歌舞享樂,繼續夸飾著奢靡生活,直到敵虜的鐵蹄踏碎了他們的太平享樂夢。徽宗被擄北上,淪為亡國囚后,這個享樂皇帝也發出了哀嘆。其《燕山亭》(北行見杏花)詞想像舊時宮中明媚艷麗的花朵,在無情風雨的摧折下,飛紅凋零,宮苑凄涼。看似寫花,實為寫人,有人物皆非的悲慨。
靖康之難后,半壁江山淪入敵手,汴京城不再是宋人涉足游歷的富貴地,兵燹過后,廢池喬木,猶厭言兵。從此,汴京退居到宋人的筆下和夢中,成為他們心中不能輕易觸碰的傷痛,偶爾提及,亦是無限凄楚。如朱敦儒《浪淘沙》中秋陰雨,同顯忠、椿年、諒之坐寺門作:
圓月又中秋。南海西頭。蠻云瘴雨晚難收。北客相逢彈淚坐,合恨分愁。無酒可銷憂。但說皇州。天家官闕酒家樓。今夜只應清汴水,嗚咽東流。中原淪喪,南北對峙。流落南方的士人懷念故土,回憶中的汴京,一片凄風苦雨。而淪陷北方的宋人更是傷情。靖康之變后,盤踞北方的女真族在宴飲場景中依然演奏宋廷的教坊舊曲,北人昕了,自然觸傷心事。“凝碧舊池頭,一聽管弦凄切。多少梨園聲在,總不堪華發。杏花無處避春愁,也傍野煙發。惟有御溝聲斷,似知人嗚咽。”(韓元吉《好事近》(汴京賜宴聞教坊樂有感))詞作寫得很是凄涼。隨著南北對峙局面的形成,汴京漸漸淡出了詞人的視野,中原成了遙遠的回憶。宋亡后,宋人的故國哀思寄托在臨安城上,汴京被進一步虛化、距離化,最后化為一片空白,
成了一段被忘卻的歷史。
“長憶錢塘,不是人寰是天上。”(潘閬《酒泉子》其一)北宋時期,錢塘即是繁榮富庶的江南水鄉城市,而且俗好奢華。史書記載:“(兩浙路)俗奢靡而無積聚,厚于滋味。”蘇軾在杭為官,對此深有體會:“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為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對于雅好山水的文人來說,杭州的自然勝景比其經濟的繁華更具魅力。文人墨客徜徉于青山秀水之間,流連忘返。在蔡襄、蘇軾等人的詩文中,都留下了他們杭州為官時期游蹤的詳細記述。“此景出關無,西州空畫圖”(張先《醉垂鞭》(錢塘送祖擇之)),杭州的秀美風景被文人詞客反復吟詠贊美。高宗移蹕,杭州一躍成為政治文化的中心,城市規模空前擴大,繁盛富麗非往昔可比。據周煇記載:“嘗見故老言,(杭州)昔歲風物,與今不同。四隅皆空迥,人跡不到。……自六蜚駐蹕,日益繁盛。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王公貴族的南遷,把汴京的享樂習氣帶到杭州,一大批北方的文人來到杭州,為杭州注入了豐富的文化因子,杭州變得更為富麗奢華,游賞侈靡之風更熾。“杭人喜邀……今為帝都,則其益務侈靡相夸,佚樂自肆也”。不僅豪奢之家如此,貧乏之人,亦喜游玩,甚至不惜代價。“至如貧者,亦解質借兌,帶妻挾子,竟日嬉游,不醉不歸。此邦風俗,自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由此可知臨安城里全民享樂風氣之盛。楊澤民《風流子》(詠錢塘)詞云:
佳勝古錢塘。帝居麗、金屋對昭陽。有風月九衢,鳳皇雙闕,萬年芳樹,千雉宮墻。戶十萬,家家堆錦繡,處處鼓笙簧。三竺勝游,兩峰奇觀,涌金仙舸,豐樂霞觴。
芙蓉城何似,樓臺簇中禁,簾卷東廂。盈望虎貔分列,鴛鷺成行。向玉宇夜深,時聞天樂,絳霄風軟,吹下爐香。惟恨小臣資淺,朝覲猶妨。
詞里竭力營造君臣和樂、舉國歡慶的場景,然而與柳永《望海潮》詞相比,多了都城的綺麗奢華,卻少了國泰民安的太平氣象。都城是一國政治的中心,也是政治最敏感的晴雨表,不同時期文人筆下的都城風貌潛藏著那個時代的氣息和政治的脈動,是國運直接的表征。南宋朝廷從汴梁移蹕臨安,顯露出政治上從平和中立到防御退避的大轉變,國運氣數已遠不能和北宋相比。兩首錢塘詞的差異中,隱伏著國脈氣運的潛轉暗換。
茲以西湖詞為例,來看南宋杭州詞的歷史變遷。“南北戰爭,惟有西湖,長如太平。”(陳人杰《沁園春》)無論戰爭還是和平,西湖都是享樂者的天堂。南宋詞人大量詠寫西湖景觀,張矩、陳允平、周密還先后作有“西湖十詠”組詞,一一描繪西湖各個佳處。“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林升《過臨安邸》)西湖上夜夜笙歌通宵達旦,日日游龍穿梭不息。據《武林舊事》記載,當時西湖上“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癡幾騃子,密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為過也。”
文人筆下的西湖是雅集之地。朱敦儒《聲聲慢》(雪)詞云:
紅爐圍錦,翠幄盤雕,樓前萬里同云。青雀窺窗,來報瑞雪紛紛。開簾放教飄灑,度華筵、飛入金尊。斗迎面,看美人呵手,旋澠羅巾。莫說梁園往事,休更羨、越溪訪戴幽人。此日西湖真境,圣治中興。直須聽歌按舞,任留香、滿酌杯深。最好是,賀豐年、天下太平。瑞雪紛紛,紅爐圍錦,紅巾翠袖,聽歌按舞,這就是半壁江山里的貴族們的享樂生活。柔媚的西湖水,浸軟了男兒的鐵骨,怯懦的南宋,連殘山剩水亦將不保。南宋后期,風雨飄搖中的杭州岌岌可危,經臨西湖,涌上士人心頭的是此景不再的悲慨。吳文英《西平樂慢》云:
中呂商·過西湖先賢堂,傷今感昔,泫然出涕。
岸壓郵亭,路欹華表,堤樹舊色依依。紅索新晴,翠陰寒食,天涯倦客重歸。嘆廢綠平煙帶苑,幽渚塵香蕩晚,當時燕子,無言對立斜暉。追念吟風賞月,十載事,夢惹綠楊絲。畫船為市,夭妝艷水。日落云沉,人換春移。誰更與、苔根洗石,菊井招魂,漫省連車載酒,立馬臨花,猶認蔫紅傍路枝。歌斷宴闌,榮華露草,冷落山丘,到此徘徊,細雨西城,羊曇醉后花飛。
先賢堂,亦名集賢堂,位于西湖南山,系為紀念自先秦至北宋一千余年出生或生活在杭州的名人而建,宋末兵燹后不久而廢。詞人在作品中融織了對歷史人物命運浮沉的感喟和自己的身世情懷,西湖因此帶上了悲涼蕭瑟的意味。
宋亡后,遺民詞中的錢塘和西湖,更是一片悲苦。面對敵虜踐踏過后的西湖,詞人感嘆:“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說。”(詹玉《齊天樂》(贈童甕天兵后歸杭))此刻,西湖的春景這般凄涼:
接葉巢鶯,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更凄然。萬綠西冷,一抹荒煙。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韋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閑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鵑。(張炎(《高陽臺》(西湖春感))((武林舊事》記載“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卷3)而張炎眼中的西湖春景,卻是“萬綠西冷,一抹荒煙”、“苔深韋曲,草暗斜川”,飛花啼鵑,惹起新愁舊恨,滿目凄然。詞人飽嘗憂患的心理以及西湖的破敗景象令人感慨不已。我們由不同歷史時期文士對西湖的描繪,可以感受到寄寓其中的不同心態和人生況味,也能認識到政治的翻云覆雨烙燙在自然風物上的印痕。
三
兩都詞的面貌并不均衡。從數量看,杭州詞明顯多于汴京詞;從藝術特色看,杭州詞與汴京詞風貌迥異。究其原因,大略有如下數端;
第一,南北宋詞創作的不平衡使然。北宋詞總的數量少于南宋,其都邑詞數量亦少于南宋,汴京詞因此少于杭州詞。
第二,詞學風氣使然。都邑詞在宋詞中所占比例并不高。詞之源起,蓋為酒席宴前的佐酒助歡,娛賓遣興,表現男歡女愛的幽怨纏綿乃詞之主調。柳永始大量寫作都邑詞,《樂章集》中描寫城市繁盛景象者有四十余首,占其總數的五分之一強,這在當時是極為突出的。柳永之外,張先、蘇軾、王安石等人亦有此類作品,但并未形成風氣。在文人以詩為詞、以文為詞等諸種努力下,詞體堂廡漸大,幾于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為。南渡以后,雖然只剩半壁江山,但朝廷的享樂風氣依舊,江南的秀美風景又為這種享樂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城市風光尤其杭州景致為文人所樂道,詞中出現了較多詠寫都市風光的篇什。故從詞學風氣的轉移看,杭州詞多于汴京詞。
第三,陪都文化的影響使然。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陪都現象,對宋詞中的汴京和杭州形象也有影響。北宋汴京以洛陽為陪都,不同于汴京作為政治權力中心的存在,“宋代西京洛陽更顯文化之都、學術之都、藝術之都的特點與魅力。”洛陽的風采不僅吸引了眾多的文人學士矚目流連,魁杰賢豪、權貴耆舊亦多聚集于此,冠蓋相望,文人士大夫的群體活動相當活躍。如歐陽修的八老會、司馬光
等人的洛陽耆英會等,均是當時的政壇要客、文墨翹楚參與其中的雅集盛會。“北宋時期是洛陽文化史上又一輝煌時代,在一定程度上與開封形成對峙或起補充作用。”可以說,洛陽在文化、學術,藝術方面的優長和魅力,與汴京在政治方面的權力和威嚴,襯托互補,各顯清輝,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汴京的光芒。南宋臨安以建康(今江蘇南京)為“行都”,相當于陪都。由于偏安一隅,南宋版圖大為縮小,建康成為南宋與金對峙的前線,傳統意義上的陪都作用幾乎蕩然無存,沒有陪都來分割其地位和重要性,杭州更顯其獨尊之勢。
第四,地理環境使然。汴京位處中原,地平野闊,農業發達。宋之前,曾經是幾個小國的都城,但不見輝煌。宋廷建都于此,蓋緣后周都于此,不過因勢而然。汴京城之勝,在于其作為都城的獨特地位,在于其作為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重要價值。詞人筆下的汴京,亦著力刻畫表現的是這一方面。杭州長期以來都是南方重要的大城市,宋室南遷,更使它一躍而為都城,成為南宋中心,獲得與北宋汴京同等的重要性。但杭州之勝,還在于其秀麗的自然風景。嘉山秀水,為杭州增添了無窮魅力,王公貴族,文人士子,乃至販夫走卒,都得以享受其山水之美。文人們詞的創作更是得益于山水之助。杭州詞,一方面同汴京詞一樣,表現其大都市的繁華,另一方面,則是對其秀麗山水的描繪。繁華和秀美融織在一起,使杭州散發出迷人的光彩,杭州詞因此繽紛多姿,引人入勝。
第五,詞人審美趣味使然。相對于北宋詞風,南宋詞尚雅風氣較濃。雅情、雅景、雅志、雅語,凡雅者,皆易入詞人法眼。徜徉于杭州秀美的山水間,把酒言歡,吟詩作賦,是文人士子的賞心樂事。杭州詞因此勝出。
第六,風格不同使然。城市的不同面貌和風情,以及詞人的不同創作心境,形成了兩都詞的不同風格。汴京以繁榮奢華勝,汴京詞著重刻畫其作為都城的帝里風光,天子腳下的皇家氣派,氣勢開闊,富麗堂皇。杭州詞既寫繁榮氣象,也寫秀麗景致。由于描摹對象和寄托情感的不同,杭州詞具有不同的風格面貌,或雄偉壯闊,或慷慨激昂,或婉約柔媚,或幽默詼諧。
四
城市的面貌隨著時光的推移,國運的興衰而變化,彼與此的差異,今與昔的不同,都傳達出盛衰興亡的信息,躍動著文人要眇幽微的心曲,兩都詞因此較多地運用了對比尤其是今昔對比的表現手法。有汴京的今昔對比。如李琳《木蘭花慢》(汴京):
蕊珠仙馭遠,橫羽葆、簇蛻旌。甚鸞月流輝,鳳云布彩,翠繞蓬瀛。舞衣怯環珮冷,問梨園、幾度沸歌聲。夢里芝田八駿,禁中花漏三更。繁華一瞬化飛塵,鄻路動灰平。恨碧滅煙銷,紅凋露粉,寂寞秋城。興亡事空陳跡,只青山、淡淡夕陽明。懶向沙鷗說得,柳風吹上旗亭。
詞篇上下闋對比汴京城今昔,昔時風云月露,鶯歌燕舞,今日紅凋碧謝,灰飛煙滅。兩相比照之下,眼下的汴京城慘痛凄涼,彌漫著衰敗肅殺的悲劇色彩。
也有杭州的今昔對比,尤以西湖更著。如張矩《摸魚兒》(重過西湖):
又吳塵、暗斑吟袖,西湖深處能浣。晴云片片平波影,飛趁棹歌聲遠。回首喚。仿佛記、春風共載斜陽岸。輕攜分短。悵柳密藏橋,煙濃斷徑,隔水語音換。思量遍。前度高陽酒伴。離蹤悲事何限。雙峰塔露書空穎,情共暮鴉盤轉。歸興懶。悄不似、留眠水國蓮香畔。燈簾暈滿。正蠹帙逢迎,沉煤半冷,風雨閉宵館。
此詞對比作者兩次游覽西湖的情景,前次的春風共度與后次的風雨閉館形成對照,寄寓人事皆非的感慨。
而將汴京與杭州加以比照,更為常見。向子譚的詞分為“江南新詞”和“江北舊詞”兩部分,江北舊詞沿襲傳統詞風,以兒女情長居多,江南新詞則表現了家國之恨。如這首詞:
紫禁煙花一萬重。鰲山宮闕倚晴空。玉皇端拱彤云上,人物嬉游陸海中。星轉斗,駕回龍。五侯池館醉春風。而今白發三千丈,愁對寒燈數點紅。(《鷓鴣天》(有懷京師上元,與韓叔夏司諫、王夏卿侍郎、曹仲谷少卿同賦))
詞作回憶汴京上元燈節火樹銀花、萬民嬉游的熱鬧場景,與自己眼下衰老愁苦、獨對寒燈的情形構成鮮明對比。親身游歷的似錦繁華隨風而逝,曾經的萬里江山化為記憶印痕,詞人感情非常沉痛。又如李清照《永遇樂》: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捻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詞篇對比汴京與杭州的元夕。上闋寫杭州元夕,酒朋詩侶邀約詞人去觀賞燈節,詞人無心游賞,謝絕推托。下闋回憶少女時代在汴京城度過的元宵佳節。結篇又回到眼前,那“風鬟霜鬢”的憔悴的嫠婦形象,與當年汴京元夕花枝招展、無憂無慮的幸福少女有云泥之別。這其中,既有詞人個人遭際的不幸,更反映出國家命運的動蕩變幻給個人生活帶來的山傾海覆般的大不幸。李清照、向子誣在杭憶汴,比照杭州與汴京今昔上元燈節,通過不同的都市節日映像,反映時代風濤的激蕩翻覆和個人命運的天壤變化,感慨沉重。
城市是凝固的風景,也是流動的文化。作為特殊的文化記憶,宋代詞人的兩都敘事,有著觀測視角的轉移變化。既有內觀視角,如在汴京看汴京,在杭州看杭州,是目擊身歷的體驗,具有真實的再現性特征。也有外觀視角,如從杭州看(回憶)汴京,從其他城市看(回憶)杭州等。記憶映像同真實映像比較起來,帶有更顯著的表現性特征,因為記憶映像的選擇,本身就具有傾向性。視角的轉移騰挪,不僅帶來景色的變化,也融織著情感的不同況味。而由體驗到眺望,由眺望到回憶,由寫實到寫意,由憶汴京到憶杭州,這種潛轉暗移包含著氣運的此消彼長。從北望不見,作為城市鮮活視像的汴京逐漸淡化,到北憶不見,作為文化記憶的精神家園逐漸消失,再到南望不見,南憶淡化,兩都視像從現實到虛擬,驗證著兩宋的現實被虛化為記憶中的一段印痕、詞史上的一些零碎的文字意象。宋詞里的汴京和杭州,由濃墨重彩的抒寫,到被淡化、虛化乃至遺忘,正記錄了這兩個游樂地的先后湮滅,兩個精神家園的先后喪失的歷程。社稷宗廟被侵凌的城市不再是都城,悲愴的文化記憶被撫平被虛化后,人物的角色和身份也發生改變。作為道具的城市名稱未變,但活動舞臺上的劇目發生了巨大變化,兩個城市以及士子詞客們,與時俱變,又將在新的劇目中扮演新的角色。
責任編輯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