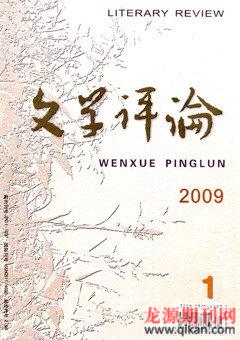反抗時間:文學與懷舊
馬大康
內容提要文學懷舊常常與故鄉、童年、舊交聯系在一起。但是,現代懷舊卻主要寓于現代化所帶來的文化變遷:都市生活對人的自然狀態的異化,對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疏離,金錢的“脫域”功能對種種聯系的抽象,以及現代人對“現在”的集體不信任,都迫使人借文學懷舊作為心理補償。對于移民作家來說,懷舊則更多根源于文化身份認同危機。懷舊文學中交織著兩種時間:過去與現在;疊印著雙重視野:作家過去之“我”的視野與現在之“我”的視野;摻雜著多種價值判斷:情感和審美的判斷與社會歷史的判斷。由此構成的敘述張力,賦予作品以特有的聲調和魅力。
文學在根子上是懷舊的。文學即對生命的眷戀,有了這份眷戀,人才會用五彩之筆來描繪生命和生命所走過的路徑,展現生命在每時每刻留下的印痕。哪怕是想象和幻想,也總是記錄著往昔的情感歷程,在創造嶄新形象,似乎正向著未來世界翱翔之際,它不能不重返過去的經驗和記憶,回到最溫馨的精神家園,從中汲取營養和力量。文學鐫刻著時間的印記,在文學的當下時間中,既包蘊著未來,又向過去回溯,它植根于過去。因此,在希臘人心目中,記憶女神摩涅莫緒涅被稱為掌管敘事藝術的繆斯。然而,當“懷舊”作為一種文體特征,它就不再僅僅是對文學與時間的關聯所作的一般性表達,而是強調人對已經逝去的時間的體驗是那么刻骨銘心,以至于它牢牢掌控著作家的文思,滲透于作家的靈魂,并在作品整體烙印下抹拭不去的鮮明的情感印記。人正是以文學懷舊作為一條重要途徑,來反抗時間的不息流逝。
一
在小說《呼蘭河傳》的結尾,蕭紅這樣寫道:
呼蘭河這小城里邊,以前住著我的祖父,現在埋著我的祖父。
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了,我長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了。我還沒有長到二十歲,祖父就七八十歲了。祖父一過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從前那后花園的主人,而今不見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園里的蝴蝶,螞蚱,蜻蜒,也許還是年年仍舊,也許現在完全荒涼了。
小黃瓜,大倭瓜,也許還是年年地種著,也許現在根本沒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還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間的太陽是不是還照著大向日葵,那黃昏時候的紅霞是不是還會一會工夫會變出一匹馬來,一會工夫會變出一匹狗來,那么變著。
這一些不能想象了。
聽說有二伯死了。
老廚子就是活著年紀也不小了。
東鄰西舍也都不知怎樣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則完全不曉得了。
以上我所寫的并沒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們充滿我幼年的記憶,忘卻不了,難以忘卻,就記在這里了。
蕭紅貌似平靜地歷數兒時的記憶:祖父、東鄰西合、后花園里的小黃瓜、大倭瓜,乃至蝴蝶、螞蚱、蜻蜒、早晨的露珠、午間的太陽、黃昏的紅霞……瑣瑣碎碎,平平淡淡,絮叨不止。然而,惟其瑣碎,才深深體現著蕭紅的眷戀之情,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生命,都珍藏在兒時的記憶中,歷盡歲月淘洗,始終拂拭不去;也惟其平淡,才將矯飾清除凈盡,剖露出熾熱情懷。任隨時間流逝,光陰荏苒,兒時的一切卻仍歷歷如在目前,一切都令作者魂牽夢縈。
是的,這就是懷舊,是刻骨銘心的懷舊之情。年青時的蕭紅決絕地離開了東北的家鄉,為逃避不幸命運背離了家鄉,時隔十年,當她因戰亂孤寂地流落于武漢、香港,那繁華而又陌生的大都市,童年的家鄉和家鄉的童年卻成為她最為溫馨的精神家園。那里的每一瑣屑事物都曾哺育了蕭紅幼小的心靈,也烙印著她的情感蹤跡,家鄉和它的一草一木都已成為她的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盡管小說不時嘲諷那些僻遠小鎮的陋習,甚至沉痛批判戕害生命的愚昧,但是,對家鄉的愛戀卻并沒有因此而沖淡。懷舊之情就像汩汩不息的呼蘭河流貫于小說敘述中。
對于任何個人,故鄉和童年都是生命的開端,也是記憶的開端。正是從這里起始,個人展開了他的生活,展開了他與世界的聯系,展開了他的希冀和憧憬。在童年單純幼稚的眼光中,故鄉被過濾為美和愛的世界,它如同母親的懷抱,是孕育新生命最為安定、溫熱的地方。然而,對于蕭紅,母愛在她記憶中是缺席的,于是,也就唯一留下了回憶中的故鄉,那故鄉小小的后花園。當她遠離了家鄉,漂泊無定,找不到下錨停泊的港灣的時候;當她歷盡了人生波折和愛情磨難,熱望愛卻得不到愛的時候;當她孤獨寂寞地只身滯留于陌生的現代大都市,而且這個大都市又正當風雨飄搖的時候,她怎能不懷戀家鄉,怎能不懷舊呢?那逝去的童年,同樣也是寂寞的,然而,卻受到慈愛的祖父庇護,小小后花園里的花花草草,蝴蝶,螞蚱,蜻蜒,都與她整日相伴,這里的一切是那么單調而單純,有的只是溫馨、和睦和和諧。即便花園外的世界上演著小團圓媳婦的悲劇,其間卻沒有陰謀、奸詐而只有愚昧,那令小小心靈難以索解的“善意又殘忍的愚昧”。
在《呼蘭河傳》中,交織著兩種視角:其一是童年的蕭紅。當作家的心靈為回憶所占據,沉浸于懷舊之情,她似乎忘卻了現實的自我,重返童年,以那充滿童真和熱愛的眼光窺視業已失去的往日世界,她就生活在過去的時間里。另一是成年的蕭紅,那經歷了人世間的簸弄,敏感、銳利而又充滿同情心的蕭紅,她不時地與往事拉開距離,敘述著,描繪著,悲憫著,嘲諷著,抨擊著……她立足于寫作的當下,用現時的睿智目光審視往昔。兩種視角相互交織,相互疊加,融合一體。蕭紅是矛盾的。對于故鄉,她既愛又恨,而恨恰恰是因為愛。正是這愛、恨所構成的張力,賦予小說以特殊的聲音和魅力;也正是這愛始終是一股深沉的潛流,是從心靈深處,從植根于童年的記憶,從遙遠的過去,平靜、沉穩卻又不可遏止地向我們涌來,才使得小說具有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它緊緊攫住我們,把我們一同卷入懷舊的深淵。
懷舊文學常常同時交織著兩種時間:過去與現在。因為愛和同情,作者帶領我們重返過去,流連于往日的世界,沉醉其間。懷舊并不僅僅是對舊跡的觀賞、憑吊,那種始終把“過去”作為“他者”,作為記憶中偶然的邂逅,不是真正意義的“懷舊”。懷舊必須是能“生活在過去”,因為“過去”孕育了他的生命,與他的生命息息相連,他從內心深處認同“過去”,“過去”對于他有著非同一般的價值,以至有著某種神圣性,是“現在”所無法替代的。當他重返過去,他似乎就回到了生命的源頭,回到了溫馨的“家”。他以過去的自己去體驗過去的生活,切切實實返回到過去的時間,流連忘情于過去的時間。
然而,作為懷舊的主體,他又無法完全脫離現在,他只能真實地生活于現在。過去對于他畢竟已經流逝而去,漸行漸遠。只有面對遠去而不再復歸的生活,只有生活于現在而與過去拉開了距離,并體驗這因時間流逝所遺棄下的距離,人才會產生人生幾何的無限感慨。但是,這兩種原本相互遠隔的時間卻又在懷舊中奇妙地突然相遇,并交織、疊加、融合在一起,在作者的創作和讀
者的閱讀過程中,轉化為當下的感受:
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鳥上天了似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無限的本領,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樣,就怎么樣。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黃瓜愿意開一個謊花,就開一個謊花,愿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玉米愿意長多高就長多高,它若愿意長上天去,也沒有人管。蝴蝶隨意的飛,一會從墻頭上飛來一對黃蝴蝶,一會又從墻頭上飛走了一個白蝴蝶。它們是從誰家來的,又飛到誰家去々太陽也不知道這個。
蕭紅似乎已經重新回到童年,回到了她心愛的小花園,以她的童心體察自然,以稚嫩而爛漫的幻想解釋自然,這花園也就幻化為滿是精靈的童話世界。可是,一句不經意間道出的判詞:“都是自由的”,卻泄露了這位備受命運簸弄顛躓,深感身不由己的成年蕭紅的心境。而當蕭紅嘲諷地回顧愚昧的舊習之際,那種時間的疏離感更躍然紙上了。小說雖然是寫過去,而作者的立足點卻在過去和現在之間游移,由此交織出斑斕的敘事色彩和復雜的情感色調。
二
區別于蕭紅《呼蘭河傳》中的懷舊以消逝的故鄉和童年為指歸,都德的《磨坊書簡》則眷戀著失落的文明。盡管這兩者在時間向度上都同樣指向過去,并總是難分難解地交織一起,但畢竟它們的主要旨趣是不同的。都德厭惡現代都市的喧囂和污濁,厭惡那一切由現代大工業所帶來的文明,為了尋求心靈的安寧,他終于在法國南方的普羅旺斯山區找到了庇護地:
一座靠風力磨粉的磨坊,坐落在羅納河谷中,位于普羅旺斯省的中心區,在叢生著杉樹和終年常綠的山崗上;上述磨坊業已荒廢二十多年,不能磨粉了,因此布滿了野葡萄藤、苔蘚、迷迭香以及一直爬上風車葉子的一些綠色的寄生植物……
這座頹圮的磨坊就像一座紀念碑,銘記下早已失落的文明,它與繁華的現代城市恰好形成鮮明對照。在現代都市,都德只是個流浪者,一個過客,他始終沒有屬于自己的精神寓所,像被折斷了根須,從它原來生長的土壤中拔離了,而只有這座廢棄荒蕪的磨坊,才令他似乎尋到了“家”的感覺。“現在,你要我怎樣來對你那喧鬧而昏暗的巴黎,表示我對它的厭惡呢?我住在我的磨坊里是何等舒適啊!這是我找到的如此舒適的一個角落,一個小小的馨香而溫暖的角落,它遠離一切人生信息、車馬喧闐和烏煙瘴氣!在我周圍有著很多美妙的東西!我定居這里才八天,在我腦子里就塞滿了種種印象和回憶……”
只有這里,都德才一見如故,一切都似曾相識,似乎它原先就曾存在于詩人的心胸,和他的印象和回憶相交織。一旦重逢,頓時就激活了詩人的想象,鉤起他無限情思,也令他失落的心靈得到安頓。
人是文化和文明的創造者,反過來,文化和文明則成為哺育和塑造人的環境。人生活于特定的文化和文明之中,就像他須臾不能離開空氣和水。然而,就像別爾嘉耶夫所說:“文明包含著毒素,包含著謊言,它使人變為奴隸,阻礙他進抵生命的整體性和圓融性。”因此,文明的進程同時也就暗寓了野蠻。“文明化了的野蠻正在蔓延,在它背后感受不到一點‘自然的氣息,觸目皆是機器、機械。工業技術文明顯現為不斷增長著的文明化野蠻和人的質的墮落”。在現代社會,當人不斷地創造物質文明的同時,人自己也被社會分工和機器生產所肢解,人成為“斷片”,成為“單向度的人”;當人努力矗立起一座座高樓大廈,讓成千上萬的人聚居于現代都市的同時,人與人之間又相互成為“陌生人”,人的心靈被隔絕、幽閉了,每一個人都成為“異鄉人”,他已無處尋覓自己的家園。“異鄉人并不只是站錯了位,從絕對意義上說,是無家可歸”。文化和文明為人創造了“安樂窩”,而同時又將人與孕育他的母胎——自然,不可挽回地分隔開了。現代文明毫不留情地廢棄原有的文明,義無反顧地斬斷與傳統的直接關聯,給人帶來了“異化”和“人的質的墮落”,使得人與自然相割裂,與傳統相割裂,與他人相割裂,也將自身割裂了。在現代生活表面的繁華下,人孤零零地無所依傍。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園”。這就不能不令人懷戀前現代的自然狀態、整體狀態和圓融狀態,不能不懷戀曾經給他的心靈烙下深深印記的失去了的傳統。
“時間中有惡本原,即致命的和消滅的本原,因為過去的死亡其實由無數的下一個瞬間帶來;這些瞬間陷入非存在的黑暗,這種非存在也是在時間中完成的,它是死亡的本原。未來是過去所有瞬息的殺手。”如果說,在現實存在中,過去的文明被時間這一“殺手”無情地扼死了生命,只殘留下一堆無生機的尸骸,文學卻常常希冀以想象重新復活它。在《磨坊書簡》中,都德借吹六孔笛的老藝人弗朗塞·瑪瑪伊的口,重新為我們講述著風磨時代羅納河的山谷:
村子周圍的坡地上全是風車。從左到右,但見風車葉子在松樹上端迎風旋轉,,一隊隊馱著面粉袋的小驢,沿著道路上上下下;從禮拜一到禮拜六,每天都能聽到高地上鞭子的響聲,風車上帆布葉子的撕裂聲,以及幫工們催趕牲口的吆喝聲,真叫人開心。禮拜日,我們成群結隊來到那些磨坊。在那里,磨坊老板們用上等葡萄酒款待我們。一些老板娘子打扮得像皇后那么漂亮,包著有花邊的頭巾,掛上她們的金十字架。我么,帶著我的六孔笛,大伙兒跳法蘭多拉舞,一直跳到深夜。
這里的一切都充滿著溫情和溫馨,圍繞著風力磨坊所建構起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親密關系,溫潤著每一個人的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生活總是這么不間斷地延續著,重復著,以致人們似乎再也不能離開這熟悉、平淡的生活。然而,現代文明卻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毀棄了這一切,切斷與這熟悉生活的關聯。都德想留住這逝去的文明,想重返這一文明,而一切都已不再可能。在機器磨粉廠的野蠻沖擊下,風力磨坊一座座關閉了,風磨時代已經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哪怕磨坊老主人戈里葉苦苦撐持著,以石灰代替麥子,讓風磨繼續空轉,勉力維持自己的尊嚴,只身抗拒機器磨粉廠;哪怕村里的鄉親被戈里葉深深打動,紛紛為磨坊送來麥子,不讓風磨停止轉動,甚至要為此“慶祝勝利”,也照樣不能拖住文明的腳步。文明的斷裂,在片刻間把都德和他的同代人一并擲入險象叢生的陌生境地,在都德心中籠罩上拂拭不去的陰影。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磨坊書簡》不僅是失落的文明的挽歌,更是都德自己心靈的挽歌,他想借懷舊之思,來撫平心靈的創傷,驅除文明斷裂留下的陰影。
在談到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進程時,伯曼說:“正是開發的過程,甚至在它把荒原變成一個繁榮的物質空間和社會空間時,都在開發者自身的內部重新創造出了那片荒原。這就是開發的悲劇起作用的原因。”現代化為社會帶來巨大的物質繁榮,以滌蕩一切的氣勢驅逐愚昧和落后,可是,同時卻為人造成了精神荒原,這不僅僅因
為不間斷的迅速變化割斷了傳統,割斷了文化之根,割斷了人自身的連續性,把人投入一個陌生世界,還在于現代文明的本性所決定的。
吉登斯和西美爾都把金錢視為現代化的推動力。在吉登斯看來,金錢具有“脫域”功能,它像“多才多藝的妓女”,可以把原先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換從時空限制中解脫出來,成為不受時空限制的間接交換。于是,金錢這一抽象的“純粹商品”也就逐漸改變了人與人的關系,解除了人之間的直接交往,轉變為通過金錢間接地打交道。金錢在有效擴大人的活動范圍和效率的同時,也將人與人的關系抽象化了,并最終抽象為單純的金錢關系,抽象為枯燥的數量關系。西美爾則著重從文化心理角度闡述了金錢的作用。他認為,由于金錢幾乎可以購買一切,人們也就很輕易地相信,能夠在貨幣價值的形式上找到經濟活動的對象確切的、完整的“等價物”,而忽略了這些對象還有不能用金錢來體現的方面。他說:“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令人疑慮的特征、不安與不滿的深刻根源。由于貨幣經濟的原因,這些對象的品質不再受到心理上的重視,貨幣經濟始終要求人們依據貨幣價值對這些對象進行估價,最終讓貨幣價值作為唯一有效的價值出現,人們越來越迅速地同事物中那些經濟上無法表達的特別意義擦肩而過。對此的報應似乎就是產生了那些沉悶的、十分現代的感受:生活的核心和意義總是一再從我們手邊滑落;我們越來越少獲得確定無疑的滿足,所有的操勞最終毫無價值可言。”金錢把人從對土地的依附中解放出來,把人從對物的直接依賴中拯救出來,把人與人的直接關聯拆解開來,賦予人以巨大的自由,而同時,金錢又把這一切關系都抽象了,把一切經濟價值之外的意義都擠干了。人與土地、事物,以及人與人之間因休戚相關而建立起來的豐富的情感紐帶,隨著這一抽象過程而被掐斷,人最終只能生活于冷冰冰的關系和意義的荒漠之中——這就是誰都難以逃脫的現代感,也是現代社會常常萌生懷舊情緒的根源。
都德顯然對這種現代感有著切膚之痛。他直覺而敏銳地感受到現代社會的情感流失,并總是竭力想逃離大都市,到山谷荒郊間被廢棄了的磨坊,到海濱孤零零的燈塔去尋找內心的寧謐,在與那些幾乎被拒斥于現代文明門外的鄉下車夫、面包師傅、莊丁、守燈塔人的閑聊中,在聽老藝人弗朗塞·瑪瑪伊講述的故事中,在品嘗老瑪美特夫婦釀制的櫻桃酒中,體驗人世間的真情,重新拾回失落的文明的碎片。
三
對于V.S.奈保爾來說,懷舊又是別一番滋味。奈保爾的祖籍是印度,他出生在西印度群島特立尼達印地語社區,青年時期到英國求學,此后定居英國。他是懷抱對未來的憧憬和勃勃雄心,對現代文明的傾心相與,來到英國的。然而,英倫生涯卻打破了他的內心寧謐,造成思想沖突和文化歸屬的困境。他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流亡者,他沒有故鄉。在英國,他是異族,是“另類”,四周包圍著冷漠的眼光;而所謂故國家園卻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是由前輩講述的故事傳說、破舊的印度器物,以及傳統儀式零零星星累積起來的,構不成清晰的輪廓。
小時候,對我來說,哺育過我周遭許多人、制造出我家中許多器物的印度,是面貌十分模糊的一個國家。那時,在我幼小的心靈里,我把我們家族遷徙的那段日子看成一個黑暗時期——從大海伸展到陸地的那種黑暗,就像傍晚時分,黑暗包圍一間小茅屋,但屋子四周還有一點光亮。這一圈光芒、這一個時空,就是我的經驗領域。
盡管這經驗領域是那么狹小和模糊,它仍然是奈保爾建構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出發點,這經驗與他在英國的文化環境和文化經驗是格格不入的。由此造成經驗斷裂,使他不得不面對身份歸屬的難題。拉雷恩說:“文化身份的形成以對‘他者的看法為前提,對文化自我的界定總包含著對‘他者的價值、特性、生活方式的區分。”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文化作為文化的“他者”,反而強化了奈保爾對自己的印度族裔身份的意識,這也是他日后一直憧憬印度,一再重返印度去尋覓文化之根的緣由。
然而,印度畢竟不是他生于斯長于斯之所在,那一小圈恍惚迷離的光芒尚不足以寄托他的懷舊之情。在他踏上故國印度前,唯有印度之外的特立尼達才是他記憶里切切實實存在的地方,也因此成為他魂牽夢縈的地方。奈保爾的懷舊起因于身份歸屬的困境和對文化之根的追尋,可是,當時他只能向特立尼達的米格爾街,向米格爾街上鎮日廝混一起的鄉親們去尋求心靈的庇護所。
在《米格爾街》中,奈保爾向我們一一介紹了那些平凡又個性鮮明的街坊鄰居:魁梧兇狠,板著冷酷無情的面孔,敢于斥責美國兵卻害怕一條狗的懦夫“大腳”;總是在想新主意逗大家開心,熱衷于焰火實驗,直至引起家里一場大火才使焰火爆發出壯麗輝煌的焰火師墨爾根;被人視為瘋子,無論競選市政議員或國會議員,次次都要參加,總只能得到三票,最后竟把自己釘十字架嘩眾取寵的曼門;整天忙忙碌碌地敲打著、畫著、鋸著,做一件“叫不出名堂的東西”的木匠波普;總愛把發動機、汽化器搗鼓出來,拆成碎片,或鉆到汽車底下瞎折騰,弄一身油污的“機械天才”比哈庫;養了八個孩子卻有七個父親,可是,當得知女兒未婚懷孕,竟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哭泣的勞拉,等等。一個個各具特征,甚至怪癖的人,對奈保爾來說,都是那么可親可近。“要是陌生人開車經過米格爾街時,只能說一句‘貧民窟!因為他也只能看到這些。可是,我們這些住在這里的人卻把這條街看成是一個世界,這里所有的人都各有其獨到之處。”奈保爾深情地回憶著。這里沒有一個是可惡的,有的只是可笑或可悲,而可笑可悲的背后則是可愛可親。那些瘋子、傻子、暴徒、小丑和冒險家……都和他的童年聯系在一起,融入他的生活,他的想象,他的血液,以至于成了他童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奈保爾生活于陌生的國度,生活于陌生的人群,因文化隔膜而倍感孤獨的時候,這些童年的街坊近鄰就更顯親切了。只有回到兒時的生活、兒時的友誼之中,他因身份困境而生的焦慮才能得以紓緩。懷舊之情消解了時間造成的距離,哪怕是作者嘲諷地回憶往事,我們都似乎跟隨奈保爾一同回到特立尼達,與米格爾街的鄰居朝夕相處,觸摸得到他們的體溫,聞得到他們的鼻息。
布萊克·沃茲沃斯是特立尼達一位窮詩人,他的詩甚至花四分錢也賣不出而只能靠唱克利普索小調維生,卻幻想著自己在寫一首最偉大的詩篇,有朝一日將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敏感、善良,就是看到一朵牽牛花也都想哭,做每一件事都像參加圣典一樣鄭重其事。他常帶著“我”做長途散步,去植物園,或登上小山觀看黑夜籠罩、漁火點點的西班牙港。當“我”遭受母親的鞭打,從家里逃出來,是他撫慰“我”,伴“我”一起躺在草坪上,為“我”講故事,告訴“我”天邊星星的名字。即便是養了八個孩子,不得不靠找男人艱難度日的勞拉,也照樣挺喜歡“我”,每逢搞到些李子、芒果或甜點,總想到要分給“我”……文化傳統并非僅僅留存于典籍和種種歷史遺存,
它最為深入充分地刻錄在民族性格上,表現于人的行為方式和日常交往中。盡管米格爾街遠離印度本土,盡管在歲月侵蝕下這些移民的風俗習慣已經潛移默化,也盡管當年奈保爾已意識到“必須離開這里”,但米格爾街仍然令離它而去的海外游子心向往之,并從中尋得最溫馨的記憶。吉爾·利波維茨基說:“所有記憶,所有意義世界,所有參照過去的集體想象都可以用于和服務于身份建構和個體的個性完善。”當奈保爾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熏陶,當他日益明了米格爾街的陋習并不時給予諷刺,可是事實卻依然是:唯有米格爾街上那段生活,文化身份才不會成為一個困擾人的問題。在米格爾街,他就生活于自己的文化中,自己的族群中,生活在貼己的精神氛圍中,一種熟悉、溫馨、怠惰、沒有任何心靈沖突的氛圍之中。
在奈保爾筆下,污穢的米格爾街只是一群個性鮮明的人的活動背景,本身輪廓模糊,始終沒有進入作者描摹的視野。王安憶《長恨歌》則不同,它所懷戀的真正主角不是某些個人而是整個城市——老上海。老上海在王安憶眼里是那么活靈活現,較之于任何一位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王安憶都更深刻地了解上海。她不僅寫出了有形跡的物質的老上海,而且連無形無跡的上海都已被淋漓盡致地加以描摹,躍然紙上,抓住了上海的靈魂,上海的氣息。
上海的弄堂是感性的,有一股肌膚之親似的。它有著觸手的涼和暖;是可感知,有一些私心的。積著油垢的廚房后窗,是專供老媽子一里一外扯閑篇的;窗邊的后門,是供大小姐提著書包上學堂讀書,和男先生幽會的;前邊大門雖是不常開,開了就是有大事情,是專為貴客走動,貼婚喪嫁娶的告示的。它總有一點按捺不住的興奮,躍躍然的,有點絮叨的。曬臺和陽臺,還有窗畔,都留著些竊竊私語,夜間的敲門聲也是此起彼落。還是要站一個制高點,再找一個好角度:弄堂里橫七豎八晾衣竹竿上的衣物,帶點私情的味道;花盆里栽的鳳仙花、寶石花花青蔥青蒜,也是私情的性質;屋頂上空著的鴿籠,是一顆空著的心;碎了和亂了的瓦片,也是心和身子的象征。
只有一個從小生活在上海,并且連她的血肉和靈魂都由這個都市孕育出來的人,才能對上海有如此細致入微的感覺。正如人總是眷戀著母親的懷抱,向往母胎中的安寧一樣,王安憶與老上海間的密切關聯,使得她在描述之際,字里行間不可抑止地流淌著深沉的懷舊之情。哪怕她故作滄桑,不時插入略帶嘲諷的議論,也照舊不能掩蓋這種刻骨銘心的情感。從中,我們似乎聽到當年蕭紅對呼蘭河的那種深情和音調。
女主角王琦瑤是老上海的魂和象征。“上海的弄堂里,每一個門洞里,都有王琦瑤在讀書,在繡花,在同小姐妹們竊竊私語,在和父母慪氣掉淚。上海的弄堂總有著一股小女兒情態,這情態的名字就叫王琦瑤。這情態是有一些優美的,它不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親可愛的。它比較謙虛,比較溫暖,雖有些造作,也是努力討好的用心,可以接受的。它是不夠大方和高尚,但本也不打算譜寫史詩,小情小調更可人心意,是過日子的情態。它是可以你來我往,但也不可隨便輕薄的。它有點缺少見識,卻是通情達理的。它有點小心眼兒,小心眼兒要比大道理有趣的。它還有點耍手腕,也是有趣的,是人間常態上稍加點裝飾。它難免有些村俗,卻已經過文明的淘洗……”作者借王琦瑤將老上海的情態風韻力透紙背地描摹了出來,盡情地表達了懷舊自戀之情。這里正是作者王安憶習慣的生活,她的文化和她的傳統,她的精神的家園。這里有她需要的一切,但恰恰沒有米格爾街溫厚淳樸的人與人的關系。沒有人是真正可靠的,值得信賴、以身相許的。在這不折不扣的勢利場,哪怕被視為人間仙境的“愛麗絲公寓”照樣沒有安全感。唯一似乎忠于愛情的程先生,也一直是在追求一個幻影,與真實的王琦瑤隔著一層,最終不能走近一步并以死葬送了這種感情。即便這樣,上海仍然是王琦瑤和王安憶們所不能忘懷、不能離棄的。即如王琦瑤就是老上海,王安憶也就是上海,她愛老上海就是愛自己,愛自己逝去的蹤跡,愛自己那永遠不能復歸的歲月。無論完美與否,那終究是一段刻骨銘心卻已無法復現的年輕迷人的歲月。
四
懷舊既起因于內心缺憾,又與精神自戀相關。人總是與生活中的種種經歷建立起拉扯不斷的情感紐帶,隨時間流逝,這一切都被無情地推落于過去之中,再也不能復現了。它們沉淀在記憶里,日漸朦朧,蛻變為如煙的影跡或空洞的軀殼。然而,也正因成為影跡和軀殼而不再真實在場,卻顯得彌足珍貴。它們被時間所過濾,變得純凈輕靈,哪怕是苦難,也因時間間距而濾去了切膚之痛,并隨情感發酵,轉而變為甘甜,甚至神圣的了。吉登斯說:“焦慮的種子,植根于與原初的看護者(常常是母親)分離的恐懼之中。”當我們意欲切斷時間,同過去的一切,諸如童年、情人、故交、故鄉、故國、自然、文明告別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正經歷著與“原初的看護者”分離的恐懼。我們從母親的子宮里被排出,從此失卻了母親安定寧謐的懷抱,茫然漂泊于不確定的世界。由此而生的焦慮,恰恰是我們意圖借懷舊重新找回“原初的看護者”的動力。如果更深入一層來看,過去的一切之所以有神圣價值,就在于它曾為人的情感所滲透,本身已成為人的生命的印跡,對它的懷戀,其實就是對過去生命的懷戀,對自己生命所失去部分的懷戀,也即自戀。在《時間,這偉大的雕刻家》一文中,尤瑟納爾談到古希臘藝術時說,那些雕塑雖歷經歲月侵蝕,變得殘破不堪,卻越發顯得美。自然和時間的作用造成了“非自愿的美”,以致從破碎的的雕塑中誕生出一種新的作品,一種因破損而更顯其完美的作品。那些模糊不清、難以辨認的半身像,那些被海水剝蝕了的軀干,那些缺肢少腿的碎塊……只能是出自人的手,出自希臘人的手,“他們曾在某個地方,在某個世紀曾經干過活兒。他們整個身心都表現在其中了,他們與世界巧妙地合作,他們與世界抗爭,并且還同作為其支柱的精神和物質幾乎同時消亡的那個最終的失敗抗爭過。他們的意愿直到最后,在事物的廢墟中都被證實著。”凡是人的生命經歷過的,凡是人的生命留下印痕的,它都將成為人的生命的印證,都將為人自身所珍惜,所戀念。這種與生命的突然邂逅,不再僅僅是過去的消逝了的生命,而是對過去生命的重新發現,對自我的重新發現。其中,浸透著似曾相識又出乎意外的驚喜和時光不再的惋惜慨嘆。
從另一角度來看,現代社會的懷舊又立足于現代人對“現在”的集體不信任。針對19世紀的巴黎,阿加辛斯基說:“現代仿佛通過提高節奏、速度和增加故事來表明現今已經不再可能,并把我們投入一個舊貨世界。”現代化所帶來的高速度、高節奏和密集的信息,使得“現在”變得愈加不穩定,愈加難以捉摸、不可信賴了。競爭把眼前的一切迅速推向過去,化為陳跡。誰也無法把握“現在”,真正占有“現在”。也正是“現在”,潛伏著重重危機,它喻示著競爭、變化、動蕩、危險和隱沒消失,唯有“過去”才是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