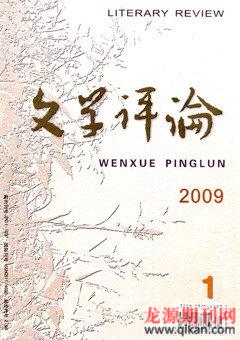“原鄉小說”的裂變與重續
張直心
內容提要重讀《南行記續篇》之意義,不僅在于探索原鄉小說在“十七年”政治語境中一息尚存、曲折變通的軌跡;更旨在揭示既有“十七年”文學研究中可能曾被忽略的意義暗角——作品中,令艾蕪神往的南疆,既是政治意識形態范疇的社會主義新邊疆,同時依然是那文化學定義下的“邊地”;而作者之所以襲用“憶苦思甜”情節結構模式,潛意識中正是為了贏得不合時宜的“懷舊”抒情的“合法性”。
王德威曾以“原鄉文學”一詞,命名“‘五四及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如廢名、沈從文、蕭紅、艾蕪等”一脈的原鄉作品。及至新中國成立,“五四”開啟的原鄉小說創作卻發生了質的裂變,特定的“社會主義時代”語境不斷逼促作家表現農村的現實政治,原鄉題材及敘述方式日益顯得不合時宜,終于為新農村小說取代:作家們或盛贊農村集體化引發的“山鄉巨變”;或書寫農村“新人”試辦互助組、合作社的“創業史”;或激賞農村歷經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風雨(大都是“人工造雨”)而贏得的一片“艷陽天”。
然而,“原鄉文學”傳統并未全然失落于現代文學與“十七年”文學表層的斷裂上;藕斷絲連,時或潛隱在兩者曲折晦暗的壓抑變通、辯難修正間。例如艾蕪寫于上一世紀60年代初的《南行記續篇》,便如一座獨木橋,勉為其難地連接起現代文學與“十七年”文學間的原鄉小說斷層。
一寫“自己所熟悉的”還是寫“革命事業需要的”
新中國的成立,使艾蕪又一次面臨題材選擇上的“遲疑和猶豫”。30年代他醞釀《南行記》時,曾與沙汀聯名給魯迅寫信,求教能否寫自己“熟悉的”、“在現時代大潮流沖擊圈外的下層人物”,坦言“不愿把虛構的人物使其一個翻身就革命起來”;魯迅的回答耳熟能詳:“總之,我的意思是:現在能寫什么,就寫什么,不必趨時,自然更不必硬造一個突變式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但也不可茍安于這一點,沒有改革,以致沉沒了自己——也就是消滅了對于時代的助力和貢獻。”盡管彼時魯迅的回答仍留有初習蘇式辯證法時的面面俱到,諸如在“熟悉”/“有時代意義”一類的取向上偏側移易;但艾蕪卻從某個“深刻的片面”,領會了“寫自己所熟悉的東西”、“不必趨時”這一創作原則。恰是有了這一主心骨,《南行記》應運而生。
時移事往,30年代業已破解的“寫什么”的困惑于今又成了問題。好在此時毛澤東文藝思想業已成為一切文學工作者必須聽命的指導性綱領。1951年9月,艾蕪寫了《略談學習、鍛煉和創作》一文,筆涉題材困惑的迎刃而解:“研究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才明確地認識了,創作作品不是以文學藝術工作者為本位,只寫自己所熟悉的東西,而是反轉過來,要以革命事業為主”,“因此文學藝術工作者,首先要研究的,不是我寫什么熟悉的東西,而是要明白革命事業需要我寫什么東西。這就變成,不是我愿不愿意寫什么的問題,而是我應不應該寫什么的問題。假如革命事業要求我寫的東西,而我又明白這是我應該寫的,只是我卻獨獨不熟悉它,那我該怎么辦呢?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你不熟悉的東西,你就得先去熟悉它”。
恰是在“革命事業需要”這一主流意識形態的導引下,艾蕪不再“南行”原鄉,而選擇了北上鞍鋼“熟悉”新生活。1958年相繼出版的長篇小說《百煉成鋼》與短篇集《夜歸》、《新的家》,便是他題材趨時求新的收獲。《夜歸》、《新的家》、《雨》等被復沓選人上述短篇集中的諸作,多以富有生活氣息、富有表現力的細節,煞費苦心地捕捉新生活的脈動;但徒剩支離破碎的“細節的真實”,卻失落了那流貫全書、生氣淋漓的創作主體。恰如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所指出的:“從整體而論,連同長篇《百煉成鋼》,都表明了在題材、藝術觀念和方法‘轉向后的挫折。對于艾蕪,讀者記憶最深的恐怕不是《山野》和《故鄉》,而是30年代的《南行記》。”
《夜歸》寫一名年輕工人雪夜歸家之行;《新的家》寫一位農村婦女到了“新的家”的安定……無意識間,適成作者在新時代中苦心尋覓并似乎終于找到了歸宿的移情。然而即便艾蕪身處“新的家”,心卻依然魂牽夢縈“原鄉”。
對于艾蕪而言,“南行”不止是一種題材選擇,而是一名自外于“現時代大潮流沖擊圈”、神往漂泊的知識者的思想外化。云南邊地亦不止具有地理學的意義,而暗含著一個疏離現實生活的精神彼岸、精神異鄉(異鄉邊地被樂于邊緣的艾蕪引為夢中“原鄉”)。這是30年代艾蕪書寫《南行記》的原動力;亦是后來他續寫《南行記續篇》的真實心境。惟其如此,方能理解當1961年艾蕪得以故地重游時,那份如魚歸水的逍遙,那種生命力勃發的銷魂。
洪子誠的文學史評說卻對《南行記》與《續篇》有著明顯揚此抑彼的傾向,稱《南行記續篇》“依然是抒情性的文筆,也還有邊疆風情的渲染,而敘述者的‘身份已完全改變,作品的‘主旨,也被納入‘新舊生活對比的簡單的觀念框架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對社會生活、對生命的發現”。
誠如洪子誠《當代文學的“一體化”》一文所言,不應該模糊當代文學“‘一體化的總體面貌”,這恐怕是他上述立論的出發點;但同樣是其必要的提醒:我們亦不能疏忽“對‘非主流文學線索的細心發現”,不能疏忽“同一文本內部的文化構成的多層性”。恰是得益于后者的提示,筆者認為《南行記續篇》中的原鄉主旨雖則會在“十七年”政治語境中被重構,但仍無改作者在“南行”這一象征中力圖重獲主體自由,在原鄉這一題材中相對游離現實的隱衷。類似不同向度的牽引撕扯,促成了文本內部的裂變,產生了《續篇》相反相成的結構性張力。
其實,即便在“十七年”一體化的輿論體制下,仍若隱若顯地存在著諸種辯議修正的聲音:諸如1957年巴人《論人情》、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的發表;1961年《文藝報》主編張光年執筆的《題材問題》的專論;及至1962年老朋友邵荃麟關于“題材的廣闊性”、“題材的多樣化”的講話。《南行記續篇》可謂以極其獨特的方式,有意無意地呼應、觸及了關于文學的階級性、文學的人情與人性、關于題材與主題等省思。
以下擬重讀《續篇》,努力捕捉其文本的裂隙,藉此穿透作品復雜多元的情節結構、敘事策略、表情方式、生命觀念。重讀之意義不僅在于勾勒蕭紅故去、廢名、沈從文擱筆后,原鄉小說在新時代語境中一息尚存、曲折迂回的軌跡;更旨在揭示既有“十七年”文學研究中可能曾被忽略的意義暗角。
二憶苦思甜情節結構模式與懷舊情調
比照成書于30年代的《南行記》,《續篇》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便是襲用了“憶苦思甜”情節結構模式。恰如作者在《序言》中表明的,旨在通過“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對比”,展現新中國“把地獄換成人間的偉大變化”。小說中,一寫到新社會,總是“陽光晴朗朗”,“顯得無邊的光明”。即
便《姐哈寨》、《攀枝花》等篇中偶生氣惱,偶有波折,亦純屬“誤會”,有驚無險。
引人注目的是,集子中除《邊疆女教師》、《春節》等兩三篇作品屬“新人新事”題材外,其余九篇均為懷舊之作。筆涉今天的生活,作者似唯余勉力紀實之能,卻拙于飛騰的想象力,文字簡約得幾近吝嗇,儼若即時性的通訊、報道。更耐人尋味的是,在那些懷舊之作中,“思甜”僅止是一個外殼,而“懷舊”才是小說中用心凸現的魂核。與其說是“舊瓶裝新酒”,不如說是“新瓶裝舊酒”。起首照例寫敘述者來到某村寨,先“簡單地說出我今昔不同的印象”;接著便“忽然記起一點影子了”,于是倒敘一個昨日的故事;直至結尾才重又回到“新世界里”。作者并未一味沉醉留連于邊疆新貌中,卻總是神魂出竅,尋覓故土舊夢。
面對“新人新事”,作者甚至有點喜“舊”厭“新”,如自序中言及:“有個高山上的漢族寨子,同外邊的美蔣特務和暗藏的特務就作過不少的斗爭。我們曾盡力調查過”,“有個邊防軍的工作組,在少數民族的山區,大力開展工作,由不懂話做到懂話,由開始受到冷遇,到最后不讓離開。整個經過,我們也作過詳細的調查研究”……結果,兩個素材都未被作者采用,理由是“都因不適合用第一人稱的形式來寫”。
《續篇》中的“第一人稱敘述”,不僅包含著敘述者采用“我”的口吻來講述故事,“我”同時也是故事里的一個人物。準確地說,作者分身為二,一個是“第一人稱敘述者”,他的身份是“機關人”(邵荃麟語);另一個是昨日的故事里的人物“我”,他的身份是漂泊知識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機關人”身上,仍隱約可見“知識者”的移情。倘若《續篇》中“敘述者的‘身份”純粹僅止是機關干部,那么,并無礙采用這兩個素材;問題恰在于,對于艾蕪而言,此處所謂的“第一人稱敘述”,并非只是敘事學意義上的視角,同時意味著一種便于凸顯自我、激揚主體的姿態;意味著一個對美的生命與人性異常敏感的漂泊知識者的眼光;意味著一種必須經由感覺記憶內化為“我有”的程序。而上述“新人新事”則尚停留于理性認知層次,難以納入作者記憶中的文化架構、感情世界里,使之凝融為有意義的整體。
《南行記續篇》通篇縈繞著纏綿不盡的追憶語調:“我為什么老要記起以往的事呢?”“比惚覺得像以前在哪里見過,但仔細看來又似乎有些陌生。可是她的聲音,總含有某種熟識的東西”,“我漸漸記起好多年前,我是走過這樣的地方。我記得那時……”無意中透露出,作者與其說是在“憶苦”,不如說是憶舊、懷舊。
“這本《南行記》,將會把今天的讀者,引到過去黑暗的社會里去。但我要說一句,過去的社會,遠比書里所描寫的,還要黑暗的多。”60年代初作者曾如是聲明,言外之音恰恰透露了《南行記》(《續篇》亦然)的描寫仍不盡“黑暗”。
黑暗的社會,究竟有何“舊”可“懷”?作者苦苦追懷昨日的風景,社會的黑暗未曾使其黯然自傷,卻因常感染著邊地自然的神奇而萌生q眙悅的詩意”;作者多方“打聽一些趕馬人、偷馬賊、私煙販子的下落”,歲月淘洗,他卻留下了那些被主流歷史拒斥的邊緣人“性情中的純金”;心的荒涼處,幸得有邊地那汩汩無盡的愛的溫泉的滋潤;“漂泊”這一不無象征意味的行為中,作者十倍百倍地領略了人性的自由、生命的銷魂。隔著36年歷史煙云往回看,原鄉在時移事往中不僅生出一份憂傷,更生出了一份美麗。至此,我們讀懂了,令艾蕪神往的南疆,與其說是政治意識形態范疇的社會主義新邊疆,不如說仍是那文化學定義下的“邊地”;而作者之所以襲用“憶苦思甜”情節結構模式,潛意識中正是為了贏得不合時宜的“懷舊”抒情的“合法性”。
三階級斗爭場域與人性“飛地”
較諸《創業史》對農村階級關系的細致刻畫,較諸《艷陽天》對農村階級斗爭的“生活化”表現,《南行記續篇》尤其顯得不善于運用社會分析方法。艾蕪似乎無意細寫邊地人民所受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更無力如浩然一類作家那樣,不無過敏地從日常生活細節中發現階級斗爭的蛛絲馬跡。盡管艾蕪將土司、頭人全寫成了臉譜化的“壞人”,盡管他將惡勢力的搶親行為一律納入階級壓迫的框架去闡釋,然而,與其說作品中階級斗爭敘事取代了人性敘事,不如說作者將階級斗爭敘事悉心轉換為表現“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與那些束縛人性、束縛愛情、壓抑自然生命的邪惡勢力之間展開的對抗。緣于此,《南行記續篇》的主題及視閾仍屬于原鄉小說范疇。邊地文化意識對美的生命與人性的看重成為作者衡量事物的標尺:“舊世界”的應推翻在于其“不知壓碎了多少美麗的生命”;而作者盡管襲用時語稱階級敵人為“十惡不赦”,但在八篇小說中唯一寫及且反復控訴的惡行卻唯有“搶親”。
如果說,《百煉成鋼》、《雨》等作雖筆涉青年工人的愛情,但那僅僅是革命生活的點綴,純屬公共話語在個人情感領域中的挪移,即便如此,也曾遭到“愛情描寫是否必要,以及如何評價作品的愛情描寫的情節”一類的質疑,“十七年”文學的革命意識潔癖已令愛情日益成為創作的盲區乃至禁區;那么,“南行”卻使艾蕪有幸遁入愛情的“飛地”。
一個為人忽視卻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十七年”文學中表現少數民族愛情生活的作品占了相當可觀的比例。個中是否隱含著漢族作家對更順應自然、接近自然的少數民族生命意識的傾慕,抑或還是因著表現邊地少數民族愛情生活時,可以少一些意識形態禁忌,多一點浪漫情調?《南行記續篇》的選題適可揭示上述玄機:十二篇小說中,竟有九篇以愛情為題材,并將愛情從小說的點綴因素升格為敘事審美的中心:或寫佛爺力爭還俗,不屈不撓,一心與心愛的女人結婚的悲歡離合(《芒景寨》);或寫獵人與其戀人被土司的兵團團包圍,水竭糧絕,寧死也要相守在一起的癡情蜜意(《群山中》);或寫有情人偏被拆散,相距咫尺(邊境線)卻如遙隔天涯般的相思夢斷(《瀾滄江邊》);或寫盜馬賊與情人因情出逃,千里走單騎,不無傳奇的生離死別(《野櫻桃》)……顯在層面自是表現對被舊社會阻抑的愛情的悲憫;潛文本中卻在不自覺間亦隱含了對新時代情愛禁忌的質疑與背離。
《群山中》自覺非自覺地襲用了傣族地區廣為流傳的獵人與公主故事母題,寫土司小姐木文娜在外出打獵時對英武的獵人寸金才一見鐘情,父親偏嫌貧愛富,硬逼她嫁給一臉麻子的另一土司的兒子,于是木文娜在出嫁路上毅然出逃,與獵人遠走高飛,卻不料被土司重兵包圍,以死殉情。其情節較之同源母本具有恒定的承傳性與共質性。這一故事母題中,儼若“天上下凡”的“公主”的角色功能至為關鍵,它不僅成為父母抑阻戀愛、情節橫生波瀾的動因,而且以此“天上人間”的身份距離,體現了“愛高于一切”的主題。
然而,獵人與“公主”身份懸殊的戀情,尚未及在小說中沖撞舊社會封建土司階級的門庭秩序;便已先在現實層面觸犯了新時代革命階級嚴
守階級界限的禁忌。“公主”這一人物設置遂使作者陷于兩難:若取消木文娜的土司小姐身份,則其戀情波瀾不驚、其主題亦毫無意義;反之,又有宣揚“階級調和”之嫌。最終作者采用了將女主角分身為二的敘事策略。在木文娜之外,節外生枝地為其添加一個貼身丫環伊娟。當木文娜帶著伊娟逃婚后,令情節陡生波折,寫土司小姐實難耐獵戶生活的貧窮卑陋頓生悔意,而此時“窮苦人家”出身的伊娟反得以與獵人繼續戀情。至此,邊地經典民間故事中的女主角,不得不由公主原型淪為新意識形態的婢女。
艾蕪敘事有術,有意利用伊娟與木文娜的如影隨形、親近無間,平生出諸多虛虛實實、真幻莫辨的魅象。彼時意識形態兩軍論戰的宏大話語:“一分為二”/“合而為一”,不經意間居然被移作了謀篇布局的“雕蟲小技”。或花開兩枝,印證親不親階級分的時論;或形影疊合,讓伊娟權充“公主”角色功能的替身,使其既具有苦大仇深的階級出身,又不失“天上下凡”的氣質。
盡管作者有意運用多重視角敘事,有意閃爍其詞,如先由獵人的哥哥出面指稱:“人家是土司家的小姐,跟你窮人家不一條心的”,接著又借另一人物之口辯解:“那不是土司的小姐,是土司家的丫頭”,使文本歧義叢生;但從小說中對伊娟的形象刻畫:“臉色白白的,眼光象水波一樣流動”,“絲毫沒有山村姑娘,見了生人就現出拘束害羞的樣子。同她說話,口齒流利,大大方方的,而且亮亮的眼神,極富有表情。她不象是寸大媽的女兒。寸大媽有著山村居民的本色,誠樸厚重,一副直心眼。她卻是心眼多得很,在大地方生活過似的。看見她,不能不想起今天走過的那一條活活潑潑的清溪”,以及問及伊娟時獵人母親的表白:“我們受不起,人家是天上下凡的”……卻無一不提示著伊娟與其身后被遮蔽的土司女兒的同構關系。潛文本中,實是不得不被“階級論”處以極刑的公主木文娜冤魂不散,借伊娟這一凈身脫胎換骨,得以與獵人重續鴛夢。
雖則艾蕪煞費苦心,縫合了邊地民間故事與階級斗爭敘事的話語裂縫;但小說的結局仍不可避免地構成了對封建門戶觀念與同樣森然的革命階級論的多重質詰。作者將男女主人公從現實生活的地面,還原于民間故事的神話型語境中,提升至神性的天空里。讓現實中倒下了的年輕情侶高高地站立起來,化身為“烏藍而又莊嚴”的山峰,“遠遠近近滿布森林的群山,都仿佛圍在它的周遭,低著頭,帶著敬仰的神氣”,“我”也“禁不住摘下了帽子”,向那高于一切、超越現實、超越階級、超越財富的“愛”致禮。
一如《群山中》的敘事真幻莫辨,《瑪米》的故事亦朦朦朧朧、恍惚迷離。小說寫客店伙計“我”與傣家女孩瑪米,雖語言不通,卻不乏真情交會,熱心的老板娘無事生非,編造出兩人相愛的流言,未料竟招致官家先下手搶占了瑪米……明明愛情純屬“無中生有”,不知怎的,通篇卻氤氳著一種“道是無情卻有情”的纏綿。結尾寫:我“低頭走著……這時正是一九二七年的冬天,但克欽山中還是夏季的景色,到處都是綠色的林子,吊滿藤蘿,開著各樣的野花。蜿蜒在山中的大盈江,時時在路邊的樹林中出現。這些流水就是從她們的甘崖壩子流來的,水波在陽光中,每一閃動,我都仿佛望見她的眼睛一樣。而且眼波中分明露出了悲哀和憂愁。我悵然地走著,一路林中盛開的野花,歌唱的鳥兒,都全沒有看見聽見。我只是悵然地走著。”——值得注意的是,至此,作者終于脫出卒章“思甜”套路,無心頌揚“換了人間”,而任由全篇(亦是全書)在“悵然”中作結。
臨了,作者還鄭重其事地在篇末標明:“1962年1月12日開始寫于允景洪,2月續于橄欖壩六鄉巴當寨子,2月3日寫完于小勐崳,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對照集子中其他諸篇篇末所留下的寫作日期,不難發現,各篇章的排列并非以執筆時間先后為序,而是按內容、情緒悉心編排。選擇唯一寫作于南行途中的《瑪米》作結,想必對于作者而言,這是最值得記取的生命性的個體時間。
這一編排令人尋味:悵然若失的是托身為瑪米的美而感傷、令人追懷的“南行”舊事?是若有若無、難尋難覓的“夢中的女孩”?是那人性美麗、人情溫暖的精神原鄉?是不得依歸、意猶未盡的去鄉之情?……作者空留下悵然省略號,任人省思。
如《序言》所挑明,時代潮流迫使作者不得不去“迎接新的東西”,身不由己,唯留魂游邊地。《南行記續篇》中的“漂泊”意象,適可借作“十七年”特定時期艾蕪續寫原鄉小說時交互偏側、迂回求索的創作姿態以及因此生成的游離不定的多重敘事魅影的隱喻。
責任編輯劉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