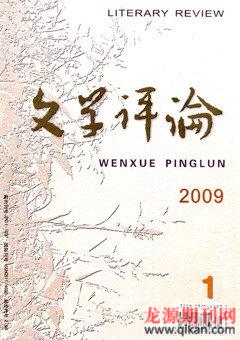論一種文學的“城市敘述史”
曾一果
內容提要20世紀80年代之后,隨著社會轉型與城市改革的興起,作家們便開始了“城市想象”。作家的“城市敘述”并不是一成不變,而隨著社會變革的變化而變動,早期的“城市敘述”偏重于宏大敘事,“改革”、“現代化”是“城市敘述”的中心話題;隨著社會繼續變革,世俗化的“城市敘述”興起;而隨著城市發展,作家越來越傾向于虛構一個“城市傳奇”。本文擬通過一些典型文本,描述這樣一種從“現代化認同”轉變為“世俗化認同”,進而走向“歷史傳奇”的“城市敘述史”。
一社會轉型與“城市敘事”的興起
1984年,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一項決定,即《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鄧小平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章中,也強調“改革要從農村轉到城市”。
《決定》的意義堪比1978年啟動農村改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因為從此改革由農村轉入城市,上海、大連等城市首先“開放”,城市蓬勃發展起來;到了20世紀90年代,城市改革進入第二階段后,中國城市人口比1978年上升30%左右,到1999年,全國城市數共667個左右,200萬以上人口的有13個,100萬到200萬的有24個,50萬到100萬的49個,20萬到50萬人的城市達216個。伴隨著城市發展,城市文化也相應地發達了,報紙、電影、電視和廣告開始迅速發展。繁華城市變成了一個雷蒙·威廉斯所說的大熔爐,“各種特殊文化引人人勝的視覺形象和風格并沒有消失,不止是民族語言、民族傳說、音樂和舞蹈的民族風格,而這一切現在都經過了大都市的這種嚴峻勘驗,它在重要的事實方面不止是大熔爐,而是一個本身緊張的、視覺上和語言上令人興奮的過程,從中出現了各種異常新穎的形式”。這個“大熔爐”為各種“異常新穎的形式”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即城市本身成為藝術創新的資源,20世紀90年代《上海文學》對這一現象作了如下評論:
親愛的讀者,近年來,中國的女性作家異常活躍,究其緣由,當與城市的現代化相關,都市的變動不居,紛繁復雜,為這些作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想象空間,而獨特的女性視角,則加深著我們對城市以及城市中人的命運的想象。
這篇評論將幾位女性作家的創作成就歸于城市的現代化,認為是城市的“變動不居,紛繁復雜”給她們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想象空間”,社會轉型為新時期作家的“城市想象”創造了條件和機遇,報紙新聞、電視廣告和城市風景,成為觸發作家創作的資源。王安憶寫《長恨歌》,池莉寫《來來往往》,作家的靈感多來源于報紙上的都市新聞;孫甘露有篇小說的題目是《像電影那樣戀愛》(2003),這篇小說告訴我們,在現代社會里,城市想象四處發生,電影上的戀愛方式成了普通人戀愛的樣板;朱文穎的小說《水姻緣》就講述了電視廣告是如何成為小說主人公的想象資源,《水姻緣》的女主角沈小紅結婚前曾對未來生活有過“美好想象”,這種美好想象來源于沈小紅電視媒介提供的場景:“沈小紅對自己的婚姻有過一些想象。她的這些想象多半是從電視廣告里得來的。很大的房子,雪白的窗簾被風吹起來。身穿白裙的漂亮主婦笑著忙里忙外。然后樓下傳來了汽車喇叭聲,是成功的西裝革履的丈夫,手里拿著一件禮物。”
社會轉型使得城市生活日益豐富,也要求創作主體把文學視野投射到城市社會上來。1995年《上海文學》連續好幾期都刊登“城市化與轉型期文學”的討論,鄒平、張同安、楊楊、楊文虎等人參與到激烈的討論中。這年第12期的《上海文學》以“編者按”的形式又提出了“讓文學吸引市民”的口號,雖然這個“編者按”只是針對《上海文學》這份刊物,但“讓文學吸引市民”的深層背景卻是中國進入了“城市社會”,出現了大量的市民階層,“編者”敏銳地感受到了這一新群體的迅速擴張:“或先或后更新了自己的生存狀態與價值觀念的那一個社會群體;這個社會群體正在逐步覆蓋我國的城鄉,從東南沿海擴展到中西部內陸地區。”正正是在此背景下,《上海文學》要求作家們把目光投向城市,寫出適合城市讀者的作品。我們在鐵凝的《哦,香雪》中看到,香雪對城市是多么陌生,香雪對城市的陌生實際表明作家對城市生活是陌生的,但當城市生活越來越豐富,創作主體再把目光投向城市,情況就不同了,過去,農村是作家們文學創作的源泉,作家們一提筆自然就想到鄉村,但現在,不再是農村,而是“城市”為作家們提供了豐富的寫作資源。
隨著社會轉型,作家們的心理也發生了變化,逐漸由鄉土心態轉換到城市心態上。從“鄉土心態”朝“城市心態”的歷史嬗變自然是一個漫長過程,并不是每個作家的創作心態都會轉變到城市上來。新時期之初,絕大部分創作主體的創作還是傾向于鄉土世界,1981年前后,圍繞著《北京文學》這份雜志曾出現了一個作家群,對此劉紹棠非常興奮,寫了一篇題為《建立北京的鄉土文學》的文章,標題即顯示出,在劉紹棠的意識中連北京都算不上“城市”,描寫北京的文學竟然被稱為“鄉土文學”;馮驥才也將他寫天津市民生活題材的“小說集”取名為“鄉土小說”。這些作家雖久居在城市里,但他們的心態卻屬于鄉土傳統,所以很自然地把描寫北京、天津等城市的小說看作是“鄉土小說”。高曉聲離開其生活了20年的農村進入城市時,他還是要“為農民立言”。直到1996年殷慧芬還寫了《面對城市》的“創作談”,還談到大批中國作家的“鄉土心態”:
我們曾經很少把自己看作城市的主人。我們永遠認同自己的籍貫,盡管城市已經成為我們生命的載體,盡管我們這些城市移民的后代,已經離祖先的土地很遠很遠。整整一代知青作家,他們就是以逃避城市,回歸鄉村的方式走上文壇的。直到今天他們中的有些人依舊在鄉村的田園里尋覓靈感,盡管他們從來就不屬于那塊土地。
不少作家都懷有濃厚的“鄉土情結”,但隨著社會變遷程度的加深,作家的創作心態實際上發生了微妙變化,他們開始正視城市了。1995年《讀書》雜志發表了由王蒙、陳建功和李輝組成的三人“對話”,“話題”是“時代變化與感覺調整”,即探討社會轉型之后,創作主體社會心理調整的問題,話題要求作家們的心態要跟上時代變化,所謂的“時代變化”便是中國社會逐漸從鄉村社會過渡到城市社會,調整的過程自然很痛苦,有一些作家也無法接受。但說到底,作家接受新事物要比農民容易,畢竟他們與城市擁有更多的“共同語言”,他們對鄉土的眷念只是出于一種牧歌式的浪漫幻想。其實,在改革開放不久,許多作家思想已發生了變化。1983年劉心武發表了一篇叫《登麗美》的小說,小說描寫了主人公看到報告文學多描寫干部和知識分子,就決定另辟蹊徑改寫城市商業題材,主人公的采訪轉向“商業題材”正表明作家創作心態的變化,但此小說隨后受到批評,劉
心武后來寫了一篇文章為自己辯護:
我越來越深切地體驗到,一個民族必須給作家以自由創作的可能,或者反過來說,作家必須以自由的心靈抒寫自己最得意的東西。一個社會的文學創作自由度是高還是低,它的作家們能夠最充分自由抒寫性靈并結出碩果的比例是大還是小,似可成為那一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志。政治家同任何一位讀者一樣,當然有權批評作家和作品,但政治機器對作家和作品的直接干涉是有害的。
從《登麗美》的作品內容,以及劉心武的反駁文章中可以看出,劉心武的創作觀念正在轉變,創作心態開始朝著具有商業氣息的城市傾斜。鐵凝和高曉聲都在描寫鄉土生活,但他們已用眼光去打量“城市”,并開始通過“城鄉對比”來展示城市世界。高曉聲雖然要為農民“立言”,但((陳奐生上城》、《李順大造屋》都有意無意地批判了阿Q式的“農民意識”。賈平凹、張煒等以擅長寫鄉土題材的幾位作家心態更復雜,盡管賈平凹在《廢都》(1993)等小說中強烈批評“城市”,張煒更是號召“融人大地”。但他們不得不面對城市,賈平凹在《廢都》“后記”中,還為自己在城市中生活了近二十年卻沒有寫一部關于“城”的作品而感到遺憾;張煒看起來是對鄉土傳統最執著的作家,他在《古船》、《九月寓言》和《柏慧》中拼命贊美鄉村社會,貶低現代城市。他宣稱:“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飾過的野地,我最終將告別它。”但他卻又說:“剛剛接近故地的那種熟悉和親近逐漸消失,代之而來的是深深的陌生感。”為什么要遺憾?為什么感到陌生?“遺憾”和“陌生”的背后是作家對“城市”與“鄉村”心態的微妙變化。
總而言之,隨著社會轉型,城市本身成為了作家創作的源泉,另一方面,城市本身也成了作家敘述的對象,當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作家們的“城市想象”并不相同,而是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動,筆者即試圖探討新時期之后文學中的“城市敘述史”,這一敘述史大致可以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1978—1987),“城市敘述”主要是一種“現代化敘事”;第二階段(1987—1993)的“城市敘述”則以“世俗化敘事”為主;第三階段(1993—)的“城市敘述”則走向了“傳奇化敘事”。
二《喬廠長上任記》:“現代化”的憧憬
1978—1987年,可以被看作是具有城市生活經驗的作家對“城市想象”的“第一階段”,總體而言,這一歷史時期,作家們的“城市想象”普遍比較簡單,與新時期之后“現代化”歷程同構,基本上是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這具有中國特色“現代化”主題的一種文學想象和詮釋,作家的城市想象還沒有擺脫反映社會問題的宏大敘事模式,表達了對“現代化”的認同和向往,形成了主題先行的“改革文學”思潮。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柯云路的《三千萬》,水運憲的《禍起蕭墻》和陸文夫的《圍墻》,是“改革文學”的代表,側重于描寫“城市改革”,這些作品往往從城市的某個工廠變革入手,引發對民族一國家“現代化”的憧憬。
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發表于1 979年第7期的《人民文學》,這篇小說塑造了一個名叫喬光樸的“改革者”,向局里提出申請,離開舒適“能上能下”的經理職位,到重型電機廠當廠長,發誓要使得電機廠面貌一新的故事。在這篇著名的“改革小說”中,出現頻率很高的一個詞語就是“現代化”,“小說的引子”是喬光樸的“發言記錄”,而這個“發言記錄”大談“現代化”,并將“現代化”和時間緊緊連在一起,“時間和數字是冷酷無情的,象兩條鞭子,懸在我們的背上,‘先講時間。如果說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時間是二十三年,咱們這個給國家提供機電設備的廠子,自身的現代化必八到十年內完成……”“現代化”是主人公奮發向上的動力,甚至和個人命運深刻地聯系在一起,像李歐梵對晚清、民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現代性”的評價一樣,《喬廠長上任記》“對個人的信念與一種狂熱的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那是出于一種著眼于使民族富強的目的”。
不錯,我對電機廠是有感情的。象電機廠這樣的企業如果老是一副爛攤子,國家的現代化將成為畫餅。我們搞的這一行是現代化的發動機,而大型骨干企業又是國家的臺柱子。搞好了有功,不比打江山的功小;搞不好有罪,也不比叛黨賣國的罪小。過去打仗也好,現在搞工業也好,我都不喜歡站在旁邊打邊鼓,而喜歡當主角,不管我將演的是喜劇還是悲劇。趁現在精力還達得到,趕緊抓撓幾年。
《喬廠長上任記》中,改革的正確性是通過喬光樸的行動來體現,主人公喬光樸扮演著一個強有力的“改革者”形象——一位“卡里斯瑪型”的領袖人物,他領導著改革,做事果斷,胸有成竹,并對未來了如指掌,他所設想的“改革方案”,總是符合未來需要。但如果仔細深究文本就會發現,這位“卡里斯瑪型”的改革者必須手握大權,獨斷專行,才可以實施改革方案,“改革”是否成功,也取決于他所掌握的權力大小,如果他是一個普通工人,即使他再有想法,也絕不可能實現改革目標。
絕大部分“改革文學”都按此“宏大敘事”邏輯展開,故事的基本結構通常是這樣組成:一位頗有抱負的“卡里斯瑪型”新領導到達“新工廠”、“新單位”,他立刻發現這個工廠存在官僚作風濃厚、組織效率低下、產品質量差等現象,他便帶領同道者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而改革勢必碰到一批代表舊勢力階層的阻擋,于是故事便圍繞著雙方斗爭而展開。如(《喬廠長上任記))中喬光樸和冀申的斗爭是“故事主線”,最終結果自然總是“改革派”獲得勝利,“保守派”雖然也是權力階層,但由于不能代表“未來方向”,勢必會失敗。
這樣的敘事結構并沒有超越“階級斗爭小說”的思維模式,“兩派對立”仍然是小說的基本結構,小說家試圖成為政治改革的開路者和引領者,蔣子龍在回顧創作時說:“文學作品的功能不是改變制度,倒可以影響制定制度的人。”
有些作家覺察到“改革文學”敘事模式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宏大敘事”本身包含著復雜陛,幸福并沒有一下子兌現,相反,隨著改革深入,問題也逐漸呈現出來;另一方面,宏大敘事模式給文學本身發展帶來了困難。馮驥才在給劉心武的信中,對這樣單一的敘事結構表示擔心,并提出文學“下一步踏向何處”的問題:“本來,文學的道路,有如穿過莽原奔往遙遠的目標,不會一條道兒,一口氣走到頭。但我們這輩作者為什么幾乎同時碰到這個難題呢?看來這是個共同性的問題。”
因此,對城市現代化改革認同的“宏大敘事”雖然是主流,但也有些小說開始擺脫“宏大敘事”,轉而通過描繪普通的生活情景,表達對于城市物質文明和“現代化”的認同。在程乃珊的《蚌——一個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一幕》一文中有這樣幾段對話:
“哦,哥哥,要你再在外地找個對象,那就甭想回上海了。”妹妹嘆息著。(第17頁)
“憑哥哥這樣的條件:海陸空都全,上海
的姑娘都搶著要呢。娶了上海姑娘,家都安在上海了,總能調回來。”(第18頁)
能不離開家了,這真好,盡情享受當代的物質文明吧。彩電、立體錄音機、電冰箱,家里以驚人的速度恢復著,甚至比十年動亂前,還“資產階級化”。(第18頁)
通過哥哥和妹妹的對話可以看出,“上海”是一個“讓人羨慕的城市”,因為它代表著豐富的“當代物質文明”,有彩電、立體錄音機和電冰箱。這些曾經的“資產階級”物質文明,現在卻是被崇拜對象。林斤瀾的《轱轆井》(1981)對于“個體商店”津津樂道地描繪,王蒙的《庭院深深》中“我”去一個古城開會,但“下了火車還想去吃餡餅,想不到餡餅鋪翻修一新”的講述四,劉心武的《登麗美》對“商業題材”的關注,母國政的《大門口兒》對北京青年在胡同里閑聊現象的批評。這些作品均通過“日常敘事”,表達出對現代城市文明的認同。
但另一方面,新時期之初,已有作家對“現代化”感到了不安,覺察到現代物質文明帶來的問題。王安憶的《尾聲》(1981)描寫了文工團老魏的城市觀光活動:“三毛錢買一張票,就可以進去乘電梯到頂樓。頂樓有二十四小時的彩色電視,有象棋、圖書、沙發。陽臺上有長椅,可以俯看城市的夜景。”但老魏在享受城市物質文明,欣賞“城市夜景”的同時,卻立刻想到了另外一個話題:“錢,錢!這究竟是怎么回事?當年打淮海、過長江,咱們文工團演出,從不指望個錢,指望戰士們看了戲……可眼下卻圖起錢來。”老魏為此感到很痛苦。張抗抗的《北極光》(1981)也想象了一幅現代城市的結婚場景,作者也由城市的風俗聯想到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的矛盾:
按照這個城市的風俗,乖乖地坐在床上,讓他給她穿鞋。他一定會非常非常殷勤地彎下身子去,給她系好鞋帶,然后坐上出租車……從前是繡花鞋,現在是皮鞋;從前是花轎,現在是乘轎車——生活的確在朝著物質文明發展,可人們的精神狀態呢?
由“物質文明”想到了人們的精神狀態,渴望“現代化”卻又對之顧慮重重,城市一開始就和“現代化”并不完全協調,很多小說開始對城市中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展開了討論和批判。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1985)、徐星《無主題變奏》(1985)和劉毅然的《搖滾青年》(1985)等作品開始以一種極端的“個人敘事”,抵抗“現代化大敘事”。
總之,在第一階段,具有城市經驗的作家對于城市的想象和敘述比較單一,總體上對于城市文明比較認同,普遍表達了一種建構現代化的熱望,作家們通過一個“商店”、“工廠”和“車間”的變化,反映城市和整個國家的變化。當然從一開始,便有一些作品流露出對“現代化”和“城市文明”的憂慮,而到了1987年之后,這種憂慮轉變為聲勢浩大的城市“世俗敘事”,這便過渡到“城市敘述”的第二個歷史時期。
三《煩惱人生》:城市生活的“世俗敘事”
第二階段(1987—1993年)城市敘述的主要特點是“世俗想象”,即以城市的“日常生活”為敘述的主要內容。在這一時期,“城市敘述”與80年代初期有了顯著不同,創作主體對城市的文學想象開始背離“現代化”主題,不少小說對“現代化”的宏大敘事失去了興趣,相反,關注城市平庸的“日常生活”。這實際上反映了創作主體對于“現代化”認識的加深,“現代化”并沒有帶來一切;同時,這也是不少創作主體對自己生活現狀不滿意的反映,他們感到繁華的城市風景和物質文明,沒有給人帶來幸福,相反,多彩的城市景觀和豐富的物質文明是“煩惱人生”的根源。
“世俗想象”興起于1987年前后,其實也和現代化歷程相關。1987年前后,中國加緊現代化建設的步伐,隨著政治與經濟的迅速發展,日常生活逐漸成了文學關注的中心話題,1987年《上海文學》第6期發表了這樣的“編者的話”: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作者關心自己周圍的日常生活:工廠班組會上的爭論,鄉鎮企業里穿梭往來的經濟聯系……
“編者的話”號召作者放棄現代化的大敘事,關注日常和底層生活。正是在此社會背景下興起了一股“新寫實主義”潮流。新寫實小說家主要集中在《上海文學》、《北京文學》和《鐘山》等期刊周圍,包括池莉、葉兆言、劉震云、方方、何士光、程乃珊和趙本夫等,有寫農村的,也有寫城市的。池莉、葉兆言、劉震云、方方和程乃珊等人主要以城市為創作對象。池莉等人創作了《不談愛情》、《風景》、《機關軼事》、《顧氏傳人》、《一地雞毛》等作品,這些作品把城市看作一個庸庸碌碌、充滿煩惱的世界。在早期的“城市敘述史”中,創作主體的現代城市經驗不足,“城市想象”還停留在對城市的表面觀察上,電梯、沙發、彩電和出租車便是城市文明的象征符號,但池莉、葉兆言、劉震云和李曉已有了深刻的城市經驗,他們的“城市”已不再局限于電梯、沙發這些“物品”,而是擴大到整個城市的日常生活,并賦之以一種觀念和價值結構,正是在此“集體想象”中,“城市”被建構、賦予了一種“世俗身份”:印家厚的人生充滿煩惱,工作突出還拿不到獎金(《煩惱人生》),大學畢業生小林為生活所累(《一地雞毛》);遲欽亭和老婆為了房子四處奔波(《艷歌》);“七哥”一家擠在十三平方米的棚子里(《風景》);“我”的自行車撞了老太太,每天要陪老太婆上醫院,還要為她系褲帶(《五月的黃昏》)。這就是“新寫實”視野中的“城市風景”——一幅庸俗無聊、擁擠不堪的“城市風景”。
池莉的《煩惱人生》是世俗化“城市敘述”的代表作。這篇小說發表在1987年的《上海文學》第8期,據作者回憶,小說發表并不容易,被好幾家刊物拒絕過,被拒絕自然與其“世俗敘述”傾向有很大關系。那時占主導位置的作品仍是“現代化”敘事,描繪普通市民生活的作品并不受重視,所以小說幾經波折,最后才在《上海文學》上發表,但發表后卻反響很大。池莉又陸續發表了《不談愛情》、《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等小說,建構了幅世俗城市圖景。池莉在一篇題為《寫作的意義》的文章中批評了兩種文學傾向:一是翻譯式語言,將國外的東西和五四時代莎菲女士情結結合起來的作品;另外是啟用半個多世紀前的中國語言,“摻雜老莊儒道佛學禪宗的玄妙機制”,她在一篇《胡同幻覺》的散文中,直接嘲笑了被鄧友梅等人所懷念的北京胡同,認為他們的懷舊小說,充滿了文人的虛假想象,“其實我早就應該明白北京的胡同只剩下名字好聽了”。她要按照自己的城市經驗建構一個“小市民城市”:
自從封建社會消亡之后,中國便不再有貴族。貴族是必須具備兩方面條件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光是精神的或者光是物質都不是真正的貴族。所以,‘印家厚是小市民,知識分子‘莊建非也是小市民,我也是小市民。在如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家全都是普通勞動者。我自稱為小市民,絲毫沒自嘲的意思,更沒有自貶的意思。今天這個‘小市民不是
從前概念中的‘市井小民之流,而是普通一
市民,就像我許多小說中的人物一樣。池莉所描繪的城市是建立在現實城市的基礎上的。她對武漢表現出了濃厚興趣:“我拿不準我是否喜歡現在的大城市。但我對它非常敏感。它用高樓大廈、鋼筋水泥和大量的生活垃圾將傳統意義上的小說因素日漸消解,同時卻把人的心無限擴張和復雜化,真可謂人心似海。我拿得準的是,作為一個小說創作者,我喜歡人心似海的現代狀態。這種狀態為被幾千年農業環境所孕育的當代作家提供了一個極富挑戰性和刺激性的創業機會,它使我們的小說創作本身有了歷史性的嶄新意義:你可以不必沿襲傳統的模式和趣味,你也可以不必模仿別國的思想和文本,中華民族正在進行的經歷與承載為小說的創作提供了飽含獨特意味的無限空間。”
在池莉的作品中,瑣碎的世俗生活組成了一幅幅“城市圖景”。在這些作品中,主人公的性格毫無浪漫可言,《煩惱人生》中的印家厚是一名生活在城市底層的工人,他的生活原則就是務實本分,雖然女徒弟雅麗喜歡他,幼兒教師肖曉芬也對他一見鐘情,但這一切都無法動搖他的生活信條,印家厚的至理名言是“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潑潑辣辣,沒有半點身份架子”。在故事中,作者的“世俗認同”往往通過知識分子與小市民的價值沖突來表現,沖突的結果通常以小市民的勝利告終。
武漢的另外一位女作家方方也擅長描寫世俗生活,她的小說《風景》題目便頗具反諷色彩,風景往往與閑暇、浪漫生活相關,但在方方的《風景》中,一日三餐便是“城市風景”,這就是真實的生活。池莉、方方小說自然有真實一面,但“煩惱人生”并不是那個時代獨有的社會現象。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庸庸碌碌、充滿煩惱的生活,“新寫實”只不過是創作主體從自己的城市生活經驗出發,對城市作一種文學想象而已。所以,“新寫實”倡導的“現實生活原生形態的還原”其實根本無法還原,作家趙本夫說:
我過去的創作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我在創作中不愁沒有故事,也沒有生活枯竭的感受。但上了魯迅文學院之后,也漸漸感到按原來的路子寫下去不行了,倒不是為了趕時髦,只是覺得原來的思維方式、表達方法已不適應我們要反映的生活,即使寫出來了也不是自己想的,所以憋了十個月沒有寫東西。后來寫了《涸轍》,自己感到跟過去的作品有變化,寫出了生活的‘原滋原味,新寫實小說的提出,我很快接受的,特別是表現生活的原生態這一點是一致的,一方面可以細到毛茸茸,一方面又很大很朦朧,把生活本身豐富的原生態再現出來。
趙本夫盼話說出了“原生形態”的本質是要按照作家“自己想的”進行文學創作,池莉也說:“我的小說全部都是重建的想象。”
許多人以為“新寫實”的“城市敘述”很真實,但是當新寫實作家所處的環境發生改變,其“寫實”也會發生變化,還是拿池莉小說為例。實際上在早期作品中,作者已流露出對“世俗城市”的不滿。《不談愛情》(1988年)結尾部分莊建亞的“日記”表明她為哥哥找吉玲這樣粗鄙的“小市民”嫂子感到悲哀,認為哥哥可憐。在《煩惱人生》中,印家厚對妻子的相貌和年齡,雖心懷不滿,但能接受;到《不談愛情》時,莊建非對吉玲已有厭倦之心;而在《來來往往》中,康偉業則最終拋棄了“小市民之妻”,與情人同居。新寫實小說的作者逐漸放棄了對“世俗城市”的認同。
四《長恨歌》:一部城市的“歷史傳奇”
1998年池莉發表了《來來往往》,并在“后記”中提到了創作主體的生活狀況,這個時候的“現實”和寫作《煩惱人生》時的“現實”大不相同。
昨天是星期天,《來來往往》已經接近了尾聲,我事先的計劃是可以將它輕輕松松寫完的。可是清早起來做清潔的時候,我們家的狗為了搶奪它的冰棍棍子,無意中咬傷了我的胳臂。傷很輕,我完全可以自己處理一下。但是狗卻不干,它很內疚,老是找我道歉。女兒也湊熱鬧,希望在這大好的春光里全家人出去走一走。這樣我就沒有辦法寫了,不想寫了,就想與他們出去走走算了。于是,我們就去了長江邊的花鳥古舊市場。
這不是寫作《煩惱人生》、《不談愛情》、《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時的池莉,作者的生活和“小狗”、“花鳥古舊市場”關聯起來。池莉的“城市敘述”變化了,越來越離開“世俗化”,而走向了“浪漫傳奇”。《來來往往》的康偉業最初雖與印家厚屬于同一社會階層:是工廠的普通工人。但康偉業后來發達了,而印家厚沒有。康偉業沒有了印家厚那種“雅麗怎么能夠懂得他和老婆是分不開的呢?”的想法,小說敘事者沒有對康偉業的改變加以批評,相反,對他拋棄粗鄙的前妻贊許有加。池莉后期作品中的主人公雖然還是“小市民”,但這類“市民”逐漸離開了那種平庸的世俗生活。在《小姐你早》(1998年)、《驚世之作》(2000年)中,池莉開始追求富有傳奇色彩的城市故事了。
葉兆言、王安憶等人也是如此,他們的“城市敘述”隨著社會轉型和城市本身發展同樣變化了,而且與池莉等人相比,王安憶、葉兆言等人的“城市敘述”有了新的特點。池莉的《來來往往》、《驚世之作》的故事雖有“傳奇色彩”,但這是發生在城市里的傳奇故事,而不是“城市傳奇”,但葉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愛情》,王安憶的《長恨歌》和張生的《白云千里萬里》則都把目光轉向了城市本身,他們要創造一個“城市傳奇”,一個“城市神話”,這是“城市敘述”的第三個階段(1993年一)。在這個階段中,“城市”從背景和幕后走出,被作為一個“主角”去塑造了。
1996年《收獲》雜志第4期發表了葉兆言的長篇小說《一九三七年的愛情》,隨后,《一九三七年的愛情》(1997)的單行本出版,在單行本“前言”里,葉兆言寫下了一段文字,向讀者告白他對“南京”的關注由來已久:
我的目光凝視著古都南京的一九三七年,已經有許多年。古都南京像一艘華麗的破船,早就淹沒在歷史的故紙堆里。事過境遷,斗轉星移,作為故都的南京,仿佛一個年老色衰的女人,已不可能再引起人們的青睞。這座古老城市在民國年間的瞬息繁華,轟轟烈烈的大起大落,注定只能放在落滿塵埃的歷史中,讓人感嘆讓人回味。
單行本“后記”卻又有這樣一段文字敘述:“小說最后寫成這樣,始料未及,我本想寫一部紀實體小說,寫一部故都南京的一九三七的編年史,結果大大出乎意外。”這段話說明作者本意是要“代史立言”,為南京寫一部“博考文獻,言必有據”的“城市編年史”,但結果“正史”被寫成了充滿個體想象的“城市野史”,宏大的“城市編年史”變成了一個叫丁問漁的教授追逐女性的浪漫故事,但這是否如作者所言,大大出乎“意料”呢?為此,我們再看“后記”之“后”一段話:“我注視著一九三七年的南京的時候,一種極其復雜的心情油然而起。我沒有再現當年繁華的奢望,而且所謂民國盛世的一九三七年,本身就有許多虛幻
的地方。一九三七年只是過眼煙云。我的目光在這個過去的特定年代里徘徊,作為小說家,我看不太清楚那種被歷史學家稱為歷史的歷史。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一些大時代中的傷感的沒出息的小故事。”
這段話表明小說不但不是“意外”,而且是意料之中的敘事策略。參照葉兆言的“秦淮系列”(《狀元鏡》、《追月樓》),我們可以發現,作者所追求的正是背離歷史主義的“城市敘事”,《狀元鏡》的故事背景也是民國時期的南京,但“南京史”中的主角只有一兩個,而且“名不見經傳”,看來是否為“南京”寫一部宏大的“城市史”并不重要,作者只是通過小說虛構一個屬于城市的“浪漫傳奇”而已。葉兆言曾在《花煞》里專門描述他“虛構”一個城市的過程:“這是我很用心寫的一部書,花的時間也比較長,寫這部書我是有想法的。首先這是我在小說中虛構一個城市的開始。這以前我的小說中有秦淮河這樣的點,但這只是利用,只是到《花煞》時才突然決定虛構一個城市,它有了一種誕生的感覺,給我以領土的歸宿感,這以后的小說將多以這個城市——梅城為背景。”
1993年《收獲》發表了王安憶的《紀實與虛構》,在“引言”中,王安憶說:“我最想叫它為‘上海故事,這是個具有通俗意味的名稱,取‘上海這兩個字,是因為它是真實的城市,是我拿來作背景的地名,但我其實賦予它抽象的廣闊含義。”四在這里,王安憶已經表明了,她取“上海”這兩個字,并不僅僅因為它是真實的城市,是故事背景,而要“賦予它抽象的廣闊含義”。隨后,王安憶發表了著名的《長恨歌》(1995)。在這部小說里,她更清晰地表明其創作企圖,她要直接在紙上重建一個城市,重建它的街道、樓宇和思想。在池莉小說中,城市是背景,為人物而存在,但在《長恨歌》中,城市不再為人物而存在,相反,人物存在是為了城市本身。“在那里面我寫了一個女人的命運,但事實上這個女人只不過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寫的其實是一個城市的故事。”
我是在直接寫城市的故事,但這個女人是這個城市的影子。‘所以你們在看這部小說時可能會感到奇怪:我那么不厭其煩地描寫這個城市,寫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氣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不是通過女人去寫,而是直接表現。
為何在1993年之后,王安憶、葉兆言和張生等人都不約而同地要虛構一個“城市故事”,書寫一部城市的歷史傳奇昵?
實際上,這說明隨著中國社會轉型與城市發展,作家們越來越關注城市自身。在池莉等人的作品中,城市作為社會和地理背景存在,就是在王安憶的早期小說中,城市也只是故事背景,是為人物而存在,但現在,王安憶等人意識到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塑造的“角色”。在這里,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到底是何模樣,已無法知曉,那些有關的歷史記載也只是片言碎語,并不可靠。作家們完全可以進行再度虛構,虛構街道、人物和精神。王安憶在《長恨歌》開頭便大段描繪上海的“城市風貌”,葉兆言在《一九三七年的愛情》中,亦煞有其事地大段描繪“1937年的南京”:“大興土木使得南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都市氣概。南京開始真正地變得繁華起來。一座座新穎別致的小洋樓拔地而起,這些美麗的小洋樓中西合璧,基本上都是那些留洋的歸國工程師設計的,風格多樣,有歐美式,也有東洋式……”他們都按照個體想象,虛構了一座“傳奇城市”。
總之,王安憶、葉兆言等人的“城市敘述”,與池莉等人的敘述已有了很大差別,他們并不把城市看成是人物活動的背景,而是已經越來越有意識地按照個體想象虛構一座城市的“傳奇故事”,“城市”自身成了這個傳奇故事的“主角”。1997年第10期《上海文學》發表了《城市與女性視角》的“編者的話”,針對殷惠芬的《焱玉》、唐穎的《愛的歲月最殘酷》、王安憶的《蚌埠》和陳丹燕的《上海女性》等作品,作了這樣說明:
我們所處的城市,正在發生越來越多的變化,它改變了我們原有的各種想象方式。而正是在這個時候,女性作家憑藉她們天賦的敏感
本能,展開了對世界各自不同的想象。王安憶、陳丹燕等人越來越有意識地虛構城市,是因為她們所處的城市本身正發生了越來越多的變化,這使得她們對城市本身的認識越來越深入。茅盾、穆時英會說他們筆下的“上海”就是“真實的上海”,但王安憶不會說其筆下的“上海”,就是30年代的“上海”,而是會說,她覺得30年代上海就應該是《長恨歌》中_的那個樣子,她遵照內心的虛構和想象,重繪了上海的地圖和精神狀況,至于這個“上海”是否符合歷史原貌并不.重要。
當然,王安憶、葉兆言等人重新敘述的“城市傳奇”,亦非毫無緣由,我們前面已經說過,是基于中國當下的社會轉型和城市發展,實際上,王安憶等人的“城市敘述”,也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個體虛構的愿望,而是出于對“中國現代化史”的重新思考,關于這點,《上海文學》曾對新時期以來大量的“上海想象”這樣解釋:
我們選擇“上海”,乃是因為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上海”已經不再是,或者說,不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域名。它更多的成為一個符號,它的昨天和今天,它的起起落落,它的悲劇和喜劇,無不昭示著中國現代化的經驗和教訓。
王安憶等人另類的“城市敘述”實際上與中國現代化“經驗和教訓”緊密聯系,關于城市的各種“野史趣聞”和“浪漫傳奇”,其實都包含了作家對城市和中國“現代化史”的一種獨特理解,可以說,王安憶等人的“城市敘述”,是對中國“現代化史”這種宏大敘事的補充,展示了“中國現代化”總體歷史所忽視的一些層面。
結語
本文探討了新時期之后作家們“城市敘述”的變化歷程,從早期追求一種“現代化敘事”,“城市”被看作是物質文明和現代文明而被崇拜;到隨著社會轉型,一些作家開始擺脫“現代化”大敘事,認同“世俗城市”;再到隨著城市的發展,作家們不滿足于“世俗化敘事”,轉而虛構一個城市的“歷史傳奇”。這種變化反映了作家們對于城市的認識越來越深入,在這一過程中,“城市”逐漸由客體,變成了一個主體。同時,作家們對于城市敘述的“變化史”,也從另外一個視角,折射出“中國現代化史”的復雜性。
責任編輯董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