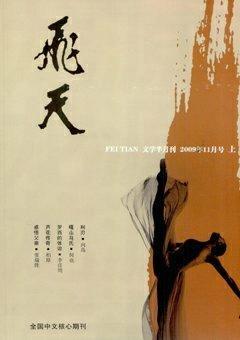《青春之歌》的鏡像分析
在創作主體自覺不自覺地將“自我”懸置的時代,具有自傳性、被戴錦華稱為“一部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手冊”的《青春之歌》,卻成為紅色經典之一。但是,看似單純的文本是否真的能如時代所愿的那樣隱匿了其他的可能性,在經過歷史去魅的洗禮之后,在敘事的間隙,潛在的層面,有哪些仍然值得我們注意的痕跡?
一、文本鏡像
在拉康早期的論述——鏡像階段(Mirror Stage)中論及,鏡像階段是嬰兒生活史的關鍵時期與重要轉折,這是每個人自我認同初步形成的時期。嬰兒在“不是他”的地方見到了自己,在一種想象的層面上認同了自身的影像,他會把鏡像內化成一個理想的自我;并且不僅僅是對于自我的認同,主體對任何對象的認同都是一種期待的、想象的與理想化的關系[1]。這種想象的探索和作家的創作有著某些相通之處。作家往往會在作品中寄托自己的理想,通過塑造人物及文本敘事表達自我主體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完成對自我的不斷確認。
美麗、熱誠,還有些天真任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林道靜,剛邁入社會時荊棘密布,幾次險些被黑暗的濁水吞沒,所幸前有溫情的騎士救美,后有瀟灑或深沉的革命者傾心指引,愛情與革命是成長的催化劑,使自我身份逐漸清晰,自我鏡像也在愛情與革命中得以彰顯。從浪漫愛情到柴米夫妻,堅定的人生抉擇,深切的革命情誼,林道靜似乎成了另一個林紅,后者“大理石雕塑的絕美的面龐”正是前者成熟的自我鏡像。
想象是作家的思維方式,現實的碎片在想象中整合,林道靜的身世之感,失學失業的焦灼,個人情感的起伏,革命的執著,都有著作者的真切體驗,隱現出自我的影子。1950年10月7日日記:“忽然,我被某種說不出的創作欲望推動著,每日每時都想寫——一些雜亂的個人經歷,革命人物的命運,各種情感的漂浮,總繚繞在腦際,沖動在心頭。”[2]與盧嘉川原型路揚的曲折感情引起的情感激蕩,無疑是激發其創作的一個重要契機,成就了文本中最動人的愛情。1951年日記,“九月一日 ,忽接s 信。……使我又高興又驚奇。…… 我應當在未來的小說中,寫出這個人物,……寫出他對我經受了考驗的感情(也許只是一種幻想的感情)……使他永遠活著——活在我的心上,也活在億萬人民的心上。”
一個女人和三個男人的故事套路產生了超時代的魅力,舊小說的“才子佳人”變為“英雄美人”,30年代左翼文學風行的“革命加戀愛”模式似乎再次得到延續。茅盾先生曾經著文討論的革命與戀愛的三種敘事模式,在文本中相繼演繹了一遍:為革命犧牲了戀愛,導致林、余的分手,林與盧則是革命與戀愛相因相成,林、江之間是因革命產生了戀愛。
描摹著愛情瑰麗、充溢著革命激情的青春,形成了人物的自我鏡像,在成長的道路上要克服多愁善感、軟弱、幻想等個人弱點的林道靜,面對的正是這樣一個主體不斷自我認同與發展的過程。林無疑又是作者的自我鏡像,隱含著作者的想象、理想與期待。突出的一點,在性格氣質上,文本中的主人公有強烈的社會歸屬感,她努力謀求職業,希求同代人之間的社會聯結,而不愿做一個居于附屬地位的傳統的家庭婦女,作家自己也在1955年12月14日日記中表白,“(我)喜歡把自己投入于一種湍急而激越的生活中。我的內心是極端不平靜的,為了一種夢想的生活 ,和一種應當那樣活下來的生活 ,我投身在兩個極端中。”林即是作者想象的理想自我鏡像,此鏡像的形成,有創作主體欲望情感的真實映現,而周圍的現實境況,也以互文的方式進人了文本的創作,透射出作家在多種鏡像映射下的復雜心理。
二、現實鏡像
基于嬰兒期的鏡像體驗,拉康進一步指出所謂的鏡像并不只限于真實的鏡子,也包括周遭他人的眼光與其對自我的反映,來確立主體在成長過程中的認同。圍繞《青春之歌》,周圍的他者,以各種不同的鏡像出現,導致了楊通過文本進行的一次次自我確認。
對《青》這一文本進行解讀,可以發現在紅色經典的內部,敘事的間隙,各種意識如一個多面鏡,互相的角力,余永澤的出場可說是五四個性解放的余緒,林、余二人的浪漫同居與江華的一夜情都帶有這種色彩。文本中林提到鄧肯的自由個性與愛情觀,自己的抱負期望,部分來自創作主體的閱讀積累。后來對歷史人物胡適、蔣夢麟的一番丑化,與現實中對胡適的政治批判運動有關。相應地,是林要迫切地求得鄭德富的認同,甚至到模糊嗅覺的地步,這無疑帶有左傾思潮的影響。后來林革命意識成熟的標志,是越來越熟練地操縱革命話語,思想言論多來自時事的引文。這些博爾赫斯所說的“引文”,存在于紅色經典的敘事中,對其意識來源做著現實注解。
將自身經歷概括為“革命加文學”的楊沫,對自己的這兩個選擇都懷著足夠的自信和熱誠,懷揣革命者對未來時間的激情,和新世界主人翁自豪感的作家,卻因為種種原因從“中心”暫時退居“邊緣”。疾病是一個客觀原因,促使她投入艱辛創作的,還有現實環境的刺激。1947年 11月 26日與1951年5月6日兩次日記都提到“中灶”待遇問題,1951年初到1952年11月近兩年的時間,組織關系從原單位調出后一度沒有落實 ,在五六十年代高度集體化、組織化的社會中,楊沫似乎成了編外人員,這雖然能使她少受干擾,較好地保留真實的生命體驗和感受,但內心是十分焦慮的,一個有著強烈自我實現欲望的人,必然努力向中心靠攏。
寫作《青春之歌》,營造主人公鏡像,正是她進行自我認同、重塑自我的途徑。在特定的意識形態籠罩下,文本題材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本的構成方式與命運。據披露的書信資料,稿子1955年初在中國青年出版社露面,1956年6月18日在楊沫的書信中,已轉交人民文學出版社,但遲至1958年1月才出版。“如果是搞個寫小資產階級的帽子當時也是要挨批的,” 楊沫似乎也在時代的光影中看到了文本的命運,不免心里惴惴,1956年12月16日日記:“那本可憐的書 (《青》)可以見世面了么?人們看了,將如何評論它?會不會批它在美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不是批它丑化了共產黨員?”
作為鏡像的“他者”起了參照物的作用,推動了文本象征化的過程。在作品問世出版的前后,外界的反響,如潮起潮落,形成沖擊,她不斷地據此進行自我調整與確認。1958年7月19日日記:“他 (北大黨委書記陸平)一股勁問我:‘用兩年時間怎樣? 兩年怎樣? 一定寫出來吧! 這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太需要了! 你要不寫,我叫學生寫信催你寫。”作品出版一年后,1959 年2月28日日記:“……看了郭開又在《文藝報》上發表的批評《青》書的文章,……我才意識到了。改,堅決地改!”工人郭開兩篇上引毛澤東的“講話”,下有工人聲音的文章,使她不能坐視,撇開茅盾、何其芳等人的肯定之詞,幾個版本幾經修改。在時代政治和文學審美之間,創作主體作了一次次周旋,向時代政治中心一次次靠攏,產生了最后的結果——高度敏感自覺、自我規范的創作主體,以及敘事中心由戀愛向革命的逐漸挪移。
“舊事重提是為了鏡照現在,所謂懷著對未來的期待將過去收納于現在。為了解釋當前,而將舊事反復重提,使之成為現實的一項注解,舊事也就‘故事化、‘寓言化了”[3]。自我的舊事成為一代知識分子革命心路歷程的象征,文本也相應成為公共性的教育讀物,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范本。《青》因此成為可讀與可寫的文本,主人公的一再被改寫,賦予他者另外的象征意義,構建了歷史的自我影像,與創作主體的自我異質同構。我們只有借助他者的多重鏡像,在想象、現實、象征幾個不同的層次中,才能看到趨向完整的主體自我。
【參考文獻】
[1]拉康.拉康選集 [M].儲孝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
[2]楊沫.自白——我的日記 [M].楊沫文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
[3]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110.
(作者簡介:徐文靜,臨沂師范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