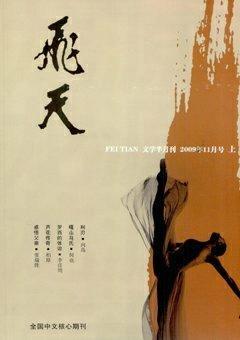“伙頭進,炕上坐”
許文郁
“伙頭進,炕上坐”,這是在康樂插隊兩年多時間聽到次數最多的一句話。
1968年的年底,還是中學生的我和學校里大多數“狗崽子”(當時對所謂出身不好的同學的蔑稱)一起列入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名單被趕出城市,下放到當時最偏僻的山鄉,從此我們進入到社會最底層。幸耶?悲耶?那時候的城市早已是一個大戰場,階級斗爭的不斷升級把人性中最丑惡的東西釋放了出來了,斗爭成了生活中的唯一內容,人與人之間互相防范,互相爭斗,他人是陷阱,處處設藩籬。父母、兄妹、夫妻、朋友,最基本的親情消失了,人人都變成烏眼雞。但在那貧瘠的鄉村,我們卻意外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體會到愛的溫暖,尋求到做人的尊嚴。
那是祖國西北一個偏僻的少數民族地區,我所去的生產大隊,百分之九十都是回民,人均工分值一角左右,一年也只能分到百十斤糧食。剛下去時,因為經歷了城市的人人自危,我們對自己的出身和村民的出身都很在意,不敢隨便串門,生怕走進階級敵人家中。但老鄉們卻從沒有問過我們這些知青的家庭出身,不論何時,不論你走到哪一家門前,認識或不認識的主人都會對你說:“伙頭進,炕上坐。”然后端上火盆,吹紅火盆里埋著的火種,開始給你熬罐罐茶, 出面柜底下僅剩的一點面粉為你烙油香。
這似乎是當地的習俗,不僅同在一個生產隊的老鄉是這樣,在西部偏遠的鄉下,幾乎每一家的大門都會向外人敞開。老鄉們那憨厚而親切的笑容,讓走到這里的每一個人呼吸暢快,自然地找到了做人的尊嚴。
一年春節,同學們都回城里過年了,無家可歸的我決定去附近林場姐姐處。當我在路口等車時,往日繁忙的公路上竟然沒有一輛車,我從清晨站到中午,又凍又餓。路邊有一戶人家,在我等車時就曾招呼我去他家里,中午時分,主人又出來招呼我“伙頭進”。我渾身哆嗦著跟他進了屋。當我的眼睛習慣了室內的黑暗時,看到炕上,擺著一張炕桌,桌上一大盆羊排骨正冒著熱氣。“炕上坐。”主人說著,拿起一塊羊排遞給我:“來,抓住。”我的眼睛濕潤了。兩年前,當父親用一根繩子結束了生命時,茫然無助的我敲不開平日熟悉的人家大門,可是在這個鄉間,在這陌生人家中,我卻得到了貴賓般的待遇。
又一次我從省城返回康樂,班車出發時出了點問題,到達中轉地時已是下午五點多,去康樂的車早已開出,我向周圍的人打聽旅社。一位老鄉告訴我某處有個店,沒等他說完,另一位穿著制服的人接了話:“那個店里都是男的,她一個女娃怎么住?”說著,他轉向另一位老鄉,似乎讓他去找什么人。一會兒,那位老鄉從街角轉出來,身后跟著一位二十多歲的女子,穿一件那時候很時髦的藍的卡上衣,渾身上下干干凈凈。她走到我跟前,笑吟吟地對我說:“去我家吧,我一個人。”
當我隨那女子進了她的房間時,眼前一亮 :一張白紗蚊帳將房屋的大半間隔開,蚊帳里是一張雙人床,床頭一個大大的紅雙喜字把整個房間映得喜氣洋洋。原來這是她的新房,我頓時不好意思。“我丈夫回部隊了,今晚咱倆就一起睡。”新媳婦一邊鋪床,一邊跟我聊起來,原來她是郵局職工。當她得知我是從省城來的知青,便問我:“你爸是做什么的?”我頓時緊張起來。父親是大學教授,在那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歲月,教授就等于反動學術權威,而我也就成了先天的罪人,動輒挨罵受批,所以我最怕別人問自己的出身。但面對她的誠懇,我不能撒謊,便告訴她父親在高校工作,沒想到她卻馬上追問:“你爸是大學教授?”我一驚,她怎么知道我爸是教授?看著她手里拿著的掃床笤帚,我緊張得不知該怎樣回答,腦中閃過一年前校園中的一幕:一個出身軍干家庭的低年級同學,“文革”前因為同樣愛好體育,成天跟在我身后叫姐姐,“文革”開始后,她卻將帶鐵扣的皮腰帶抽向我這個“反動學術權威”的女兒。
望著窗外漸暗的天色,真有些絕望了。可是我又不習慣撒謊,只好承認。“你爸是教授?你爸真是教授?”新媳婦的眼睛一下子睜得很大,她停下手中的活兒瞪著我。我更加緊張了,心撲騰撲騰地跳著,低下頭,像一個等待刑事判決的犯人。“你真幸福,有一個教授爸爸,我特別仰慕大學里的教授。”我又一次吃驚,懷疑自己聽錯了,這年月,還有人敢說他仰慕教授?而且是一位軍屬。“你們家的書很多吧?”我想起父親書房中那排滿一面墻壁的五個大書架上的書,父親去世后,一位軍代表看上了我家原來的樓房,全家人被趕出了教授樓,那幾千冊書也都拉到了學校辦公室。“書都上交了。”“那太可惜了!”
新媳婦垂下眼瞼,嘴唇緊抿著,半響沒有說話。看著她的表情,我懸著的心放下來,暗自捉摸:教授值得仰慕嗎?雖說有一個教授父親,但過去我對他的感情是畏懼甚于尊重,而文革開始后,我也參加了批判父親的行列,甚至在父親只能用一根麻繩維護做人的尊嚴時,我也沒敢在人前掉淚。
四十多年過去了,那夜夜在炕邊守著我進入夢鄉的房東老阿姆,那接待我的新媳婦,還有公路口那戶把我請到他家炕頭吃羊排的人家,都常常出現在我眼前。在那最艱苦的日子里,有些老鄉家中炕上連一塊完整的氈都沒有,更遑論被褥,幾塊破麻袋片鋪炕,一件破裹頭(棉襖)蓋身,四季如此,鄉親們卻總是張開胸懷迎接我們。對比從小生活過的城市,我不知道哪個更親切。
都說城市代表著人類的文明進步,但在那荒誕的歲月里,文明的含義就是壁壘與爭斗嗎?平等、關愛、寬容、理解,這些最基本的人性哪里去了?看來文明并不完全等于物質的豐富。我們古代的先哲老子早就說過:“絕圣棄智,民力敗北;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也許這位倒騎驢的思想家是過于消極了,但他那反思人類文明的話語卻不能不給我們啟示。
城市、鄉村孰更文明?我不想在這里具體辨析,但我認為,文明的本義應該是人性的充分發展與成熟。可是文明常常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接過去,巧言令色,為原始的私欲制造變臉,于是,各種荒謬的行為便常常會集中在都市上演。而當各種非人性的暴戾充斥于都市上空時,在偏遠的鄉村,在社會的底層仍然存在著最基本的人性。
“伙頭進,炕上坐。”這就是最基本的人性,這樸實的鄉音用文明詞匯翻譯出來,可以說是平等、寬容、信任,是一種無私的友愛,而它的基點,便是以人為本。底層人是不會說“以人為本”這個詞的,但底層處處體現著以人為本,這是底層人的存在方式,是底層最真實的人性。從這里出發,任天災人禍,強權暴政,無論何種族,無論何信仰,底層的人不僅從不放棄最基本的人性,也從不放棄對美的追求,對文化的仰慕,對知識的渴望。
其實,一切抽象的理念無不來自生活深處,社會的底層永遠孕育著人性最珍貴的種子,文明的進步從來離不開底層的滋養。四十多年過去了,那些深植于底層沃土的人性之花逐漸在整個社會盛開,民間的情感升華為全體民眾的共識。
2008年,首都北京的大街小巷傳唱著一首歌,那清新優美的旋律,樸實親切的詞句,像一股清泉沁入人們的心田。“我家大門常打開,開放懷抱等你。”多好!透著平等、透著理解,如清風徐徐,似山溪流淌,看不到都市的傲慢,熱情和自豪中卻有著深深的愛意和對溝通的渴望。不知為什么,每當聽到這句歌詞,我耳邊總是響起那令人魂牽夢繞的聲音:“伙頭(屋里)進,炕上坐。”仿佛時空大挪移,一個是西部農村樸實的鄉音,一個是現代都市清甜的民謠,時間跨越近半個世紀,空間相距近四千里,但兩者的情感基調卻何其相似。
這不就是“伙頭進,炕上坐”的現代版嗎?每當唱起這首歌,我心中總會有一種深深的甜蜜感,一種遙遠的,帶著山野清新的氣息縈繞著我。我覺得這二者一脈相承,有著同一根系。這就是那種以人為本的基本情懷,它的根系延展得無比深遠。這也是一個象征,是最基本的人性的復歸,它唱出了多少人的渴望,它也將長久地傳唱下去,因為在那優美的旋律背后襯著樸實的鄉音,那清新活潑的歌詞正因為有了厚重的底色而晶瑩堅韌。今天我們看到,無論城市,無論鄉村,人心打開了,心靈的柵欄解除了,人們正在張開胸懷,擁抱整個世界。家門開放了,國門開放了,思想之門開放了,情感之門開放了,整個社會正在逐步變成一個和諧開放的大花園。
責任編輯 子 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