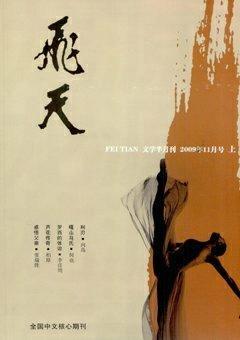論文學與音樂之間的相互聯系
音樂是人類社會產生最早的藝術之一,是人類最親密的東西。因為它可以備于人的一身,無待外求,所以在人群生活中發展得最早,在生活里的影響勢力也最大。詩、歌、舞三位一體的擬容動作的綜合藝術,也就最早地結合在一起了。音樂與文學從表面上看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門類。音樂是通過音響的組合達到表現的目的,而文學的表現目的則是通過語言的手段去達到的,但是,語言與音響在表現形態上又有某種一致性,這些都是通過聲音來展示的。
一、音樂與文學的共性
音樂作品或是文學作品,均具有作品的開端、發展、戲劇性沖突和結束的整體結構。這是一個有邏輯性的有機整體。任何文學作品均有故事的開端、發展、戲劇性的矛盾沖突,或悲或喜的結尾。音樂也同樣,奏鳴曲式中矛盾的提出便是呈示部中兩個互相對置的部分,展開部使兩部分音樂發展趨于不穩定,使矛盾激化。再現部通過統一兩部分矛盾的調性使音樂逐漸走向穩定,解決矛盾并結束全曲。
文學作品中蘊含音樂性。在文學作品中的詩詞,其語言的構成因素中,節奏與韻律是其靈魂和生命。朱湘說:“詩而無音樂,那簡直是與花無香氣,美人無眼珠相等了。”甚至有人將文學與音樂并稱為“時間的藝術”。兩者之間共通的時間性因素是節奏和韻律。節奏是音樂和文學諸多藝術中共同具有的基本要素。音樂作品中也蘊含文學性。在文學作品中,動人的作品其共同特點就在于塑造典型的文學形象,是衡量其審美價值的重要標準。對音樂創造也一樣。作曲家采用典型的音調、節奏、和聲等手法,以獨特的個性去感受、尋覓能用來表現音樂形象的典型手法、能表現作品內蘊的情態來體現在自己的創造中。
二、音樂與文學的差異性
音樂的過程與文學的過程各有自己的特點。文學展開的是客觀世界的過程,而音樂展開的是主觀世界過程。文學作品所揭示的是故事情節的過程,音樂作品卻無法展示,它所展示的是一種建立在模仿、象征、暗示和表情基礎上的表現過程,主要是人的內心世界。音樂的過程固然不同于文學的過程,但它卻為聽眾的文學性聯想提供了過程的依據。正因為如此,人們才能夠從音樂中感受到富有過程性的文學性內容。
從藝術分類講,文學屬于再現藝術,音樂屬于表現藝術。作為再現藝術的文學,自然和實體對象關系最為密切,具有鮮明的形象性。而作為表現藝術的音樂則與之截然不同,具有鮮明的情感性,這是毋庸置疑的。從人的感受上來說,音樂直接訴諸聽覺,它又是聽覺藝術。而文學直接訴諸視覺(不包括說唱文學),它又是視覺的藝術。對于這種感覺上的區別,古羅馬詩人卡爾·盧克萊早就說過:“對于每一種感覺,都賦予了特殊的領域和能力。因此就必然有了特殊的感覺。”
三、取材于文學作品的音樂作品
古今中外,有許許多多優秀的音樂作品取材于文學作品。例如:柏遼茲的交響樂《羅密歐與朱麗葉》,李斯特的交響詩《浮士德》《塔索》。德彪西的管弦樂序曲《牧神午后》等均出自文學作品。以我國傳統戲曲音樂中的說唱音樂來說,京韻大鼓《逼上梁山》就取材于文學名著《水滸》。在我國現代的器樂作品中,如陳剛、何占豪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以及近期的青年作曲家譚盾創作的交響樂《離騷》、弦樂四重奏《風雅頌》等都取材于不同的文學作品。這類音樂與歌劇和歌曲不同,雖然取材于文學作品,但它們的構思線索并不是文學原作的情節或思想發展過程,而是根據音樂藝術的特征,以音樂發展的需要與可能性為出發點,從文學原作中提取必要的過程和沖突作為音樂構思的基本線索,或從文學原作中提煉它的精神實質作為音樂構思的基礎。
有些音樂作品并不直接取材于某文學作品。有些作曲家在創作過程中采用一些文學性的記錄作為作曲構思的基礎,如柏遼茲的《幻想交響曲》,每一個樂章都做了具體的文字說明。有些音樂作品并沒有具體的文字說明,但它們的標題及音樂發展的各個階段都能夠比較形象化地為聽眾提供想象的依據。當然,音樂中所渲染的情緒氣氛與它所暗示的對象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正如托馬斯·門羅所說:“音樂中暗示出來的情緒總是模糊不清的,并且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解釋。”但是,正因為含糊不清才需要我們用想象去為它澄清,而我們的想象依據又正是作曲家對它的暗示和象征所做的文學性約定。
四、文學作品中表現音樂的文章
最早專門描寫音樂的是《詩經·小雅》中的《鼓鐘》一詩,詩中無一句正面描寫音樂,它是用“借賓形主”之法,將筆墨全用在寫樂器上,通過描寫樂器的演奏,來表現音樂的美妙。寫樂器的重點又放在主樂器編鐘上,全詩四章,每章以“鼓鐘”起句,突出編鐘奏出的旋律在樂曲中的主導地位。結尾眾樂合奏,使人感到美妙和諧的音樂境界,其詩寫音樂富有想象力和創造性。
魏晉南北朝音樂有較大的發展,描寫音樂的作品比較多。謝朓的《和王中丞聞琴》寫音樂不從實處見工,而從虛處傳神,著意渲染聞琴時的環境與氣氛,作者的印象與感受,因而給人以更多的聯想。沈約的《詠箏詩》是通過視覺形象,即彈箏時的弦、指變化,表現聽覺形象,即樂曲旋律的緩急斷續變化,從而表現復雜的音樂形象和音樂情緒,使人領略到音樂的妙境,表現箏曲之優美動人。
白居易的《琵琶行》歷來為人們所稱道,被認為是中國詩史上寫音樂最為杰出的一首,其寫作技巧非常高妙。他把彈奏者起伏跌宕的思緒貫穿于演奏始終,使其音樂內容具有明確的主題。寫演奏時邊寫指法技巧,邊寫奏出的樂音。寫樂音,使用了各種手法,不僅以視覺比聽覺,而且以聽覺比聽覺,強化了音樂的形象。李白的《聽黃鶴樓上吹笛》是由笛聲中的樂曲名聯想到音樂形象,以幻想中的音樂形象描繪蒼茫景色,從而烘托作者心中的悲愁情緒。劉長卿的《聽彈琴》手法更為特別,他是將聽覺訴諸觸覺,暗示琴聲的凄清,引導讀者進入那凄清的音樂境界。
而到了中國的近現代,音樂則更緊密地和文學連在了一起,現代自由體的白話詩,有許多被譜曲傳唱:如趙元任曾為胡適的《也是微云》《上山》、劉半農的《教我如何不想他》《聽雨》、徐志摩的《海韻》譜曲。這都是音樂與詩的最高層次、最完美的默契。而像趙麗宏的散文詩《小提琴獨奏》學習古人技巧,將難以捕捉的旋律狀寫出來,顯得神韻俱足,情景活現。郭風的散文詩《笙歌》在寫音樂時不從正面細致刻畫,而是跳躍式的在關鍵處點幾筆,激活讀者的聯想,去領略作品的意境,也很成功。
總之,音樂與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們都表現了人類最真摯的情感,而且都能互相成為創作與借鑒的對象。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更加多元化的音樂與文學的結合形式,將有待于我們繼續探索和發現。
【參考文獻】
[1]毛麗偉.音樂與文學的幾點相關性研究[J].河南社會科學,2006,(7).
[2]楊洪冰.論音樂與文學相互融合的美感[J].樂府新聲(沈陽音樂學院學報),2000,(2).
[3]田春生.淺談文學與音樂塑造形象方式之比較 [J].湖北教育學院學報,2007,(4).
[4]尹勛鋒.試論音樂與文學之間的必然聯系[J].江西科技師范學院學報,2008,(4).
[5]史麗欣,趙敬蒙.音樂與文學[J].文學自由談,2006,(3).
[6]尹勛鋒.文學作品的音樂描寫技巧探微[J].重慶工學院學報,2005,(7).
(作者簡介:安慶武,河南大學藝術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