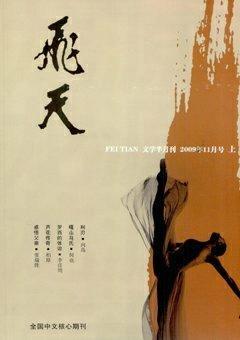靜默與本色之詩
《易經》賁卦中有這樣的描繪:“上九,白賁,無咎。”“賁”是斑駁華才,絢爛的美。“白賁”,則是絢爛又復歸于平淡。因此,《易經》雜卦說:“賁,無色也。”這里包含了一個重要的美學思想,就是認為要質地本身放光,才是真正的美。這種思想在中國美學思想史上影響很大。劉熙載《藝概》說:“白賁占于賁之上爻,乃知品居極上之文,只是本色。”中國人作詩作文,講究“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白賁,從欣賞美到超脫美,所以是一種揚棄的境界。而中國當代詩歌由于受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長期以來強調的是政治立場和浪漫理想,無形中就忽略了詩歌的美學特色,遠離了詩歌本體特征。這造成了中國當代主流詩歌在美學上的嚴重缺失與不足。關于其中的原因,有這樣的一個因素是不容忽視的,那就是當代主流意識形態對詩歌的限制與要求,洪子誠認為“藝術借鑒的狹隘、單一,以及將獨特的發現和探索當作‘個人主義加以責難的文學思潮,規定了這些詩人可能的藝術道路,是尋找對己確定的政治觀念、社會情緒的稍有特色的表現方式。偏離思想、藝術規范的試驗的合法性問題,在當代這一時期,不可能獲得解決。因而,他們的個性特征和詩歌風格或者根本沒有形成或者未能充分展開。”[1]這無疑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實!但今日,我們到了重新審視詩歌的審美標準的時候了!本文就是以這樣的出發點試圖來重新認識和研究中國詩學中的美的標準,重新打量中國當代詩人的詩歌。而作為西部重要的當代詩人人鄰的詩歌無疑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和視角。先讓我們來讀讀人鄰的詩歌:
暝色,游人遁去/跌落的松果/只是一
些微微翹起的聲音,干燥而悄然//我尤自
迷戀/ 藍色的月光,最后的喜鵲叫聲里返
身照耀/ 我只是還在松脂如酒的醇厚氣味
里/要等到周圍的松林,百步以外/寧靜
如禪,暝色里淺淺的澗流/月的光亮比苔
綠的石頭,石頭比時間/還要頑強,還要令
人難忘
——《山頂的松林里》
再來看一首:
我看見一片白/陰郁暗淡的白,有些
銀灰的/ 一片白色的偶然/仿佛月光,也仿
佛雪的一個斜面/借著暗黑的巖石/而漸
漸有了鋒利的分量//些微的冷風擦過,一
再,擦過/ 而讓人感到微微的顫栗/斧刃的
銀灰冷而疼痛地/借著巖石翹起
——《月下山坡》
從以上的詩歌可以看出,靜默構成了詩歌的底色,詩歌的力量來自于靜默中,詩歌的意蘊來自靜默與語言之間的緊張關系,來自于靜默的無言的所指及語言留下的空白處。關于人鄰詩歌的靜默意味,也許借助帕斯的一首詩歌更能形象地給予概括:
詩人用清晰的文字抒寫/他晦澀的真
話/他的話語/不是公共紀念碑/也不是
指路的向導/ 它們誕生于沉默在無言的枝
芽上開放/我們默默地欣賞它們
——《路易斯·塞爾努達》[2]
然而,詩人為什么會選擇靜默這樣一種言說方式呢?因為靜默是智者的生活方法和態度。王羲之有兩句詩云:“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靜照”(comtemplation)是一切藝術即審美生活的起點。晉人的文學藝術都浸潤著這新鮮活潑的“靜照在忘求”和“適我吾非新”的哲學精神。大詩人陶淵明的“日暮無天云,春風扇微和”,“即事多所欣”,“良辰入奇懷”,寫出這豐厚的心靈“觸著每一妙光陰都成了黃金”; 回首莊子的人生哲學,就充滿了如此的“無言”智慧。他認為“大美而不言”,(《莊子·知北游》),“得意而忘言”。(《莊子·外物》)最高境界的精神存在或最高境界的美,也不能憑借語言這個有限的心靈工具來傳達,語言也不能盡善盡美地表達深刻復雜的精神意義:“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莊子·知北游》)“道”作為精神的最高虛無,最高的美,當然不可能以語言或其他的方式來表達或描述,甚至也不能憑借感覺去把握。推到詩歌領域,許多現象和思想當然無法用語言傳達。六祖慧能的“摩訶般若波羅蜜”所謂“大智慧到彼岸”(《壇經》),也采取無言的靜默方式應對提問。所以,為了使自己避免陷入精神的沼澤而難以自拔,為了使自我不去扮演無聊的語言喧嘩者的角色,為了求得心靈的安寧,最智慧的方式便是保持靜默。
然而,如何使靜默在詩歌中成為可能?
首先,通過虛己來讓靜默出場。虛己就是自我的虛位。詩人借著自我的虛位,來讓素樸的天際活潑興現。讓我們讀一首詩歌來感受一下:
雨,停歇下來。暗黑的對面/偶爾的犬
吠,孤獨的燈燭/ 人的呢喃的親切話語/ 聲
音奇怪,傳得好遠。//毛絨絨的松林間/月
色照著的矮矮的人字屋頂/滿是松脂和野
花香氣/一大塊一大塊的巖石濕得厲害。
——《對面山岡》
這首詩,景物自然興發與演出,詩人不以主觀的情緒或知性的邏輯介入去擾亂眼前景物內在生命的生長與變化的姿態,景物直觀讀者面前。詩人通過使用靜默這無言的語言,把現象中的景物從其表面上看似凌亂互不相關中解放出來,使雨、偶爾的犬吠、孤獨的燈燭、人的呢喃、毛絨絨的松林、月色、人字屋頂、香氣、濕的巖石這些意象以它們原始的新鮮感和物性原原本本地呈現出來。詩歌的韻味在語言的靜默中,在語言所營造的靜默氛圍里。
其次,和情感保持一定距離。“懷疑論美學認為,藝術不是單純的情感活動和情感表現,情感只能構成藝術文本的有限方面。另外,藝術還具有懸隔情感和否定情感的美學特征,或者說,藝術只有保持和情感的合適距離,才可能達到自我的絕對自由和智慧與想象力的充盈。”[3]關于這一理論觀點,艾略特曾有過非常精辟的論述,他說:“詩不是放縱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現個性,而是逃避個性。自然,只有有個性和感情的人才會知道要逃避這種東西是什么意思。”他解釋說:“因為詩之所以有價值,并不在感情的‘偉大與強烈,不是由于這些成分,而在藝術作用的強烈,也可以說是結合時所加壓力的強烈。”[4]以上的論述告訴我們,藝術創作需要節制情感,情感并不能成為創作的直接力量,它的狹隘性、短暫性或是紀實性、欲望等特征都使它具有歷時性特點,因而,真正的詩人就必須學會和情感保持一定距離。人鄰的詩歌給人以冷靜和克制的印象,他詩歌的情感經過了大量的過濾,是典型的在寧靜中對激情的回憶,他以追求更為寧靜的思考的力量來取代詩歌的激情。并且更為可貴的是,人鄰將這種寧靜的思考形象化為靜默的意象,如他那《暮野》《農具》《落葉》《石峽》最確切完美地表現了對情感的節制和對靜默的抒寫。
最后,通過審美直觀。什么是審美直觀?審美直觀就是詩化的思。對于人鄰來說,審美直觀具有溝通自我觀照與意象的作用。審美直觀把靜默意象化了,把意象轉化為直接的靜默,保證了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對現象界最有力最直接的征服。請看《彈琵琶的女子》:
那個女人幽暗、絲綢的臉,/指尖,風
與流水/ 平白就帶給了我/ 一陣悲戚,/
一場風雪,一根蒼茫的憂傷落羽。
這就是由審美直觀得來的詩句。詩歌寫的就是一張女人的臉在詩人心中引起的感覺。這個女子,有著一張幽暗、絲綢的臉,為什么是幽暗、絲綢的?這就是詩人的審美直觀所捕獲的美。這種美感是不為現實所左右的,它直接越過邏輯分析,它甚至是超時空的,這一美感給了詩人詩意。在人鄰的詩歌中,我們會讀到這樣的詩句:“舞者,暗淡的紫色綢衣/似乎就是為了那/為了那一點點美/而疲憊//稍稍差著半拍的步子/半點鐘以后,倦怠/是灰和灰白,是深色的/不同的抑郁和哀傷/是稍稍差著一點的/為了戀愛的凄涼/而同樣淡紫、淡紫的美呀!”(《舞者》)“清秋清晨,泥土悄悄挪動。/陰冷的河灘上一只土色蟾蜍的緩緩挪動/有著難以描述的/大地挪動時,泥土色膝蓋一樣的/孤獨。”(《蟾蜍》)這些詩歌都是詩人在審美直觀中獲得的,他是人鄰作為感性個體同時作為一個詩人認識世界的真正方式,也是詩人把握世界意義的認識方式。
那么,人鄰靜默的詩取得了什么樣的藝術效果呢?主要有這樣兩點:
一、氣韻生動之美。何為“氣韻”?五代的荊浩解釋“氣韻”二字:“氣者,心隨筆運,取象不惑。韻者,隱跡立形,備遺不俗。”(《筆法記》)這里是說,藝術家要把握對象的精神實質,取出對象的要點,同時在創造形象時又要隱去自己的筆跡,不使欣賞者看出自己的技巧。這樣把自我熔化在對象里,突出對象的有代表性的方面,就成功為典型的形象了。這樣的形象就能讓欣賞者有豐富的想象的余地。所以黃庭堅評李龍眠的畫時說:“‘韻者即有余不盡。” 人鄰的詩歌充滿了“韻”味,他的詩歌就是一幅幅中國水墨畫。讓我們來一起欣賞這首詩:
感覺狼在一片風景里/誰的手能系住/
這冷色。/別一種浪骸。/別一種艱難的輝
耀。/一種浪骸。/一種艱難的輝耀。/一
種暗夜盛開的頑鐵。一種悄然的孤獨/背
向月光……
——《感覺狼在一片風景里》
人鄰的詩如中國畫善于用虛筆,抓住事物的最傳神處進行濃墨重彩,于最不似處,最荒率處,最為得神。似真似夢的境界涵渾在一無形無跡、而又無往不在的虛無中,使詩歌具有氣韻生動之美。
二、本色之美。中國人欣賞兩種美,一種是華麗繁富的美,一種是本色的美。但這兩種美是有高下之別甚至是對立的。鮑照曾比較謝靈運的詩和顏延之的詩,謂謝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顏詩則是“鋪錦列繡,雕繢滿眼”。《詩品》:“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采鏤金。顏終身病之。”(見鐘嶸《詩品》《南史·顏延之傳》)這可以代表了中國美學史上兩種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而上述兩種美感,兩種美的理想,在中國歷史上一直貫穿下來。六朝的鏡銘說:“鸞鏡嘵勻妝,慢把花鈿飾,真如綠色中,一朵芙蓉出。”(《金石索》)在鏡子的兩面就表現了兩種不同的美。后來宋詞人李德潤也有這樣的句子:“強整嬌姿臨寶鏡,小池一朵芙蓉。”被周頤評為“佳句”(《惠風詞話》)。鐘嶸很明顯贊美“初發芙蓉”的美。……李太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真。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清真”也就是清水出芙蓉的境界。杜甫也有“直取性情真”的詩句。無論是“初發芙蓉”的美,還是“清真”的美,還是“情真”的美,其實就是本色之美。人鄰的詩追求的是無言之言,在靜默中讓事物自現,他去掉了詩歌多余的成分,“虛室生白”,因此,他的詩歌是一派自然,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我們幸運地在當代詩歌中再次看到這樣一種不加修飾之美、本色之美。
人鄰對和諧與中間色調的色彩有著微妙的感覺,他喜歡寫從容的美、閑適的人,喜歡寫不動聲色的力量,喜歡寫靜默中的人、物。如雪中的山坡、樹木,夏日黑夜的玫瑰花叢,清晨無人的街道,秋后陽光下的莊稼,老屋子、故宅、紅椅子、僧人、禪院等這樣靜默的場景,從中發現一種別趣,在無聲的氣韻中悄然寄托一種人生理想,或是營造一股懷舊的氣氛,或者是抒寫一種淡淡的哀愁,也許是一種深深的孤獨、寂寞,但無論怎樣,詩人總能讓自己的詩歌自成一小宇宙,具有自己獨特的境界。正如鄭敏先生所說的:“境界是一種無形、無聲充滿了變的活力的精神狀態和心態。它并不‘在場于每首詩中,而是時時存在于詩人的心靈中,因此只是隱現于作品中。”[5]我們很榮幸地在當代詩人人鄰詩歌中發現這樣一種詩歌境界,而這對于我們的當代詩歌來說無疑是非常寶貴的。
注:該文受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文學青年項目“中國當代西部詩潮研究”資助(批準號: 07czw033)
【參考文獻】
[1]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王軍.詩與思的激情對話——論奧克塔維奧·帕斯的詩歌藝術[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3]顏翔林.懷疑論美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A].黃晉凱,張秉真,楊恒達.象征主義·意象派[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5]鄭敏.詩歌與哲學是近鄰——結構——解構詩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作者簡介:張玉玲,江蘇技術師范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