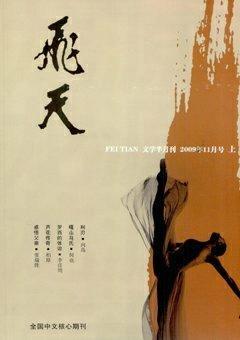孔子《詩》教成因探源
目前,學術界多關注孔子的《詩》教思想,但對孔子《詩》教思想形成的原因還未曾作過深層次的探源。本文從春秋時代稱《詩》風氣和孔子在當時學術文化界所處的地位入手,分析孔子《詩》教的形成原因及其特點。
一、孔子生活時代的稱《詩》之風尚
春秋時代,各種儀式場合程規化的歌詩奏樂,仍然是瞽矇樂工的職責,同時也是《詩》的傳播方式。除了《周禮》《儀禮》《禮記》等先秦禮書記載中固定的儀式歌奏之外,一些新型的用《詩》方式開始頻繁地出現于《國語》《左傳》當中,這就是聘問燕享中的樂工歌誦、行人賦《詩》以及言語引《詩》。朝聘、會盟、燕享賦詩是春秋邦交活動的重要內容和特色。《漢書·藝文志》說:“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諸侯會盟之時,通過賦詩表明己志,這種“微言相感”的言談方式為各國諸侯所認同。
據馬銀琴統計,《國語》《左傳》所載屬于聘問歌詠的賦詩言志共31起,涉及詩歌71篇次,其中《國風》28篇次,《小雅》33篇次,《大雅》6篇次,《周頌》1篇次,逸詩2篇次。賦《詩》之風從魯僖公時代逐漸興起,至襄、昭之際達到頂峰,到魯定公時代走向沉寂。另外,在引《詩》方面,進入春秋以后,《詩》作為最具有代表性的先王典籍,經典性權威性更高,《國語》《左傳》之中有相當一部分言辭都是以《詩》作為立論的依據。據馬承源統計,《左傳》中以“君子”等名義引用《詩》者有35例。然而無論是在政治、外交場合賦《詩》言志,還是在勸諫、游說、評論和著述過程中征引《詩》中語句作為言辭的論據,春秋時代的賦《詩》、引《詩》總體上的特點就是斷章取義,強調《詩》的政治功用。“斷章取義”是指賦《詩》言志之時根據需要只采用一首詩的一章,并不重視整個文本之意。
孔子是春秋末年魯國人,一生大致經歷了魯襄公、昭公、定公和哀公時期。孔子生活時代的襄、昭之時,正是賦《詩》、引《詩》之風的鼎盛時期。《詩》在當時主要是用于典禮、諷諫、賦詩言志和言語等方面。典禮和諷諫是《詩》固有的作用,言語和賦詩言志是后來發展出來的。春秋時期,典禮的種類很多。對神的祭祀和人們宴會時,往往以《詩》來幫助禮節的進行,增加怨傷或歡樂的程度和氣氛。諷諫的詩是作了獻給統治者,用以陳述自己的意見。
二、孔子以周代禮樂文化的傳承者自居的文化心態
從文化傳承的方面來講,孔子不僅是締造儒家學派的宗師,同時,他也是周代文化的直接繼承者與傳播者。《淮南子·要略》云:“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這不僅是《淮南子》一家之說,比《淮南子》更早的莊子,在《天下》篇綜述古之道術與百家之學時,沒有單獨列出孔子一派,也相當明顯地表明了他把孔子當成“古之道術”的直接繼承人來看待。除了來自諸子學說的證據之外,孔子自己對此也有著十分明確的敘述。《論語·子罕》云:“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不僅以周文王的直接繼承者自居,而且自認為是周代文化的唯一繼承人。既然如此,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末年,當執政者失去了恢復周道、重修禮樂的意識與能力時,以天下為己任的孔子,必然主動地承擔起恢復和弘揚周人禮樂文化的歷史責任,知其不可為仍勉力為之。在其周游列國,干七十余君而莫之能用的情況下,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通過教授弟子來傳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也就成為孔子的唯一選擇。
結合孔子《詩》教思想形成的以上原因,筆者認為孔子《詩》教思想有以下兩方面的特點:
第一,在教育理念上,孔子對其弟子進行文化教育活動的過程中,極其重視《詩》的傳授,用《詩》作為重要的教科書來教育弟子,以《詩》為教。孔子對《詩經》有許多論述,《論語》較為集中。如: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論語·季氏》)
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論語·陽貨》)
孔子重視語言教育,教育自己的兒子孔鯉要重視《詩》的學習。因為學《詩》可以得到精練語言的本領,知道很多語言表現手法,為政治生活和外交出使發言做好準備。春秋時各諸侯國統治者以及貴族之間朝聘會盟,在儀式上、在宴會上,各依所需,斷章取義,引《詩》述懷,賦《詩》喻意,用詩來做交際的工具,表達各自的意向,已成慣例。各國國君在討論國內事務時,也常常征引《詩》句來申述己見。如《左傳·襄公十九年》記載: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蔽邑?”賦《六月》。
對于范氏所賦《黍苗》,季武子的反應是起身座中,“再拜稽首”,對范宣子許諾幫助魯國表示感謝,并賦《六月》以晉侯比尹吉甫。這一賦一答,在溫文爾雅的氣氛中進行,都是符合禮的。而當時的士大夫如果不能賦詩,就要被人瞧不起。如《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載: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華定因為不能以《詩》答賦,當場出丑,并受到昭子的一番奚落。宋人邢昺《論語注疏》說:“以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之,何以為言也?”可見孔子以《詩》為教的觀念顯然是受到了當時稱《詩》之風的影響。
第二,在學《詩》目的上,孔子繼承了前人稱《詩》時取其政治功用的觀點。但繼承的同時更有所發展,即更加重視《詩》在倫理教化、性情修養和增長見識方面的作用。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
孔子既為現實政治培養人才,受政治外交場合賦《詩》言志風氣的影響,他就不得不教其弟子學《詩》。由此可見孔子強調學《詩》的主要目的,實質上是為了從政。孔子指出學了《詩》要能隨機應變地運用,如果單是死記硬背,而不能據以處理國政,又不能獨立地運用去辦外交,即使背得再多,那又有什么用呢?孔門弟子中最善于外交活動的子貢,就是學《詩》能用的代表人物,因此曾受到孔子的稱贊。
孔子認為讀《詩》不僅可以鼓舞情緒,可以觀察風俗民情的盛衰,可以建立相互間的諒解,可以諷諭或批評時政的得失;甚至還可以運用其中的道理來侍奉父母,以至從政事君,認識自然界的鳥獸草木。用《詩經》來培養學生從政、外交的應對才能,這顯然是受到了春秋稱《詩》之風這一在當時普遍盛行的文化現象的影響。孔子用《詩經》進行教學是多方面的,如以《詩》作為文化知識的教材、音樂學習的課本、悟道的材料等等,這些就充分體現了這一文化巨人的創新之所在。
綜上所述,可以說孔子的《詩》教并非空穴來風。春秋時代稱《詩》之風是孔子《詩》教形成的外因。而孔子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末年以周代禮樂文化的傳承者自居的文化心態,則是其《詩》教形成的根源。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2]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四卷本)[M].北京:中華書局,1981.
[3]匡亞明.孔子評傳[M].濟南:齊魯書社,1985.
[4]陳桐生.史記與詩經[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作者簡介: 黃文熙,河南科技學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