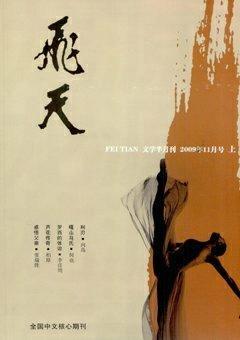“新文化”氛圍中儒家思想的確認
常 海
“新文化”運動體現的是在現代文化追尋中把傳統文化作為批判的對象,努力闡揚西方的現代文化。“新文化”運動中的“反傳統”只是要摒棄那些愚昧落后的封建文化的因素,并非全盤地否定傳統文化,但“新文化”的建構者更加彰顯西方的現代文化,宣傳西方的現代精神。而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我們通過豐子愷的散文創作讀到的卻是他不斷地對儒家傳統思想的確認,這包括他對家園的不斷書寫、都市興起背后對家園失落的反思,也飽含著他對中國傳統儒家藝術觀念的認同。
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而儒學的根基,是對“生”的重視。儒家向來是看重生的,先秦儒學及其衍生物魏晉玄學、宋明禮學,均以肯定現實生命的存在為前提,重視人在此岸的生存際遇,命運波折。從《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生生而有條理”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等,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先哲所觀照的宇宙不是一個物質的機械系統,而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真實的生命系統。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曾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心目中代表儒家道理的是‘生。”考察豐子愷當時的生存背景,中國正飽受列強欺凌,尤其是日本侵略者發動侵華戰爭之后,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迫切需要激發和凝聚整個民族的生命力量。特別是當“八·一三”事件后,豐子愷親歷了戰爭的殘酷,飽嘗了亂世的酸辛,因而在其散文創作中體現出“仁者”的情懷,渴望用自己的文字為民眾吶喊,為民族國家的強盛泣血書寫。在此,我們看到豐子愷的“國家”觀念依然是中國傳統的“國家”理念,而并非西方意義上的“大眾在正義的法律之下的聯合體”。豐子愷把“國家”理解為家庭、家族、家園到國家的統一體,因而豐子愷以“家庭”“家園”的書寫入手,并以此為主體,進而進入對現實社會的體悟,其實我們應該把這些都視作是對國家的書寫。
初涉文壇的豐子愷多以家庭瑣事、兒女情懷為描寫的主要內容,但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豐子愷的筆鋒一轉,深入到現實里面,作品充實而厚重,表現了積極的現實主義精神。三十年代的散文創作是豐子愷的豐收期,他先后出版了《子愷小品集》《隨筆二十篇》《車廂社會》《緣緣堂再筆》等散文集子。豐子愷曾經這樣來剖析自己:“一個是出世的,超脫物外,對人間持靜觀態度的;另一個是入世的,積極的,有強烈愛憎感情的。這兩者始終在我心中對峙著,而后者的優勢越來越強,終于壓倒了前者……”這積極入世的一面是他儒家文化精神的體現,也是促使他在30年代后把散文創作的筆墨更多地投放到人生社會的根本所在。這一時期他散文的代表作有《肉腿》《榮辱》《兩場鬧》《楊柳》《山中避雨》等,堪稱反映現實的佳作,其中《肉腿》反映在大旱時節,運河岸邊廣大農民無論男女老幼拼命蓄水抗早的情景,作者將踏水車農民的肉腿與舞池、銀幕上舞女們的肉腿作對照,慨嘆人生的艱辛與社會的不公,反映了自己的愛憎取舍。《兩場鬧》以流氓地痞與下層貧苦百姓的對比,揭示了人世間的不平。豐子愷還歌頌了貧民百姓的勇敢和智慧,訕笑了有閑階級的虛弱與無能,這表現在《半篇莫干山游記》《手指》中。《榮辱》則以漫畫的筆調,寫自己開始被誤認為官長而倍受尊敬,后來又被認出不是官長則又受到辱罵,從而諷刺了那種見官僚肅然起敬、遇百姓怒形于色的大小官吏及爪牙,表達了作者對丑惡世態的憎惡之情。他在1935年出版的漫畫集《人間相》序言里說:“吾畫即非裝飾,又非贊美,更不可娛樂,而皆人間不調和相,不喜相,與不可愛相,獨何與?東坡云:惡歲詩人無好語。若詩畫通似,則竊比吾畫于詩可也。”他在《談中國畫》一文里發出這樣的疑問:“為什么現代的中國畫專寫古代社會的現象,而不寫現代社會的現象呢?”為此他大聲疾呼:“不要一味在深山中贊美自然,也不妨到紅塵間來高歌人生的悲歡,使藝術與人生的關系愈加密切,豈不更好!”豐子愷在抗日戰爭中流亡了八年,攜家眷十余口,顛沛流離歷盡艱辛,但在這流亡之中他創作了大量散文。司馬長風在《“藝術的逃難”》一文中說:“在《巴金的散文》中,我嘗嘆息,反映抗戰生活的散文太少,《豐子愷文集》及《教師日記》則使我意外驚喜。巴金的《旅途雜記》寫烽火離亂間的行旅苦識,雖已相當生動入微,但是與豐子愷的《辭緣緣堂》和《藝術的逃難》相比,有如路旁小花與滿園盛開的花卉。”豐子愷抗戰期間散文創作,如《還我緣緣堂》《告緣緣堂在天之靈》《辭緣緣堂》《中國就像棵大樹》等,具有明顯的戰斗性和強烈的愛國熱情,這與他憂國傷時的儒家情懷是密不可分的。他在《還我緣緣堂》一文中,表明了自己威武不能屈的儒者本性:“我雖老弱,但只要不轉乎溝壑,還可憑五寸不爛之筆來對抗暴敵。我的前途尚有希望,我決不為房屋被焚而傷心,不但如此,房屋被焚,在我反覺輕快,此猶破釜沉舟,斷絕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進。”可見,豐子愷并非主張退守到“深山中贊美自然”,而是渴望“到紅塵間高歌人生的悲歡”,并且在緣緣堂被毀后更加表現出對民族國家強盛的渴慕。
中國的傳統文化其實都是以鄉村為背景的,因而非常注重鄉土人情。豐子愷的散文中體現出他對現代都市文明的反思,同時也表達了他對鄉土文化的認同,這在他的鄉土題材和都市題材散文作品的兩端不同的價值判定以及表述態度中就可以窺見其端倪。如在《故鄉》一文中他這樣寫道:“到了現今的工商時代,人都離去了破產的鄉村而到大都會里去找生活,就無暇紀念他們的故鄉。他們的子孫生在這個大都會里,長大后又轉到別個大都會里去找生活,就在別個大都會里住家。在他們就只有生活的地方,而無所謂故鄉。‘到處為家,在古代是少數的游方僧、俠客之類的事,在現代卻變成了都會里的職工的行為,……現在都會里的人舉頭望見明月,低頭所思的或恐是亭子間里的小家庭。而青春作伴,現代人看來最好是離鄉到都會去。至于因懷鄉而垂淚,沾襟,雙袖不干,或是春夢夜夜歸鄉,更是現代的都會之客所夢想不到的事了。……然而大家離鄉背井,擁擠到都會里去,又豈是合理的生活?” “鄉村”是與現代“都市”相對立的一個兼有文化、地域意味的空間概念,“離鄉”的意義不但表現為鄉村凋敝與城市發展的過程,而且也還牽涉到“鄉村”與“都市”之間生存環境與文化環境的改變。毫無疑問,這樣的文化批評帶有現代性批判的文化意義。豐子愷以城鄉間的生活對比為基礎,超越了現代進化論視野下的城鄉觀念,進而看出現代都市生活中諸多的丑惡,包括人性的隔膜、物欲的膨脹、詩意人生的消退。鄉村世間里的鄰里關系是和諧而充滿親情的,而在都市之中這種鄰里的關系被隔斷了,他在《山水間的生活》中這樣來對比城鄉之間的差別:“我曾經住過上海,覺得上海住家,鄰人都是不相往來,而且敵視的。我也曾經做過上海的學校教師,覺得上海的繁華和文明,能使聰明的明白人得到暗示和覺悟,而使悟力薄弱的人受到很惡的影響。我覺得上海雖熱鬧,實在寂寞,山中雖冷靜,實在熱鬧,不覺得寂寞。就是上海是騷擾的寂寞,山中是清靜的熱鬧。”在《樓板》中對城市中人與人之間的異化關系批評得更直接:“這‘出入同門的幾戶人家,除了經濟上的往來,其余竟至于很少講話:偶然在門間或窗際看見鄰家的人的時候,我總想招呼他們,同他們結鄰人之誼。然而他們的臉上有一種不可侵犯的顏色,和一種拒人的力,常常把我推卻在千里之外。盡我們租住這房子的六個月之間,與隔一重樓板的二房東家及隔一所客堂的對門的人家朝夕相見,聲音相聞,而終于不相往來,不相交語,偶然在里門口或天井里交臂,大家故意側目而過,反似結了仇怨。”在《鄰人》中這種表達近似憤怒:“這(引者注:指鐵扇骨)是人類社會的丑惡的最具體,最明確,最龐大的表象。人類社會的設備中,像法律,刑罰等,都是為了防范人的罪惡而設的,但那種都不顯露形跡。……只有那把鐵扇骨,又具體,又明顯,又龐大地表示著它的用意,赤裸裸地宣示著人類的丑惡與羞恥。……假如造物主降臨世間,一一地檢點人類的建設,看到鎖和那鐵扇骨而查問它們的用途與來歷時,人類的回答將何以為顏?”豐子愷本人是喜歡甚至迷戀那種人間情味的,他在《告緣緣堂在天之靈》中描述在桐鄉石門故居的生活:我的親戚老友常到我家閑談平生,清茶之外,佐以小酌,直至上燈不散。油燈的暗暗和平的光度與你(引者注:指緣緣堂)的建筑的親和力,籠罩了座中人的感情,使他們十分安心,談話娓娓不倦。豐子愷的散文中表達著自己對儒家文化中世俗人情溫馨體驗的堅守。
豐子愷的藝術創作體現了儒家的藝術追求,特別是30年代以后的創作,他執著地實踐著“為人生”的藝術觀念,追求美善的統一,完成著他對于現代社會的構建模式的追求,渴望用美善的傳統文化實現在中國由古典態向現代社會轉型中的承續。在《藝術必能建國》這篇文章中,豐子愷談到了道德與藝術的關系:“道德與藝術異途同歸,所差異者,道德由于意志,藝術由于感情。故立意做合乎天理的事,便是道德;情愿做合乎天理的事,便是藝術。藝術給人一種美的精神,這精神支配人的全部生活,故直說一句,藝術就是道德,感情的道德。”這其實是對美善統一的儒家藝術精神的一次闡釋,亦可視為是他對現代性中的理性因素的反駁,對感性的重視和宣揚,也是對人性的堅守。他的學生胡治均曾回憶說,豐老在1947年對他說:“我們崇拜弘一法師的人格,但不學他做和尚,要在世俗社會中做點有益事。”豐子愷是一個醉心藝術、摯愛家庭、立足現世、憂國傷時的藝術家。在儒家思想引導下,他心系家國,努力竭盡自己的綿薄之力,只是在人生之旅的疲憊時刻,在心力交瘁的緊要關口,他才借助佛教的力量暫時地躲避一下。1979年發表在香港文匯報上的一篇紀念文章這樣描述他:“他的一生,畫得最多的是兒童和女子,點綴得最多的是楊柳與紫燕,他幾十年來心向手追人世間的春天,他終是一個入世的人。”豐子愷雖然讓自己避居在其的藝術小筑中,但依然可以看出他對國家步入現代過程中自己的思索,那就是在現代社會中的儒家思想觀念的不斷確認。
【參考文獻】
[1]梁漱溟.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M].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122.
[2]陳嘉明.現代性與后現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1.
[3]豐子愷.《人間相》序[M].豐陳寶,豐一吟.豐子愷文集(藝術卷三)[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6).115.
[4]豐子愷.談中國畫[M].張品興[M].豐子愷散文.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05,(1).185.
[5]豐子愷.還我緣緣堂[M].豐陳寶,豐一吟.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6).52.
[6]豐子愷.故鄉[M].豐子愷文集(第5卷)[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2.333-334.
[7]豐子愷.鄰人[M].豐子愷文集(第5卷)[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2.242-244.
[8]豐子愷.告緣緣堂在天之靈[M].豐子愷文集(第5卷)[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2.56-63.
(作者簡介:常海,沈陽大學新民師范學院副院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