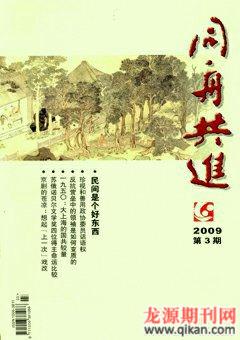臺灣民間社會的“點、線、塊”
鄢烈山

早就聽龍應臺教授說過:臺灣最珍貴的部分,其實是它的民間力量而非政府。2008年11月我有機會“臺灣一周行”,雖只短短幾天,觀察所得只能是浮光掠影,但對于龍教授的話已有深切體會。
“點”——志工
最令人難忘的是島內幾乎無所不在的“志工”(即我們所說的“義工”、“志愿者”)。我猜測除了企業,舉凡慈善機構、事業單位、非營利組織、公益活動和公權機關,“志工”是無所不在的——之所以說“猜測”,是因為我沒有到過工廠,不知道那里有沒有退休人員在做義務勞動。
在花蓮的第二天,我們參觀了“慈濟精舍”(它的主人就是陳云林訪臺期間拜會過的“證嚴上人”——佛教“慈濟宗”的宗師兼住持,創辦多所慈濟學校、慈濟醫院的慈善家)。“精舍”里最令人注目的是“志工”。我拍的照片中,有志工在為廚房揀菜。同行的臺灣朋友說,這些志工可能是身家億萬的實業家,在自己的財團里一呼百應,但在這里就是普通勞動者、工作人員,服從分配,做最平凡的事務。這些“成功人士”毫無倨傲之態,懷抱感恩之心回報社會,其精神境界相當難得。
參觀宜蘭縣政府大樓那天是星期天,工作人員不上班,在一層大廳只看到“志工”的職責說明(給來訪縣民指路、叫出租車、指導復印資料等)。他們是政府與民眾的橋梁。
“龍應臺文化基金會”的執行長李應平女士說,她們的基金會只有4個受薪人員,活動主要靠100名志工。這些志工都是從網上報名者中挑出來的,50%是在校大學生,30%是上班的年輕人,利用休息或輪班的時間前來服務,還有20%是家庭主婦和退休者。志工的構成有所不同,但他們的志愿和無償奉獻社會的熱情是一樣的。
仔細想來,“志工”為什么這么令我感動呢?首先,他們給人的直觀感受是人與人之間的友善、溫暖、信任,而不是冷漠、猜疑乃至敵視和防范。這樣的社會氛圍,只能靠志愿者這樣的民間力量才能形成;靠警察和政府力量維持秩序也許很“安全”,卻不會有如沐春風的親和力。再深入思考,普通的、普遍存在的志工,并非出于宗教熱情和犧牲精神,他們的情懷難道不是基于對社會信賴、對家園熱愛的公民精神嗎?這種建設美好家園的責任感、泛愛眾的奉獻精神,正是社會最寶貴的力量。
本不想把這些感受寫作成文,不過從臺灣回來后,旋即奔成都參加媒體論壇,隨隊履及地震災區綿陽及受害最嚴重的北川原縣城,然后又去都江堰市。這一圈奔波下來,我對災區志愿者的“銷聲匿跡”感觸頗深。在綿陽一間堆放救災物資的倉庫,我們看到了大堆因缺少人手來不及發放的即將過期食物、飲料以及冬天可御寒的衣被……人們的愛心是毋庸置疑的,危難之時多少人都愿意做義工,然而,若不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們為什么都不出現了?
據報道,鐘南山院士最近加盟“志愿者之家”。廣東志愿者聯合會首次召開的代表大會,聘請港星成龍任特邀榮譽會長。我多么希望大陸的志愿者也能做到隨時隨處可見,同時但愿“不要與陌生人接觸”之類的提示因無必要而趨于消失。
“線”——基金會
言歸正傳,再說臺灣的民間力量。如果說作為個人的志工是民間社會網絡上的“點”,各種基金會、非營利的非政府組織(NGO),則是這個網絡上的“線”,或經或緯。
臺灣的基金會很多,它們是獨立的,雖然是勸募集資而非營利,也號稱“財團法人”,比如“龍應臺文化基金會”的全稱前面就有“財團法人”四個字。我們在臺北著名的溫泉區北投住過兩晚,翻閱了“北投文化基金會”與“北投社區大學”辦的雜志《北投文化》,看得出這個基金會主要是為社區服務的。雜志不僅介紹北投地區的大街小巷、生活場景,介紹社會文化創意、品牌設計,還有專講北投的“永續(即大陸所說的‘可持續發展)農業”等,內容相當廣泛,組織和參與的社會活動也相當豐富。
這些非政府組織對于社會血脈的暢通,對于營造社會和諧,顯然有著不可抹殺的作用。
社會的運行和治理,有三種主要的力量:一是廣義的政府即公權機關,它的責任和義務是提供秩序、公正、安全等公共產品;但因為它要用警察維護秩序,用法警保障司法公正,用稅警處罰不按章納稅者等,它必須倚靠強制力,而公權隨時有被濫用于壓制民權的可能。二是市場的力量、商業的力量、金錢的力量,這種力量主要由有組織的企業來體現,用利益來驅動、引誘、壓迫分散的消費者。這兩種力量對社會正面意義上的控制都可能“失靈”,即所謂“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因而它們有聯手對付公民個體的可能,即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而第三種力量,包括基金會在內的非政府組織是公民的自愿聯合,它們既不牟取商業利潤,也不具備行政強權,自然就成了社會中最健康的力量。

當然,我們也早已認識到非政府組織的存在對于社會的巨大意義,早有學者提出“小政府、大社會”的建設目標,可是做起來很難。這些年,轉型為公共服務型政府的任務越來越艱巨。這是因為民間力量的弱小難以發揮制衡和推動作用嗎?那么,誰來當政府轉型的“第一推動力”呢?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近年來,由于權力過于強勢,非政府組織對建設和諧社會發揮的作用甚微,官民沖突的群體事件日漸多起來了——這不是好趨勢。
“塊”——社會自治
如果說志工是社會網絡的“點”,NGO是“線”,那么,社區自治則是“塊”,一塊一塊構成了公民社會的“國土”。
“社區大學”在臺灣非常普遍,它們是社會自治、社區服務的重要內容之一。先說社會服務:陪同我們的臺妹、鳳凰網的宮小姐說,臺北最值得驕傲的是,每個街區都有一個社會服務中心,500米內、24小時、全天候,你所有的需求都可以在那里得到滿足,包括寄郵件和求診。臺北市市長郝龍斌也對我們講過類似的意思,可惜我們沒有機會去體驗。
在臺北參觀完“立法院”,一出來就在街邊看到了“中正社區大學”的招牌。幫我們做攝像的臺北攝影家翁先生說,他就在這個社區大學當過兩年教師。這樣的社區大學是社會自治的組織之一,主要為社區居民提供非學歷教育,也是居民參與社區生活的場所,對社會整合頗有作用。
在農村,我們參觀了宜蘭縣的“中山休閑農業區”。接待我們的人名片上有多重身份,他們是工人、店員,又是作坊主、店主、莊園主,還是理事、委員,大到縣、鄉農民組織、互助組織,細分到茶葉等專項協會,名目眾多,讓我這個在大陸農村長大的人眼花繚亂。正是靠著這么嚴密有效的鄉村自治組織,分散的農戶才能夠互助合作,共同面對變化莫測的市場。同行的翁先生是臺南人,他說,在臺灣說“我是農民”那是很自豪的,如果不意味著他是富人,至少不是窮人,絕不低城里人一等。這令我感慨不已。
因為是走馬觀花,我不可能看到臺灣民間力量的具體運作過程,說得出的只有這么多。但我確實感到了民間力量的廣泛存在和巨大能量。
回來不久,在《中國青年報》上看到了一整版的報道《深圳實驗:通往公民社會》。據介紹,建設“公民社會”已寫進了深圳市的政府工作報告,“公民社會,共同成長”已成為深圳人的共同旗幟。我衷心祝愿特區人重振雄風,官民一心,為中國的民間力量發展——也就是為中國的和諧社會建設闖出一條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