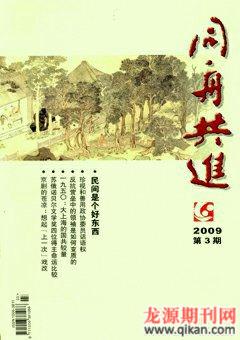蘇俄諾貝爾文學獎四位得主命運比較
陳為人

自諾貝爾文學獎頒發一個世紀以來,蘇俄前后共有四人獲此殊榮:1933年得主蒲寧,1958年得主帕斯捷爾納克,1965年得主肖洛霍夫,1970年得主索爾仁尼琴。(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羅茨基雖屬俄裔,但1977年已加入美國國籍,以美國作家身份獲獎,故不列入此文敘述之內)四人同為世界公認的大師,在蘇俄的遭遇卻有霄壤之別,對他們略作比較,對寫作者和讀者不無啟迪作用。
【蒲寧:漂泊至死者的“第二種忠誠”】
1933年,蒲寧成為第一個為俄羅斯文學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然而,由于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一直到蒲寧獲得諾貝爾獎,在蘇維埃的讀者中,許多人對蒲寧這一名字依然茫然無知。直到1965年蘇聯文學出版社才出版了《蒲寧文集》九卷集,蘇聯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新世界》雜志主編特瓦爾多夫斯基在序言中說:“……要么我們把蒲寧這個在政治思想上墮落到腐朽的君主主義立場上的反動家伙、白俄分子拒之門外,同時擯棄由他的才華創造的一切美的東西;要么提取其中一切成為我們民族文化、我們俄羅斯文學的財富的精華,拋棄他不再是一位藝術家以后所說所寫的一切陰暗、自私、反人道主義的糟粕。我們必須在兩者之間進行選擇,而選擇已經做出:我們理應把注意力集中在蒲寧的驚人的詩才上。”
蒲寧成為一個“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被“批判性接受”的作家。這一現象當然是主流話語幾十年來對蒲寧的排斥和遮蔽。
蒲寧可說是俄羅斯文學承前啟后的人物。一向不輕易贊人的契訶夫對蒲寧十分賞識。高爾基更是對蒲寧的才華給予極高的評價、極熱情的贊揚。高爾基在給蒲寧的信中,常常流露出一種含蓄的溫情和感人至深的欽佩態度,他甚至愿意把他在藝術界的泰斗位置謙讓給蒲寧。1916年高爾基在給蒲寧的信中寫道:“我愛您,請別見笑。我喜歡讀您寫的東西,想到您,談論您,在我這紛擾困頓的生涯中,您也許是,甚至肯定是最好的、最有意義的。對我來說,您是一位偉大的詩人,當代第一詩人。”
就是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作家,卻因為他的觀點和立場而遭到蘇維埃文學史的有意遮蔽。用偉人階級分析的觀點看:“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蒲寧1870年誕生于俄國一個破落的貴族世家,但蒲寧與那個時期的許多貴族文學家如托爾斯泰等一樣,出于那顆高尚的同情憐憫之心,在作品中描寫到農村莊稼人的時候,總是用真誠真實的筆調描繪那些一貧如洗、走投無路、饑腸轆轆、被有權有勢者欺壓的人群。
蒲寧文學命運的轉折點發生在1920年。十月革命中的一些暴力行為,使得貴族出身的蒲寧持一種拒斥和疑懼的態度。這樣,他與新政權的裂痕已無法彌合。1920年,紅軍部隊攻陷了敖德薩,蒲寧只得乘船逃離俄國,先是流亡巴爾干半島,后定居法國。從此,蒲寧成為無身份無國籍的“浮萍”。
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在授獎詞中這樣評價蒲寧:“他繼承了俄羅斯19世紀以來的光榮傳統并加以發揚光大;至于他那周密、逼真的寫實主義筆調,更是獨一無二……這些才能都是他突出而神秘的天才所致,而使他的文學作品給人留下精美的印象。”
蘇維埃對蒲寧的獲獎這樣定調:“1933年授予蒲寧諾貝爾獎,同樣無助于這位作家的名字在他的祖國傳揚,因為這種做法顯然是別有用心的,帶有政治色彩的。至于蒲寧作品的藝術價值,在此不過是個借口而已。”
于是,這樣一個為國爭得榮譽的作家,因意識形態的原因,在瑞典皇家音樂宮的授獎儀式上,卻經歷了尷尬的一幕:當年的蘇聯駐法大使拒絕出席授獎儀式,而在授獎的莊嚴會場,竟史無前例地沒有懸掛得獎人所屬國家的國旗。由于蒲寧“自絕于自己的祖國,自己的人民”,被取消了蘇聯國籍。
這樣一個“姥姥不親,舅舅不愛”、失去國籍失去身份、浪跡天涯有國難歸的流亡作家,令人想起日本電影《人性的證明》中那句撼人心魄的臺詞:“媽媽,你真的那么嫌棄自己的孩子嗎?”想起曾經呼喚革命“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的高爾基,在革命勝利后卻憤然出走國外,并在致羅曼?曼蘭的信中寫道:“……我不返回俄羅斯,我越來越覺得我是沒有祖國的人。”這位“無產階級偉大作家”的話,是否也說出了蒲寧的心聲?
蘇聯衛國戰爭勝利后,蒲寧也曾產生回歸祖國的念頭。然而,據西蒙諾夫的日記回憶:1945年,愛倫堡和西蒙諾夫訪問歐洲。在蘇聯大使館吃飯的時候,大家都站起來為斯大林干杯,蒲寧卻端坐不動。蒲寧對斯大林的專制獨裁始終持批判態度。后來很快發生了對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的批判,更使蒲寧斷了歸國念頭。這個叛逆者至死也沒能回到俄羅斯這片土地,只能孤獨凄慘地于1953年客死他鄉。
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心中都有一個偶像——恰達耶夫。恰達耶夫的名字中國讀者并不陌生,因了普希金那首《致恰達耶夫》的詩,一個叛逆者的形象走近我們。恰達耶夫的那本《哲學書簡》,被赫爾岑贊譽為劃破沙皇專制統治的“長夜槍聲”。普希金在《致恰達耶夫》一詩的結尾處寫下:“俄羅斯將從睡夢中蘇醒,在專制政權的廢墟上,將刻上我們的名字!”
恰達耶夫被沙皇宣布為“狂人”,戴上了一頂“不愛俄羅斯祖國”的帽子,遭到當局的慘毒迫害。10年之后的1846年,恰達耶夫在另一封“哲學書信”中為自己辯護道:“我是用另一種方式愛我的祖國……不管對于祖國的愛是如何的美好,但還有更為美好的,那就是對真理的愛,不是通過祖國,而是通過真理方能走上通天之路。”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第二種忠誠”。這是一代代知識分子心中的情結。
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思想》一書中,對知識分子有一個說法:“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始祖是拉季舍夫……當他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中說:‘看看我的周圍——我的靈魂由于人類的苦難而受傷時,俄羅斯的知識分子便誕生了。”拉季舍夫就是因為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中,揭露了沙皇統治的黑暗現實,抨擊俄國農奴制度而險些被殺頭,后來改判為流放,成為俄羅斯第一代流亡者。
知識分子就是不斷批判社會和進行自我批判的人,就是對不完美的現實挑鼻子挑眼睛的人,正如別林斯基所說,是盯在社會肌體上的牛虻。可以說,蒲寧不僅在藝術上繼承了俄羅斯傳統,在思想上也與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先驅們一脈相承。
【帕斯捷爾納克:“就像被圍獵的野獸”】
赫魯曉夫的兒子謝爾蓋在《赫魯曉夫下臺內幕及晚年生活》一書中,曾憶及赫魯曉夫對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的態度——兒子免不了帶一些“地下手抄本”給父親看。那時,有許多官方不讓出版的作品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莫斯科廣為流傳,當年作為蘇聯作協書記處書記、《新世界》主編的特瓦爾多夫斯基才向赫魯曉夫建議:“靠接吻是不能夠生孩子的。取消對文藝作品的書刊檢查吧!如果手抄本遍地都是,那是再糟糕不過的了!”
謝爾蓋的書中寫道:“有一次搞到一本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父親讀了很久:鉛字很小,字跡不清,紙又薄得幾乎跟卷煙紙一樣。有一次散步的時候,父親對我說,我們不該禁這本書的。當時我本該親自讀讀,書中沒有一點反蘇的東西。”
帕斯捷爾納克從1948年開始,用了8年的時間,終于完成了這一對蘇聯十月革命深沉思考的長篇巨作。帕斯捷爾納克的書寫成后,首先把手稿寄給《新世界》,這是蘇聯作家協會主辦的刊物,可見他當時并不認為這本書有什么問題。可是《新世界》編輯部把手稿退回,并附了一封由當年蘇聯作協領導西蒙諾夫、費定等人簽發的嚴厲譴責的信:“你的小說精神是仇恨社會主義……小說中表明作者一系列反動觀點,即對我國的看法,首先是對十月革命頭十年的看法,說明十月革命是個錯誤,支持十月革命的那部分知識分子參加革命是一場無可挽回的災難,而以后發生的一切都是罪惡。”這無異于當頭一棒,打得帕斯捷爾納克暈頭轉向。

1956年6月,帕斯捷爾納克把手稿交給意大利共產黨員費爾特里內利,希望在西方出版。但3個月后,帕斯捷爾納克又有些后怕——把書交給西方出版在當時被看作是“為敵人提供反蘇的炮彈”。在這一背景下,意共領導人和蘇聯駐意大利使館都向費爾特里內利施加壓力,試圖阻擾該書的出版,但費爾特里內利頂住壓力,請人以最快的速度譯成意大利文,當年11月就在米蘭出版了。此書一經問世,馬上引起轟動。兩年后,瑞典文學院宣布將1958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
西方的熱捧使蘇聯當局大為惱火。《真理報》發表了著名評論家薩拉夫斯基的文章《圍繞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囂》。文章指出:“反動的資產階級用諾貝爾獎金獎賞的不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誣蔑者和蘇聯人民的誹謗者帕斯捷爾納克。”蘇聯作家協會宣布開除帕斯捷爾納克的會籍。后來成為克格勃主席、當時是共青團第一書記的謝米恰特內表現得尤為極端。
據謝爾蓋回憶:謝米恰特內是反帕斯捷爾納克最積極的斗士。他在共青團成立41周年的大會上說:既然帕斯捷爾納克對蘇聯如此不滿,盡可以離開蘇聯到“資本主義樂園”去,并強烈要求政府褫奪帕斯捷爾納克的蘇聯公民權。此后就發生了學生集隊到帕斯捷爾納克的住宅鬧事,投擲石頭,砸爛門窗的事件。而國家安全部門對這些暴力行為持縱容態度,認為是帕斯捷爾納克“咎由自取”、“激起民憤”。
1958年的冬天,對帕斯捷爾納克來說,真是“風刀霜劍嚴相逼”。迫于國內的巨大壓力,帕斯捷爾納克12月29日宣布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現在回顧當年帕斯捷爾納克致瑞典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電文,真是耐人尋味而又意味深長:“鑒于我所從屬的社會對這種榮譽的用意所作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這份已經決定授予我的、不應得的獎金。希勿因我自愿拒絕而不快。”經過半年的心靈煎熬,帕斯捷爾納克寫下《諾貝爾文學獎》一詩:“我算完了,就像被圍獵的野獸。/自有光明與自由的所在,/可緊跟我的卻是追殺的喊叫,/我已經無法到外面去走一走。//漆黑的森林的池塘的陡岸,/還有被砍倒的樅樹的樹干。/通向四方的路已經被切斷。/一切都聽天由命,隨它的便。//我可到底做了些什么壞事,/我是殺人犯,還是無賴、潑皮?/我僅僅是迫使全世界的人/為我美好的家鄉俄羅斯哭泣。//但盡管已面臨死期,/我也相信有朝一日/善的精神定將壓倒/卑鄙和仇恨的邪力。”
哈維爾說:“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盡管帕斯捷爾納克違心做出妥協,但并沒能換回當政者的寬容寬恕。在一連串慘毒的打擊下,帕斯捷爾納克身心受到極度摧殘,心臟病不時發作,僅僅離獲諾貝爾獎不到一年半的時間,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爾納克在他的寓所溘然逝世。彌留之際,他說了這樣一句話:“認真地徹底死去。”這是何等凄愴絕望下發出的生命哀嘆!
帕斯捷爾納克說到過蘇維埃第一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死亡(我國的讀者對這一名字非常熟悉)。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富有才華的詩人,因為寫了許多歌頌十月革命和偉大領袖的詩歌而得到官方的推崇,成為“左派文藝”的代表人物和蘇聯文藝界的領導人,但他最終還是在內心的劇烈矛盾和痛苦中自殺了。馬雅可夫斯基死后,名聲急劇下降,斯大林只得親自出面維護。帕斯捷爾納克不屑地說:“推廣馬雅可夫斯基,就像葉卡捷琳娜女皇統治時代推廣土豆一樣,是強制的。這是他第二次死亡。”
大概正是基于對“生與死”的辯證法哲學考慮,帕斯捷爾納克在臨近生命終點時,與朋友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已經老了,也許很快就會死去,我再也不能放棄自由表達自己思想的機會了。”這大概可以看作他的“絕唱”。
官方當然不會舉行任何追悼儀式,報紙只發了一條簡短得不能再簡短的消息——“文學基金會會員帕斯捷爾納克逝世”,甚至連他是一位詩人、作家也不承認了。
【肖洛霍夫:“退出戰斗的妥協者”】
1965年,瑞典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決定把這一年度的文學獎授予肖洛霍夫。
與帕斯捷爾納克的獲獎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肖洛霍夫的這次獲獎,在蘇聯國內掀起了大規模的宣傳和熱捧。報上幾乎一個口徑地說:“這是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大事件。”并且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7年前因把諾貝爾獎授給帕斯捷爾納克時對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攻擊,改口說:“瑞典文學院終于以公正的態度對待一位偉大的蘇聯作家的作品……瑞典文學院的這一崇高決定,提高了它的威信……”
其實,肖洛霍夫的獲獎,與蘇聯當局的賣力推銷是分不開的。早在1954年,蘇聯促成肖洛霍夫獲諾貝爾獎的運作就已緊鑼密鼓地拉開帷幕。1956年,蘇共中央還作過一項決議:“關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候選人的決議,同意高等教育部有關推薦斯科別爾岑和肖洛霍夫的提議。”此后,蘇共中央不放過一切機會力推肖洛霍夫,直至他1965年獲獎,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肖洛霍夫是蘇俄文學史上極具爭議的作家。他是為東西方兩個對立世界所共同認可的文學家:他是唯一的既獲斯大林文學獎又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什么好事都讓他趕上了,肖洛霍夫真可謂“左右逢源”。
肖洛霍夫1905年出生于一個貧苦的哥薩克家庭。由于戰爭,他13歲被迫中斷學業,當了蘇聯紅軍的一名辦事員,參加過剿匪,這些經歷都為他以后的創作積累了素材。肖洛霍夫22歲即發表了后來獲諾貝爾獎的重要作品《靜靜的頓河》第一部。此書出版后,肖洛霍夫遭遇了與他的同伴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相似的命運,馬上遭到主流意識形態的批判。當年許多著名作家、評論家抨擊小說歪曲了國內戰爭,偏離了蘇聯的革命文藝路線。只是由于得到了高爾基的鼎力支持,小說才得以出版。到第四部出版時,蘇聯評論界再次產生激烈的爭論,有許多“上綱上線”的批判意見,甚至斯大林也指出小說有“非蘇維埃傾向”。
肖洛霍夫表現出“過人的聰明”,他以某種妥協,避免與當權者正面沖突。遭到斯大林責難的《靜靜的頓河》,最終幾經波折,能于1941年獲得斯大林文學金獎一等獎,從中也可見肖洛霍夫“柔道”、“太極拳”的推拿功夫。
蘇俄文史學者提出有“兩個肖洛霍夫”的觀點:一個是作品中所顯現的肖洛霍夫,一個是蘇聯文壇上的肖洛霍夫。一個是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擁護者、為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事業搖旗吶喊、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肖洛霍夫;一個是進入自己的文學世界、作為民眾疾苦的呼吁者、求真求善的尋道者的肖洛霍夫。
與作品中展現的形象,“給人的感覺是作者心靈深處對人性的崇高敬意”(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授獎辭)截然不同,肖洛霍夫在蘇聯文壇留下許多劣跡——
肖洛霍夫攻擊索爾仁尼琴說:“這是個瘋子,不是作家,是個反蘇的誹謗者。”當索爾仁尼琴的《第一圈》、《癌病房》在國外發表,肖洛霍夫公然指責索爾仁尼琴是“吃著蘇聯面包,為西方資產階級主子服務,并且通過秘密的途徑把作品送到西方的人”,是“蘇聯作家們要求除掉的典型疫病”。
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當政者要對兩位作家達尼埃爾和辛雅夫斯基(筆名阿爾夏克、杰爾茨)進行公開審判,理由是他們用筆名在國外發表了作品。這次公開審判激怒了許多作家,62名作家聯名發表抗議信。許多人要求旁聽,不能旁聽的就坐在法院門口抗議。而時任蘇共中央委員、蘇聯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的肖洛霍夫在蘇共二十三大上卻說:“這兩個黑心的壞小子要是落到難忘的二十年代就好了,那時并不按刑法典嚴格劃分的條款判決,而是遵從‘革命的法治意識判決,哎呀,這兩個變身有術的妖怪恐怕不會判得這么輕。”并且干脆要求“槍斃這兩個敗類”。這里真用得上中國曹植的一句詩:“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肖洛霍夫扮演了為虎作倀的角色。

84歲的著名老作家茹可夫斯基的女兒、詩人利季婭憤然寫信給肖洛霍夫說:“您的發言把您置身于俄國傳統之外。可惜我們不能懲罰您;不過您已經受到足夠的懲罰了,罰您多年來創作力枯竭。”
國外的媒體甚至向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提出:對于這種違背諾貝爾本意,喪失作家人格的獲獎者,能不能向他追回諾貝爾獎金。
斯大林去世時,肖洛霍夫還曾寫下這樣的文字:“我們突然間可怕地成了孤兒!黨、蘇聯人民、全世界的勞動者都成了孤兒……人類還沒有遭受過這樣無法估量的重大損失。我們失去了所有勞動人民的父親。”
但是,從斯大林時代血雨腥風中的過來人,對肖洛霍夫給予了一定的同情和理解。他們用了屠格涅夫長篇小說《羅亭》中主人公羅亭的一句話:“有多少次我從孩子般的沖擊變成弩馬般的麻木……有多少次我像雄鷹般展翅飛翔,搏擊長空,到頭來卻像一只碎了殼的蝸牛爬回原地!”
杜勃羅留波夫曾為俄羅斯作家筆下塑造的“多余人”形象定義為:“一群退出戰斗的妥協者”,并有這樣一段精彩論述:他們“否定了跟壓迫著他們的環境做殘酷斗爭的必要”,“走進了一座郁蒼茂密、人所不知的森林里”,他們攀援上樹原本是想尋找一條新路,但上樹之后,“不再去探索道路,只顧貪吃果子”。肖洛霍夫用自己的生命軌跡,為俄羅斯文學史勾勒出一個活生生的“多余人”形象。
對于肖洛霍夫的功過是非,自有歷史公論。換個角度看,似乎可以說,肖洛霍夫是一個生不逢時的作家。他“過人聰明”的生存策略、“過人才華”的寫作分寸既是他的成功,也是他的敗筆。
【索爾仁尼琴:永遠說“不”】
索爾仁尼琴出生于蘇聯北高加索。衛國戰爭期間應征入伍,兩次榮立戰功,被提升為大尉炮兵連長。1945年2月,就在戰爭即將結束之時,索爾仁尼琴在東普魯士前線被捕,原因是他在與老同學的通信中批評了斯大林。索爾仁尼琴對自己的寫作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他在勞改營期間就立下誓言:一定要將這里所發生的一切記載下來告訴人們。為了那些不能夠活著回到人世間的無數生命,他覺得自己是他們其中的一位代言者。
1962年11月,經赫魯曉夫親自批準,索爾仁尼琴的處女作《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得以出版。這部蘇聯文學中第一部描寫斯大林時代勞改營生活的作品,立即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然而正應了我國一句古語:“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隨著蘇聯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索爾仁尼琴遭到公開批判。就像當年火箭般地被吸收進蘇聯作家協會一樣,索爾仁尼琴又被閃電般地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兩次都沒有通過作家本人。索爾仁尼琴在被開除出蘇聯作協時,說了這樣一句話:“我不能用幾十萬幾百萬同胞的苦難和生命,僅僅為了換取一頂作家的頭銜。”
索爾仁尼琴還說了這樣一句話:“這一生我都感受到自己是從下跪的狀態漸漸直起腰來,我是由被迫緘默到逐步自由自在說話的。”索爾仁尼琴跪久了,要挺起腰桿,活動活動膝蓋骨,成為一個直立的人。
1970年,索爾仁尼琴“因為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授獎辭)而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索翁未能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且隨之而來的不是鮮花和掌聲,而是傳訊、逮捕、流放……
索爾仁尼琴在致蘇聯作家協會的公開信上說:“請你們擦拭一下刻度盤吧!你們的表落后于時代了。快撩開昂貴而沉重的帷幔吧,你們甚至還沒有發覺外面已經破曉。”更為有名的是這樣一句話:“一群瞎子為另一群瞎子擔當向導!”后來這句話成為經典名言,被許多媒體引用,成為刺向專制的匕首。
索爾仁尼琴還說“公開性,真誠和全面的公開性,這是任何社會健康的首要條件,我們的社會亦然。誰如果不希望我們的國家具有公開性,那么他們對于祖國就是漠不關心的,他們就是只關心自己的一己私利。如果有誰不希望祖國具有公開性,那他們就是不希望祖國治愈病癥,而是想要病入膏肓,無可救藥。”
蘇聯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蘇爾科夫這樣對比地評價索爾仁尼琴和帕斯捷爾納克:“對于我們來說,索爾仁尼琴的創作比帕斯捷爾納克更加可怕:帕斯捷爾納克是個脫離生活的人,而索爾仁尼琴的氣質具有動態性、戰斗性、思想性,這是一個有思想的人。”
1974年2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宣布剝奪索爾仁尼琴的蘇聯國籍,并把他驅逐出境。同年10月,美國參議院授予索爾仁尼琴“美國榮譽公民”稱號。
索爾仁尼琴到西方后,仍然保持了一個“批判者”的角色。索翁在哈佛大學發表講演時,題目是《分裂的世界》,對西方的拜金主義、實用主義和自由主義進行了抨擊。這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甚至可以說遭到圍攻。美國的報紙稱索爾仁尼琴是一個“忘恩負義的老頭”。
1994年,首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迎接索爾仁尼琴回國,索翁仍保持著一個“批判者”的本色。他公開貶斥新權貴,批評民主派,也批評共產黨。當戈爾巴喬夫要為《古拉格群島》給索爾仁尼琴頒獎時,他拒絕了。他說:“我不能因為一本用幾百萬人的血寫成的書而獲得個人榮譽。”當葉利欽在他80歲生日要頒發給他圣安德烈勛章時,他又一次斷然拒絕了,他說“不能從一個將俄國帶入當今災難的最高權威那里接受獎賞”。
俄羅斯人評價索爾仁尼琴時有這樣一段話:“今天的索爾仁尼琴仍然是昨天的那個索爾仁尼琴。”高爾基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說‘不!”索爾仁尼琴就是這樣一個永遠說“不”的現行制度的叛逆者。
1911年,普列漢諾夫回眸沙皇專制統治的俄羅斯文壇,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一切歷史,自然包括文學史,都可稱為一片大墳場——其間,死者多于生者。”這與《紅樓夢》中的詩句“只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有異曲同工之妙。一手狼牙棒、一手胡蘿卜的政治手腕,使一批人不幸“夭折”,使一批人滋潤地“活著”。不斷“死”去的人,增加著這個大墳場的死寂;活著的人醉生夢死行尸走肉,也使這個死寂愈加陰森。
然而在這一片死寂中,俄羅斯文學畢竟時有強音發出。普希金在《紀念碑》一詩中呼喊:“不,我不會死亡——我的靈魂在圣潔的詩歌中,將比我的灰燼活得更久長。”
俄羅斯一批不屈的反對者,用自己不朽的作品聳立起一座座靈魂的豐碑。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