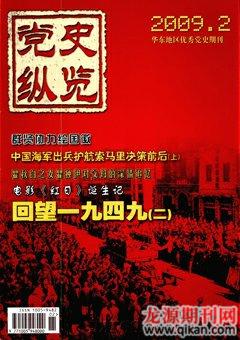陳獨秀與高一涵
楊 飛 范 婷

陳獨秀一生酷愛寫作,“除卻文章無嗜好”,他在63年的人生歲月中,給后人留下了數百萬字極具價值的文章著述;他自幼輕錢財,重感情,知己滿天下,“世無朋友更凄涼”。以文章為媒介,陳獨秀與皖籍同鄉、著名學者高一涵由相識到相知,在歲月的磨礪中,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一
1913年9月1日,在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重兵圍攻下,南京失守,孫中山發起的討袁“二次革命”宣告失敗。10月21日,袁世凱的爪牙、時任安徽都督的倪嗣沖發出通告,捉拿革命黨人,第一批名單有20人,陳獨秀赫然被列為第一名“要犯”。在反動軍警的嚴密搜捕下,陳獨秀在安徽無法藏身,遂潛往上海,后于1914年7月東渡日本。
到達日本后,陳獨秀進東京雅典娜法語學校學習法文,同時幫助老友章士釗編輯《甲寅》雜志。《甲寅》雜志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釗、陳獨秀外,還有在早稻田大學讀書的李大釗、蘇曼殊以及在明治大學學習的高一涵等人。也正是由于編輯《甲寅》雜志的機緣,陳獨秀以文會友,結識了高一涵,兩人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傾心交往。
高一涵原名永浩,別名涵廬、夢弼,1885年2月生,安徽六安人。他8歲入私塾讀書,13歲即能詩善文。中學肄業后,考入安慶安徽高等學堂,陳獨秀曾在該校任教,因此他與陳獨秀又有師生之誼。1913年,為了進一步探索富民強國之道,高一涵東渡日本,考入東京明治大學攻讀政法。在這期間,他與“二次革命”失敗后流亡日本的著名革命家章士釗結識,思想進步的高一涵被章士釗在東京創辦的《甲寅》月刊所吸引,遂加盟《甲寅》雜志,成為章士釗麾下的主要編輯之一。
在章士釗的介紹下,陳獨秀與高一涵在《甲寅》編輯部里相識。陳獨秀與高一涵兩人很早就聽說過對方,彼此都很欣賞對方的文章,只恨無緣一見。此次相見,陳獨秀一口濃重的安慶口音,讓與其有師生之誼的安徽老鄉高一涵倍感親切,他那樂觀大度的革命豪情、淵博的學識、敏捷的才思,以及對政治問題精辟的分析,更讓高一涵深為嘆服。而英姿颯爽、思想激進、對政治問題很有見地的高一涵也給陳獨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陳獨秀與高一涵初次相識時,陳獨秀“窮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虱子在內存活”, 而高一涵亦“為窮所迫,常斷炊”,于是,兩人便相約共同投稿,以每月的十幾元稿費勉強度日。患難見真情,陳獨秀與高一涵在日本的這段艱苦生活,以及兩人由此結下的真摯友誼,為他們以后攜手編輯《新青年》、領導五四運動打下了基礎。
1914年11月10日,《甲寅》第I卷第4號出版之后,章士釗離開日本返回上海,《甲寅》雜志社也隨之遷回國內。隨后,在日本就萌發“讓我辦十年雜志,全國思想都全改觀”念頭的陳獨秀,亦于1915年6月回國抵滬,開始積極籌辦自己的“雜志”。陳獨秀首先便想到了高一涵,誠心誠意向他約稿。
接到陳獨秀的稿約后,高一涵奮筆疾書,先后寫出了《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近世國家觀念與古相異之概略》、《民約與邦本》、《國家非人生之舊宿論》、《讀梁任公革命相續之原理論》、《自治與自由》,以及譯文《戴雪英國言論之權利論》等文章,陸續刊發于1915年9月15日開始發行的《青年雜志》創刊號至第6號。這使得高一涵成為繼陳獨秀之后的《青年雜志》的第二號人物。
作為《青年雜志》的主要撰稿人,高一涵還將李大釗的不朽名作《青春》推薦給了陳獨秀。在接到大氣磅礴的《青春》之后,陳獨秀立即安排在《青年雜志》第2卷第1號上發表,并從這一期起,將《青年雜志》改名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青年》。《青年雜志》改名為《新青年》雖然有許多其他原因,但刊發李大釗的《青春》一文也是促其改名的一個重要因素。改名后的《新青年》雜志先是倡導文學革命,發表白話作品,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繼而又率先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對馬列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共產黨的成立做出了重大貢獻。當然,這里面也有高一涵的一份功勞。
二
1917年8月,經時任北大文科學長的陳獨秀介紹,高一涵進入北京大學,先后擔任北大叢書編譯委員會委員、講師、教授,還兼任北京中國大學教授、政治系主任。高一涵也因此成為新文化運動基地“一校一刊”的核心人物:“一校”即指北大,高一涵時任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一刊”為《新青年》雜志,高一涵是《新青年》六大主編之一。
《新青年》創刊初期,高一涵以其深厚的西方政治學素養和文法精密、論理嚴謹的古文,筆鋒觸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民主與專制的區別、國家與國民的關系、民主與自由的關系以及人生的價值等諸多方面,主張以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代替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連續發表宣揚西方民主、自由、人權思想的文章,“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成為陳獨秀最重要的助手。同陳獨秀一樣,他不僅極力宣揚民主啟蒙思想,而且也積極投身到實際活動中,試圖以此喚起國民的民主意識和參政意識。在這期間,高一涵還與陳獨秀一道,參加了北京大學內部新派力量與守舊派勢力的斗爭。
《新青年》始創時,陳獨秀與胡適、高一涵等編者及主要撰稿人曾有“不談政治”的約定。但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1918年,陳獨秀開始意識到僅強調“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而回避時事政治是不行的。因為個人的思想修養無時無刻不受到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影響。而且,一戰結束后,國內外政治形勢變化迅速,《新青年》作為出版周期較長的大型文化月刊已顯得不夠靈活,不能滿足形勢發展需要,于是,陳獨秀開始設想編輯一個專門評論政治問題的刊物。這一想法得到了以研究法政為主攻方向的高一涵的理解和支持,并共同醞釀創辦一份“政治辯論論壇”性質的小型雜志。
1918年11月下旬,一生標榜不愿談政治的胡適因母親去世,返回了安徽老家,陳獨秀與高一涵等一些有談政治愿望的朋友便利用他不在北京的機會,于11月27日在“文科學長室議創刊《每周評論》”,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與會。大家“公推陳獨秀負書記及編輯之責,余人俱任撰述”。《每周評論》為周刊,以“主張公理,反對強權”為宗旨,編輯部設在沙灘北大新樓文科學長辦公室,發行所在北京騾馬市大街米市胡同79號,初定于1918年12月22日出首期。
《每周評論》創刊后,陳獨秀的思想逐漸向馬克思主義軌道轉移,但高一涵的思想卻仍停留在社會民主主義階段。陳獨秀認為:“強力擁護真理,平民征服政府”,要民眾用“直接行動”達到目的,將民眾運動視為奪取或摧毀現行政治制度的手段。高一涵則反對暴力革命,堅持走憲政民主的議會道路實現社會主義,挽救中國社會的危機,他認為“……中國的問題,非從法律上改革不可”。盡管與陳獨秀出現一些思想上的分歧,但高一涵理解和支持陳獨秀從事革命活動的態度始終沒有動搖過。從《每周評論》創刊開始,一直到被反動政府查封結束,高一涵一共發表了12篇文章和33篇隨想。不僅如此,他還以巨大的熱情積極投身于陳獨秀領導和號召的革命實踐活動中。由此,二人結下了深厚情誼。
三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運動發生后的第三天,高一涵就在陳獨秀的提議下,寫下了《市民運動的研究》一文。文章認為,五月四日,北京發生的“完全是市民的運動,并不單是學生運動。這件事順著世界新潮流而起,絕不可輕易看過”,他甚至強調:市民運動“是國家興旺的氣象”。高一涵的文章對于號召人們起來參與“五四運動”,擴大“五四運動”的社會基礎,具有重要的意義。
為了進一步推動運動的發展,陳獨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對當時中國的內政外交提出了5條具體的要求,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表達了其“平民征服政府”的思想。《宣言》寫好后,陳獨秀交由胡適譯為英文,并在6月8日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邊一個專為北大印講義的小印刷所去印刷。第二天,陳獨秀與高一涵等人親自到北京新世界游樂場、城南游藝場等處廣為散發。

6月11日晚10時,當陳獨秀再次在新世界娛樂場向下層露臺上看電影的群眾散發傳單時,被北洋軍閥政府的便衣警察當場逮捕,押往外右五區警署。夜12時,軍警百余人荷槍實彈包圍了陳的住宅,破門而入,當即搜去信札多件。
忽聞陳獨秀被捕,高一涵大吃一驚。他迅速聯系胡適等一大批著名皖籍人士,為營救陳獨秀積極奔走。最終,懾于輿論的壓力,在高一涵等一大批陳獨秀的安徽同鄉和老朋友們的營救下,經受了83天牢獄之災的陳獨秀被保釋出獄。
陳獨秀被保出獄時,保釋書上曾有“不得擅自離京”一條。但1920年1月29日,接到章士釗等籌辦西南大學發來的邀請函,生性倔強的陳獨秀毅然決定秘密前往上海。2月4日,他又溯江而上,來到武漢,在這里進行了多場講演,提出“打破階級的制度,實行平民社會主義”;“打破繼承的制度,實行共同勞動”;“打破遺產的制度,不使田地歸私人傳留享用”等政治主張,使得湖北官吏極為驚駭,明令其停止講演。無奈之下,陳獨秀乘車返回北京。
此時,京師警察廳已偵知陳獨秀潛出北京多日,決定在陳獨秀返京時,將其逮捕囚禁。高一涵和李大釗等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靜候在北京西車站,將他秘密送到北京大學的同事、《新青年》撰稿人之一、同陳獨秀關系也相當密切的王星拱教授家,以暫避風頭。2月中旬,李大釗與高一涵、王星拱等人商定:陳獨秀和李大釗化裝成下鄉討債的商人,出朝陽門去天津。李大釗讓陳獨秀頭戴氈帽,穿上王星拱家廚子布滿油漬的背心,躲在車里。說河北話的李大釗則坐在車把上,攜著幾本賬簿,像個外出討年關賬的生意人。兩人一路平安地出了北京城。隨后,陳獨秀從天津乘船到了上海,《新青年》編輯部隨之從箭桿胡同9號遷回上海。就在這次離京路上,李大釗與陳獨秀相互約定,南呼北應,共同籌建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也就是在這一年,陳獨秀與李大釗在上海、北京先后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稍后,中國共產黨于1921年7月在上海誕生,陳獨秀出任黨的第一任總書記。
高一涵參加了這次營救陳獨秀的行動,心情很激動,多年來一直記憶猶新,甚至在陳獨秀被解除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跌至其人生的最低谷時,他還為參與營救陳獨秀而感到自豪。而陳獨秀對高一涵的這次救命之恩也念念不忘,無論是身居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高位,還是落寞寄居四川江津,都常常提及此事。那時,陳獨秀與高一涵由于種種原因相隔甚遠,不能相見,但每憶及此,一生珍視親情和友情的陳獨秀都會熱淚縱橫,對摯友的掛念與感激之情,盡顯無遺。
四
在“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際,高一涵并未介入李大釗與陳獨秀籌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但是,他的思想已經明顯受到陳獨秀的影響。1921年,為了從事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研究有密切關系的歐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搜集歐洲政治思想史資料,高一涵再次去了日本。也就是在這一年,高一涵專門寫了一篇《共產主義歷史上的變遷》的文章,同時參加了《新青年》舉辦的“社會主義討論”,還于這年5月14日應清華學校政治學研究會的邀請,做了《共產主義之歷史》的學術演講。
1926年,高一涵在赴武昌途中由李大釗和高語罕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在李大釗的動員下去武漢找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準備參加武漢的革命工作。當時武漢的革命形勢如火如荼,身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的陳獨秀工作相當繁忙。見到老友高一涵后,陳獨秀異常高興。鑒于其在政治學方面的較高造詣,陳獨秀安排高一涵擔任國民革命政府設在武昌的中山大學的教授,并兼任法科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還出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編譯委員會主任委員。此后,高一涵便在陳獨秀的領導下,同陳獨秀等中國共產黨人一道,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不懈奮斗。
1927年7月15日,繼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汪精衛也在武漢發動了反革命政變,殘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不久,陳獨秀被解除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被迫轉入地下。鑒于與陳獨秀的特殊關系,高一涵無奈之余,跟中國共產黨脫離了組織關系,由武漢到上海避居,先后在上海法政大學和吳湖中國公學擔任教授,并出任新建立的社會科學院院長。1931年,他還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出任南京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1935年又被任命為駐武漢的兩湖監察使,1940年轉赴蘭州出任甘、寧、青監察使。
晚年陳獨秀窮困潦倒依然筆耕不輟,他傾其主要精力,歷經數載,寫成了一生中最為重要的學術著作——《小學識字教本》。對此,高一涵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而同樣醉心于學術的高一涵也不甘落后,他先后完成了《政治學大綱》、《政治學綱要》、《歐洲政治思想史》、《金城集》等著作,并翻譯了美國的《杜威實用主義》、《杜威哲學》等書籍。1942年5月26日,陳獨秀因病在四川江津鶴山坪逝世。噩耗傳來,高一涵禁不住老淚縱橫:“仲甫啊,仲甫,你怎么能先我而去呢……”過度悲傷使得高一涵聲音哽咽,聞者無不落淚。
抗日戰爭勝利后,高一涵回到武漢,復任兩湖監察使,他多次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掩護董必武、周新民等共產黨人。解放戰爭后期,他逐漸脫離了與國民黨政權的聯系,隱居南京,后與中共秘密組織聯系,同朱子帆、沈子修等民主人士一道,為迎接南京的解放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高一涵先后任南京大學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學院院長和江蘇省司法廳廳長、江蘇省政協副主席等職務,并擔任江蘇省民盟副主任委員。稍后,他還作為中國民主同盟的代表,被聘為全國政協委員。1968年,高一涵因病在南京去世,被安葬于雨花臺公墓,終年84歲。
陳獨秀與高一涵從以文相識到相知,在歷史的長河中,共同演繹了這樣一段友誼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