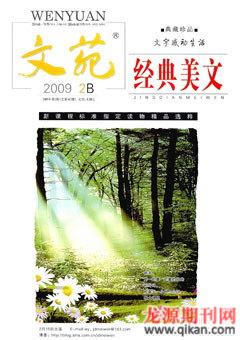紡車記憶
李漢榮
在《辭海》的深處有它的芳名和生平,還有附圖,說明它的結構、部件名稱及功能。我從它的身邊剛一轉身,它已被潮水卷走,只在文化的深海里,占據著一個小小的、化石的位置。
然而,在深遠的天空下,古中國世世代代的生活,都有紡車搖動、旋轉的身影。
它嗡嗡的聲音,混合著雨的聲音、雪的聲音、風的聲音、河流的聲音;也混合著蠶的聲音、雞叫的聲音、檐滴的聲音、家燕筑巢的聲音、狗吠的聲音;有時混合著遠處兵戈的聲音、殺伐的聲音。
它偶爾被打斷,但不會終止。天上的雷電,地上的暴君,都很短暫,只有一種聲音如河流般綿延著涌動,聽聽,那就是紡車的聲音,在無數個角落響起:嗡嗡嗡,嗡嗡嗡……
歷史縱有千萬頁厚,無窮厚,你隨意打開一頁,都會發現,它的根部,都由素樸的線連綴、裝訂。
就這樣,周而復始,輪回著,復輪回著,就這樣,紡車是一個得道的高人,講授著天地人生的大學問。
就這樣,母親們的手,世代搖著紡車,節奏溫柔,動作穩重,使大起大落的歷史,不至于暈眩和昏迷,而保持了正常的呼吸和勻稱的心跳。
我記得小時候,我母親紡線時的神態——她專注的眼神,沒有語言能夠形容。
她看著左手的棉芯被紡車一點點抽成白色的細線,稍不留意,線索拉斷,又得從頭再來。她看著棉一寸寸變成線,她目送著棉花不斷地離開自己,變成線,變成布,變成衣服,變成生活的顏色和款式。
于今想來,歷史的經經緯緯,都是母親的目光織就。
她莊重的姿勢,同樣沒有語言能夠形容。
她右手搖動紡車,左手抽出絲線,氣定神凝,面容安和。不同于虔敬,她并沒有面對一個神靈或祖先,她面對的是棉和紡車,是生活本身,因此,這莊重是對生活本身的尊敬,是對這勞作過程的尊敬。
我母親不是大家閨秀,并沒有受過詩書禮樂的熏陶,但我母親坐有坐相,站有站相,靜時如佛,動時如仙,日常生活里有著自然而然的風度和禮儀,這是為什么?
我只能說與傳承了數千年的民間風情有關,也與紡車有關,與有節奏、有經緯的勞動有關。這種勞動不教唆人的貪心和輕狂,而讓人變得知守常,懂規矩,有敬畏。如這紡車,有行有止,有動有靜;如那棉花,由棉而線,由線而布,由布而衣,一生的路,都守著貞潔的情操和柔軟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