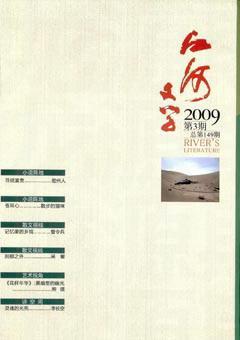蒼耳心
散步的貓咪
他說:“我只能承諾不跟你離婚,其他的辦不到。”
她生得丑,字亦不識得幾個。只因為她爹在一次礦難中救了他爹。五期紙后,他娘上門要了她這個孤兒做兒媳婦。
他不應。
但他孝順。忤不過娘的以死相挾。
婚終于結了。
洞房花燭夜,他搖晃著單薄的身子,和著濃重的酒氣,隔著紅蓋頭指點著她的額,撂下一句:我答應娘不跟你離婚,不過我的事你也別問,這,這是警告。頹然丟下一地嘔吐物和頂著紅蓋頭的她和衣睡去。她揭下蓋頭,心被滿屋的喜慶與安靜刺得通紅。收拾好臟物又打來熱水給他擦洗。她想,這是妻子的本分。立在床邊看他楚楚朗月似的臉,淚水珍珠般滾過粗糙的雙頰,重重落下,激起小小的歡喜的微塵。
日子過得平順。她整日里低眉順目,只知清掃煮飯,照料老人,還有一大幫子家畜。似乎,在村人眼里這也是段不錯的婚姻。只有他知道自己要的愛情至少是樹旁的一株木棉,或者是紅玫瑰和白玫瑰。她,于他,只是塊丑木,多看一眼,就添厭煩。
終于等來機緣,招聘會過五關斬六將,他在縣城小學當了一名語文老師。擺脫了窩窩頭和黑咸菜的束縛,擺脫了她唯唯諾諾的陰影,仿佛有了卸去枷鎖的輕松。
“我不愛她,從來沒有過。”他想。
一掃慣有的慵懶,才華加上勤懇,他在寸尺講臺上神采飛揚。上他的課,成了學生最大的期盼。不久,提了職,分了房。他想接爹娘同住。老人惦念家中幾口薄田,不肯。她,守著滿腹卑微,躊躇著說不出好,或者不好。他不強求,沒有她,更心凈。七年,他一直當她是可有可無的東西,無視,甚至回避她的存在。
成功往往滋生人對生活現狀的不滿。他有遺憾。于是,他迷戀上紅的白的酒精,迷戀上一張張荷花臉和狐貍臉,越陷越深,越覺得自己是個男人。他的緋聞,她不知。就算有人傳進她的耳鼓,她也只是打著大大的哈欠說:坑人,坑人。
他輕易不回家,說忙,只按時讓人捎來家用。就算回來也跟她無語,更無親熱。而她卻不曾有半句怨言。仍舊算好他回來的日子,鋪床曬被,灑掃庭院,做他愛吃的蛋炒蒸野菜,一刻不停。婆婆拉著她的手說:“孩子,歇會吧。”她把散落的發絲抿到耳后,說:“娘,不累。”臉上的皺紋笑成一叢雜草,深掩起酸楚麻木的心。
他有風濕。
她哄著六歲的兒子拉他一起去找蒼耳籽。
“蒼耳能通鼻竅、祛風濕、止痛呢。”她重復著老中醫說過的單詞。他不知道,為這幾個單詞,她反復背誦了整整一天,只為怕說錯會招來他不屑的冷腔。
這天她少有的歡樂,少有地多言,還在鬢角插一撮淡紫色的野花。用眼角偷偷瞥著他問:“兒子,娘頭上的花好看嗎?”
九月的正午,陽光溫熱。她一邊在蘆席上鋪曬蒼耳籽,一邊聽廊下他和兒子說話:“這叫蒼耳,是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你看,它是什么形狀?不對,不對,不是圓的,它是紡錘形,嗯,就像你奶奶以前紡線用過的紡錘”。
她偷偷地想:什么是菊科?什么是草本植物?是不是地里的草都是革本植物?他怎么什么都懂啊?轉過身,眼前依舊是記憶里那個書生模樣。呆呆地望著他的背影,視線忽聚忽散,眼角彌漫起幸福的哀傷。他從兒子的眼睛里看到背后的她,突然轉過來。四目相對,空氣在剎那間凝固。望著她臉上僵硬的笑容,他的心,劃過一絲歉疚。撫摸著腿上兒子的頭發,兒子黑亮而濃密的頭發,像她。這是她身上最美的地方。他說:“孩子該上學了,還是城里的條件好一點,所以,我想讓他到城里去讀書,你,你也一起去吧,這么多年辛苦了。”他的話音剛落,她就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先是憋忍著抽泣,后來聲音很大,像打開了洪門,釋放出多年的郁氣。這是他第一次用商量的口吻和她說話,是他第一次認可了她的努力。她覺得所有的付出和等待都值了。她使勁地點頭。陽光照在她頭頂油亮的黑發上,閃出爍爍的一圈光亮。
是不是生活就此轉了個彎。她這樣想。
當天,她東收拾西收拾忙的不亦樂乎。他看了她的成果,只淡淡地說了聲,都扔了吧,用不著。她諾諾地應,僅帶走用粗格子布裹著的小小一包蒼耳。
坐在后排座上,她沉默著,心隨顛簸更加忐忑。倒是兒子,像一只自由的小雀子,興奮地問這問那,嘰喳不停。因緊張而挺直的脊背讓她感覺很累,于是,她松開緊絞的手指,緩緩地挪了個姿勢,并借此機會從后視鏡里偷偷看他。他正和兒子高聲地交談著,不時發出爽朗的笑。氣氛看上去輕松而融洽。她輕輕地吁了口氣,卻正巧被他捕捉在眼里。他說:“咱們家在三樓,靠近馬路。白天會很吵,也沒有鄉里哪樣寬敞。剛開始也許會有些不習慣,但慢慢就好了。”
他說家!是的,他在說家!我和他還有孩子的家!她又一次眼眶濕潤起來。這一天美好得如同一場春夢。她深深地喜歡這種感覺,并深深地害怕失去,失去她還未握住的幸福。
她努力地學習如何向小販砍價;如何跟電視上學做一些光鮮的菜肴;如何捏住粗嗓門裝出輕柔的樣子和鄰居說話;如何熟悉公交車的線路時間表;如何打理孩子和他的衣著;如何禮貌地接電話。為了弄明白家用電器的使用方法,她甚至開始學習文字。她也習慣了當有人在她面前稱呼他為沈校長時,要露出標準的八顆白牙;習慣了他的早出晚歸,習慣了在他醉酒后的整夜守候,在他翻身要水時,雙手奉上一杯溫熱的蜂蜜茶。她按他的要求燙了發,漂了牙。學會使用一些功能繁雜的化妝品,在自己的頭發上、臉上、手上、脖頸上。她甚至喜歡上照鏡子,喜歡在家里只剩自己的時候,偷偷地照鏡子。仔細地打量,然后很開心地爽聲大笑,并深深追憶彼時那個丑陋的鄉下婦人的身影。只是,他從不帶她出門,從不讓她參加孩子的班會,從不和她談論自己的工作和工作以外的生活。她倒也寧愿守在家里,守在等待門鈴響起的忙碌里。
分房而居,如大海里兩個世界的游魚。但是,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對她來說,已經是莫大的恩賜,她不敢奢求其他,不敢期待著進一步的親密。
只是,當不經意聽他電話里傳來的嬌媚女聲,不經意發現他口袋里的情書。衣領上的唇印時,當他一次次不做說明的未歸或深夜外出時,她的心,會扭曲著痛,會害怕。她常常把自己埋在黑暗的角落里,憋屈著,不敢出聲,只是大口地吸氣,吐氣。如同一條離開水的魚。是啊,他是她的水。他給,她就活;他不給,她只好缺氧地死去。
只是,也有不甘心的時候。她跟蹤他。親眼見證車廂里,一對男女在黑暗掩映下恣意地調情。但是,她不敢上前叫罵,甚至不敢哭出聲來。就那樣僵直地目睹事情的發生。在頭嗡的一聲巨響后倒在地上,黑瘦的身子直挺著,如同一條死去許久的魚。
她依舊沉默。對所有關于他的緋聞不做聲息。只是整日微笑著,在灼人的等待中打發時日。
“等他老了,走不動了,他就是我的了。”她想。
他習慣于她的侍奉,習慣于在家庭的寧靜中如沐春風。迫于聲望,他沒有拋棄她。看起來倒像是兌現了婚夜的承諾。只是,他仍
習慣無視她的存在,無視她的喜怒哀樂。
“給你吃喝,給你錢花,給你地位。你應該很滿足了吧?”
他這樣說的時候,她淺淺地微笑著,正盛滿滿一碗雞湯端給他,一條大雞腿橫在碗中央,突兀的很。
他沒有聽見她心碎的聲音。她的心一次又一次在他面前破碎,他卻從來沒有聽見過。他習慣于她的存在,如同習慣于在空氣里呼吸。
她等到了兒子結婚,女兒出嫁。她滿以為有足夠的時間等他屬于她,卻從沒想過時間不給她機會。
一夜,他醉醺醺地吆喝著要她倒水。久久不見回應。他心咯噔一聲慌亂起來,徑直推開她的房門,慘亮的燈光下,她的臉正憋得發紫,猙獰著,手臂在空中抓狂,像是要攥住救命的繩索。他的頭腦片刻間麻木,留下短暫的空白,緊接著撲上前,捉住她揮舞的手,大聲地叫:“來人,快來人。”已是深夜,老屋里也只剩他和她。
她張大了口,急促地呼吸,像一條因缺氧快要死去的魚。他俯下身,唇貼上她的唇。他要給她氧氣。這不是她一直渴望的嗎?她和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給他生兒育女,他卻從來沒有吻過她,從來沒有。現在他卻要急切地挽留她,要告訴她自己還沒有做好失去的準備,還沒有想過沒有她的生活應該怎么過。只是,這虛弱的挽留在死亡面前輕薄如煙飄過。
她用力地張了張嘴,終于安靜下來。因抽搐而變形的面部肌肉漸漸松弛下來。臉上似乎還帶著淺淺的淺淺的微笑,一如今晨她送他出門時的微笑。
他跪在床頭,手里緊攥著她的手,嗚咽著,不甘地再次吻上她的唇,給她做人工呼吸。眼淚滴落,從她臉上皺紋的溝壑中滑下,連同她唇上的溫度正一點點地散去。他嚎啕失聲。他知道自己被遺棄了,被一個他從不在意的女人遺棄了。這對他來說是多么荒唐的事。
“世上最愛我的女人去了!”他悲慟地想。他聽到有什么東西正在身體里噼啪地破裂,一聲聲,接連一聲聲。他突然想起順治哭董鄂妃的那場戲來,終于明白就算能呼風喚雨也會有上天人地皆無門的時候。像浪子頓悟了往日的混沌,再無風花雪月。他變得安靜起來,提前退了休,整日侍弄她留下的那些花草,還有一只瘸腿的卷毛狗。那狗是她從垃圾堆撿來的,那會兒已經奄奄一息,是她執拗地帶回家。她說她就像一條可憐的狗,不知道會在什么時候,會在什么地方,會毫無準備地就會被人丟棄。他看著她日記上的這句話,淚水噴涌而出。他以為給了她物質上足夠的多,這個從黃土坷垃里爬出來的女人一定會對他感激涕零,卻從沒想過原來她一直生活在忐忑中。他也沒想過她竟然不聲不響地學會了讀書寫字,更沒想到她會把他的一場場艷遇統統記錄下來。而那些女人香艷的名字在紙上橫豎交織成一張張哀怨的網,緊緊地纏裹著她,令她不能呼吸。
她說:“我像一個濃妝遮掩下的戲子,舞臺上披著人的皮,卸了妝,退回黑暗里,實在是個萎瑣的鬼。”他不敢相信這會是那個大字不識一筐的鄉下婆娘的文字,而這些字正如錐刺般狠狠地刺痛他的神經。令他寢食難安。
他用一把重鎖將這本厚厚的日記連同那個格子布的包裹一同鎖了起來。包裹里是她辛苦采來的已經落盡鋒芒的蒼耳子。是他不屑服用的蒼耳子。
她走了。他開始重新學習家里電器的使用方法,學習如何把飯菜弄熟,記住每個房間開關的位置……他努力地嘗試著她剛到這個家時努力學習過的一切。可是,他還是會常常忘記吃藥,忘記天冷要加衣,陰天出門要打傘,夜晚要在臥室、客廳、衛生間都留一盞小燈。所以他常常獨自哭著吃下夾生的飯粒,常常在做菜時切到手指,常常在夜晚上廁所時跌破膝蓋…,,她走了,他才終于悟出她的好,才終于明白這個蒼耳般丑陋的女人也有著所有的美,才終于明白了自己的悲哀:結婚時,他絕望地以為自己得到的是自己不想要的,而現在,卻已經永遠失去自已想要的了。只是,所有的后悔都已經太遲。
他開始信奉上帝,靜夜里他習慣了跪在神像前,一邊懺悔,一邊流涕。他曾多次祈求上帝讓他忘記曾經的浪蕩生涯,希望藉此減輕對心靈的折磨。不知道是不是上帝憐憫,十多年后:他終于得了老年癡呆癥。他再不能說話,對種種詢問也都沉默不語。他只愛呆呆地靠在醫院病床上看天上飄過的云彩。
如此,如此。
經年,經年。
終于,一個雷雨交織的夜,他去了。
他的私人護士說他走的很平靜,只是在臨終前曾突然坐起來,望著黑漆漆的窗外大聲高呼:“彩云,彩云!”
護士納悶地向同事說起他的死:“外面漆黑,哪有什么彩云啊?而且,他不是不會說話了嗎?”
自此這世上再無人知道她的小名就叫彩云。常彩云!
上帝曾讓他忘記人生的繁華喧鬧,卻唯獨沒有讓他忘記她,沒有讓他忘記常彩云!沒有讓他忘記這個被他忽視了一生卻又真正愛的女人!不知道這對他來說究竟是懲罰還是成全。
原來,這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我愛你,也不是明明相愛卻不能在一起;而是,在一起時不知道我愛你,等失去了才發現不能沒有你。
責任編輯,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