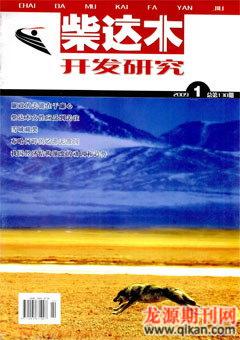潛龍西起(二)
王澤群
回到德令哈
2008年09月06日
與鄭登旗一起來接我的。還有州糧食局局長萬瑋。
萬局是老德令哈人了,但我在德令哈的時候并不相識。可是一見面,仍然親切。他那高高的個子,英俊的模樣,讓我感覺,這真是咱柴達木的男子漢啊!
凌晨里,天還未亮,但一路上還是可以感覺到德令哈的巨變。
首先是燈光多了,路邊的建筑也有模有樣了,不再是那一片荒原、沒有光影的戈壁灘。
這也才知道,火車站南移了,距德令哈有20公里。而這其間的20公里多了許多工廠與建筑。其中,很堂皇、讓我震動的是一間大型堿廠。極具規模。
車進德令哈,讓我這“老德令哈人”更是吃驚,完全不認識了。這路,這樓,這城市的布局,全都和我離開時不是一個模樣了。特別是海西賓館,那樣完美的建筑,那樣優美的庭園,園中的路,路邊的樹,樹上的花,花前的燈,燈光里現代線條的賓館,在凌晨的夜色燈影里美得讓人心動……等我住進房間,那一樓的大堂、雕塑、燈飾、華美沙發、環樓的二層、三層的廊臺……全讓我驚訝。我記起了我離開德令哈時的海西招待所,那典型的一排排平房和中間的一座三層樓的招待所大樓,我還記得那位勞動模范老趙所長呢……而現在,真正叫作不可同日而語了。房間的硬件也很過關,舒適,好用,大器,漂亮。
這一路,我住了西安的西京國際飯店,西寧的青海賓館,但德令哈的海西賓館絕對不遜色于這兩家都有些名氣的酒店呢!甚至,比它們更好,更美,更舒適。
畢竟凌晨。還可以找一個“回龍覺”,在這么好的賓館房間里,我五分鐘就睡著了——這是回到“老家”德令哈的第一覺。我睡得很穩,很香,很沉。
再次醒來,已是近八點了。去餐廳吃早餐,順便也把這海西賓館細細地看了一下。變了!變大了!大變了!不能說天翻地覆,卻可以說是眼前一亮,日月一新!
我的心中充滿了喜悅。是的,只有曾經在這里生活過二十年,又是二十年后再回來的人,才會對德令哈的巨大變化有真正的深刻的印象與強烈的興奮的感覺!因為這是柴達木,遙遠的西部的柴達木。你不是她的親人,絕不會有這種親情難捺的細膩溫暖的感覺呢。
萬局開了車來,登旗做陪,我們去看德令哈。
第一站,當然是我曾經的家。當年調入海西文聯,位于祁連路(當年叫團結路)那排獨門獨院的宿舍還沒蓋好,我們一家是住在海西招待所的二間房子里的。當那排宿舍蓋好,我是第一批就住進去了的居民。當年,對那獨門獨院、兩間隔成兩室一廳一廚的干打壘房子我們都滿意壞了呢。雖然入廁還要跑出院外去蹲那種“朝天坑”,但在1 978年,這已經是相當不錯了呢。在這個家里,我不知道接待了多少路過德令哈、采訪柴達木的作家、記者:在這個家里,我不知道和多少詩朋文友把酒論道,討論研究西部文化與瀚海詩文呢。然而,車到原址,過去的家、與院子、與大門已不留一絲痕跡。矗立于此的是嶄新的電信局宿舍,現代化的小高層宿舍!與當年我的家“風馬牛不相及”了!
這就是變化。我站在當年進家門的地方,讓朋友拍下一張難忘的照片。背后,是現代的風景;眼前,是亮麗的德令哈;心中,沒有遺憾,只有驚訝、驚喜、欣慰。
第二站,是去看我離開德令哈時的文聯大樓,那是八十年代的一棟新建筑,當時蓋竣,給了文聯不少的房間,幾乎可以說是寬綽得讓人自豪。那時候,我們就感覺到改革開放帶來的好處。但是,它也沒有了。在它的原址,是曠大的廣場,廣場一直與路北的原來的百貨大樓(當然,百貨大樓也沒有了!)毗連。形成了一片美麗的城市廣場區。
第三站,是我調入海西文聯第一個辦公的地兒。當時,文聯尚未成立,我們的那個單位叫海西州群眾文化工作站。可別小瞧了這個文化工作站啊。當時,也就是后來走向全省、乃至全國的柴達木的文化精英們,大部份都在這“站”里工作呢。當然,它的舊址也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民族進步團結塔”。我們的“站”,做了塔的一小部份基礎。是的,這個“文化站”,應當,也必須做為這個塔的一部份,小小的一部份基礎。
沒有基礎,哪來高塔;沒有最初,哪有未來。
祁連路這短短的三百公尺,我的家、單位、工作的地方,一條直線我走了八年。從青年,走到盛年,從一個文化工作者,走成一個專業作家。對于這條路,對于這座城,對于柴達木,我怎能不懷有深深地深深地感激與感恩啊!
得益于柴達木土地的富裕與遼闊,我發現,德令哈的路都修得極其漂亮、寬闊、平坦、現代。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座城市,德令哈有那么多的漂亮的廣場,夸張地說:“一去二三里,廣場四五個,雕塑六七座,八九十個闊。”到處都顯現出曠大與遼闊。這在其他的城市里,恐怕極難看到這樣的美景呢。它們沒有這么寬闊的土地。
萬局讓司機再一次送我們去堿廠飛車觀花。
這一次看得細一點兒了。連堿廠的院子,也是一個小小的廣場呢。時間緊,我們沒下車,只是任司機師傅開著小車在堿廠里彎來拐去,看廠房,看道路,看機械,看產品,看布局,看能看到的一切。萬局介紹說,很快,堿廠的生產能力將達到400萬噸,居世界第二,德令哈當仁不讓地成為中國堿都。我心中興奮異常!記得當年在德令哈工作的時候。我和張家斌、高澍等同仁對德令哈這座城市是否可以發展、是否能夠生存進行過多次探討。哲人說:“有了水,就有了生命;有了電,就有了文明。”水和電,德令哈都有,但當年的她,缺少一個城市發展的要件:高科技的大工業。當年的德令哈,只有一間農機廠,生產著微不足道的、出不了盆地的農機配件。而其他的工業。似乎都不好在這里開拓與發展。但一個內陸小城,既無旅游資源支持,又無傳統文化墊底,既不能像桂林、麗江靠風景出名,又不能像曲阜、敦煌有老祖宗蔭蔽;僅只是因為氣候環境條件較好,成為一個以政府部門為主的城市,沒有經濟的支點與熱點,她終究要衰亡的。依舊會成為一個驛站、或是農牧業據點。這正是我們熱愛德令哈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離開德令哈多年,曾聽說海西州的政府職能部門要向格爾木搬遷。遠在六千里之外,我仍然是著急且無奈:德令哈這座小城,還沒長大就要衰亡了嗎?
這次來一看,不一樣了。絕對地不一樣了。不光是有一個未來的“中國堿都”,其他的工業也在德令哈有了布局與建設,近一點兒的,好像是鐵路機械廠,遠一點兒的好像是有色金屬基地;盆地北緣,大柴旦不但開發了黃金產業,再西一點兒的魚卡也建起了煤業集團公司,錫鐵山已經走向全國,還有鹽湖,還有已探明的天燃氣大礦床,再往西的茫崖石油……只有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柴達木,這個被稱道了五十多年的“聚寶盆”,這一次才真正地顯現出她的巨大的潛能資源與真正的財
寶來了。
作為一個老柴達木人,豈能不興奮、振奮?豈能不對柴達木這片熱土,充滿了愛的熱戀?我想起了當年在西部走過的那些荒冢,那些在枯黃的席芨草搖曳中沒有姓名的墳瑩,那都是埋葬在柴達木里的柴達木的先行者啊!都是對柴達木這個祖國西部高原盆地充滿過憧憬的年輕人不死的精靈啊!今日,若他們碧落黃泉有靈,知道了柴達木今天的發展與飛躍,是不是也會透出一個欣慰的微笑來呢?是不是也會覺得自己的此生沒有白自度過呢?畢竟,他們比我們更偉大。他們奉獻了一生。
中午萬局設宴為我接風。主陪是從未謀面的州人大副主任朱建華先生。
朱副主任是位熱情、真誠、文學涵養很深的人,聽說我是為了寫一部真正反映當年山東青年支邊青海的大書《大戈壁》。要重走我在柴達木工作過的所有地方的想法,大為贊賞。畢竟,我是柴達木培養出來的專業作家;畢竟,我在德令哈奉獻了我最美好的年華,為柴達木的文學藝術也貢獻了我的一份心血。他立刻掛電話“召來”了宣傳部的楊東亮副部長,州文聯的肜子歧副主席兩位年青人,向他們隆重地推介了我,并要求他們要安排好我在德令哈的一切活動。楊副部長外向,肜副主席內斂,但都洋溢著一種西部人才有的熱忱與真誠。頻頻敬酒,侃侃聊天,主人們為我詳細地介紹了柴達木這些年,特別是最近幾年的飛速發展。去年,地區生產總值突破200億元,地區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突破40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0000元,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突破3000元,今年上半年已經是36億了。全年再有一個實實在在的大躍進確實不在話下!
我感動,我振奮,我欣喜。柴達木這條五十多年潛在的巨龍,在今天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真正從西部起飛騰躍。一展雄姿,已經是指日可待了!
下午,萬局和楊副部長親自陪我去了可魯克湖。
去可魯克湖其中的一種原因是為了去品嘗大閘蟹。離開德令哈的時候,已經聽說放養了大閘蟹了,但走時匆匆,放養也是初始,并不知道這江南的美味是否和西湖鯉魚一樣,能夠適應我們這高原寒冷的特殊氣候。
“沒問題!”楊副部長高興地說,“長得一點兒也不比江南差。你想想那大鯉魚么!”
是的。我想也是沒問題。當年,可魯克湖剛剛放養西湖鯉魚的時候,我曾來此采訪,曾經是兩位員工劃了一只小劃子載我進湖的。那一片天高水闊,那一種嫻靜安逸,那一派秀美鮮亮,那一幅江南風光,葦綠水清,漣漪層層……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更記得有一次一條重十七斤的大鯉魚被捕獲上來,送到海西招待所食堂的時候,就是一條爆炸性新聞。好多人都專門來食堂里看看那條膘肥體厚的高原鯉魚。還記得有一次我陪著外地來的作家詩人們來拜謁可魯克湖,他們聽了可魯克湖與托素湖的傳說故事,一個個驚訝地睜大了眼睛,怎么也想不明白,為什么只有一河相連的兩座湖泊會有這么大的差別?他們更對那流傳已久的“情人湖之戀”充滿了好奇與想象……在這樣荒涼的高原大漠里,有這樣神奇的情人湖;在這樣神奇的情人湖中,一個是淡水,一個是咸水;一個葦綠草盛,一個寂寞荒涼;一個居然可以養出肥碩的大鯉魚,一個卻連最基本的生物都不長?讓那些“內地人”驚嘆連連!哈哈!這就是柴達木呀!這就是神奇的西部的可魯克湖!
再一次站在可魯克湖邊,我依舊是意蕩神迷!太美了,可魯克湖,太好了,神奇的柴達木盆地。
那長長地通往碼頭的路邊,白茨果結得正盛;那高高的蘆葦青青地繞滿湖畔,只幾小舟。裝了它的風景;兩座紅頂的涼亭是新添的,若隱若現在湖邊讓人心生感動。
船來了,我再一次在湖中逡巡,看漣漪破浪,推碎了藍天白云,推不碎的卻是我對這可魯克湖的愛戀。柴達木的這一座湖,給柴達木增添了多少景色與詩韻啊!柴達木能夠出產大閘蟹!這本身就是對高原盆地最好的宣傳與證明。
2008年09月07日
去拜訪州文聯,看看當年的編輯部,是我回到德令哈的一大心愿。還有,去見見一直與我保持著聯系,從未謀面卻給我提供了柴達木各方面信息的《柴達木開發研究》編輯部的朋友們,也是我的一大心愿。
雖然都是我不認識的人了,但一進入州文聯,仍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親和與熟悉,州文聯的辦公地兒與過去不同,一是強化了少數民族的刊物編輯班子,二是辦公室比原來更擴大了。當然全是“生面孔”啦!肜副主席向我做了介紹——李占國、李春蓮、吳海燕、胥海蓮、崔建偉,像1 978年的我們一樣年青,一樣充滿生命的活力!他們仍然堅持著那份當年我們開發柴達木改革開放新文化時期的刊物,只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嚴酷競爭,他們辦得比我們那時候要艱難多了。主編李占國先生找出了當年《瀚海潮》的合訂本,我捧著它留了一張影,然后和編輯部的年青朋友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留了影……
我不知道我能否再回德令哈,能否再來州文聯、再進編輯部,但是我知道,隨著柴達木真正的日益飛躍、闊步前進,《瀚海潮》這朵三十年前開放在一片荒蕪的戈壁上的文學小花,只會越開越旺,越開越艷的。因為,中國,在進步!中國人民,在進步!
中午,肜副主席設宴,意外地碰見了我惟一仍留守在德令哈的同事喬永福。緊緊擁抱,深深敬酒,殷殷祝福。喬永福、肜子歧和其他的年青文友們送了我好厚好厚的一摞新著。捧著這沉甸甸的書,好似捧著整個柴達木盆地,捧著柴達木的新人們晶瑩的汗珠。
巴明德先生是接到我的電話就趕了過來的。見文聯的同仁們留了我,他下午再開車,接我去了《柴達木開發研究》編輯部,與《柴達木報》的總編輯王浩先生一起接待了我。
我是深深地感謝《柴達木開發研究》的,正是《柴達木開發研究》讓我和柴達木的聯系沒有斷線,讓我的第二故鄉柴達木時時刻刻地與我保持著息息相關的聯系。我的許多關于柴達木的回憶與思念,也都是刊登在這本刊物上的。
記得回到青島若干年后,突然收到了一本雜志,爾后,又接到了當時的執行主編張珍連先生的電話,約我寫一寫關于柴達木的文章。我拿到刊物,一口氣從頭翻到了底。人,就是這么個“東西”,當他知道了他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地方的新信息的時候,他是恨不能立刻再一次飛回去親自看一看,聽一聽,見一見的。而《柴達木開發研究》代我完成了這個夙愿。巴明德先生接任主編后,與我的聯系更密切了,我期期準時收到刊物,而且常常是三冊——他們知道,在青島,我有許多柴達木返青的戰友呢。他們常常會來我家,拿起《柴達木開發研究》看著看著就裝進兜里“拐”走了。人,怎么能不眷戀著生他養他的那片土地啊!不管她多么遙遠、多么荒僻、多么寂靜,人的心思,此一生的心思,是不會不思念關懷著她的。
2008年09月08日
昨夜,獨自去巴音河畔走了走。
對于這條河,我是懷著神圣的情感的。是它,養育了這一方土地,是它,讓我們可以在這里建一座城市;是它,給柴達木創造了兩個神奇的湖、百里林帶、萬畝良田;是它,保證了人類在這里的開拓與發展。
記得初進柴達木的1966年6月,我們第一夜宿在黑馬河,第二夜就是在德令哈。
第一夜,我們許多同學相約去看青海湖,從黑馬河畔走啊走,終于走到了青海湖畔。遠看靜靜的青海湖,走近了才知道好大的風。湖上的浪不亞于青島海邊的浪,甚至更冷冽、更波動、更嚴峻。讓我印象極深刻。
第二夜,在巴音河畔,這條河卻給我留下了極美、極溫柔的記憶。那時候的巴音河完全是自然形態的河。它曲曲彎彎地穿過小鎮德令哈,河面是清亮湛藍的浪花,河底是彩色的鵝卵石子兒,波動得美麗極了。河上,是一道低于河岸的木制橋,幾根木柱,一河流水,完全是一幅高原風情畫的模樣兒。而現在的巴音河,正在大施工,要修建成一道一道的疊水湖,兩岸業已砌平。想來不久再見巴音河,將是一座人工的花園湖似的河了吧?
這真是一個悖論——在現代化的城市里生活的人們。渴望自然;在自然狀態里生活的人們,渴望現代化。
人類,就是這么矛盾地前行著,改變著世界也改變著自己,獲得了許多也失去了許多。
上午去郵局寄書,到銀行為太太辦工資卡,我更感受到德令哈人,不。應該是柴達木人的熱情與質樸讓人心暖、心動。這是我走過許多城市也難以感覺到的美好感情了。
先說寄書。新朋老友送我的書當然珍貴,但帶著一路旅行卻困難,登旗陪我去郵局寄。這么多書,需要一個紙箱,郵局沒有合適的,便出門去找。進了一家書店,說明來意,人家二話不說,就給我一個紙箱,我要付錢,人家死活不要。而郵局的同志,則是熱心地幫你裝箱、捆扎打包。那份真誠自然。讓你心暖得無以言謝。銀行更不用說了,幾位女同志非常認真細致地幫我把一個身份證號、密碼號全都搞錯的工資卡理順了。雖然費了不少的時日,但她們不急不惱,還替我解釋政策、出主意,終于把這事兒也做成功了。
兩次和服務界的人士打交道,兩次都感受著柴達木人的質樸與真誠,讓我更喜歡我這第二故鄉了。
驟然想起二十年前在德令哈“辦事”,從來都很順利、容易,當時以為是“人頭兒熟絡”,理應如此;這次來,可是地不熟、人更生了呢,也辦得讓人心里順暢痛快。可見,仍是這高原盆地里民風質樸可鑒。
德令哈的三天,感受極深。更莫說在一場場酒宴上。新朋舊友的豪爽俠義,杯杯見底的真情厚意了。文章寫到這兒,心中涌動,不由得再從工作室的酒柜里取一瓶從青海帶回來的“七彩互助青稞酒”,滿斟一杯,向西北,向高原,向柴達木,遙遙致敬,深深一酹!
德令哈;我生命中的德令哈;我生命中永遠的德令哈;我生命中永遠葆有繽紛絢麗難忘的德令哈。我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