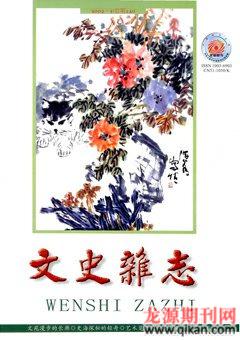杜詩中的“衛(wèi)八處士”
鎖 理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這是感慨人生難逢(如參商二星,此出彼沒)的著名詩句,出自杜甫《贈衛(wèi)八處士》首二句。只是那“衛(wèi)八處士”是誰,卻不得而知。
杜甫《贈衛(wèi)八處士》屬五言古詩,比較長,這里暫且引前八句: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今夕復(fù)何夕,共此燈燭光。
少壯能幾時,鬢發(fā)各已蒼。
訪舊半為官,驚呼熱中腸。
一般認為,此詩系杜甫自洛陽返回華州(治所在今陜西華縣)途中所作,時在乾元二年(759年)春天。那么,杜甫當年是寫給誰的呢?傳為唐宋間作品的《唐史拾遺》說:
杜甫與李白、高適、衛(wèi)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號“小友”。
所以,舊注多以“衛(wèi)八處士”即衛(wèi)賓。但明清以降的注杜者卻不信。如清人錢謙益《錢注杜詩》在“略例”中質(zhì)疑道:
有本無其名而偽撰以實之者,如衛(wèi)八處士之為衛(wèi)賓。
清人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注此詩也說:
師氏引《唐史拾遺》作衛(wèi)賓,乃偽書杜撰,今削之。
宋人注本中的“師氏”有兩個人,一是師尹即師民瞻,一為師古。究竟《唐史拾遺》是否偽書?朱鶴齡所論“師氏”是誰?因無關(guān)本文旨趣,暫且不作追究。
清人仇兆鰲的《杜詩詳注》,于此也不相信是衛(wèi)賓。其注引黃鶴之說,“衛(wèi)八”或是唐代居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濟蒲州鎮(zhèn))的隱逸衛(wèi)大經(jīng)的族子,并推斷此詩系杜甫于乾元二年春任華州司功參軍時至蒲州衛(wèi)家所作。
但是,清人施鴻保在《讀杜詩說》中卻于此而駁仇注。施氏云:
今按,謂衛(wèi)八即大經(jīng),或未可知;若謂大經(jīng)隱逸,其族子亦隱逸,故稱處士,未免附會。
不過,今人有認可仇兆鰲的。如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杜甫年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述杜甫在乾元二年時的行蹤說:
道出蒲州,與少年時之友人衛(wèi)八處士相遇,因飲其家,作《贈衛(wèi)八處士》詩,……衛(wèi)疑為唐隱士衛(wèi)大經(jīng)之同族,居蒲州,必杜甫將抵華州時道經(jīng)其家一宿,故明朝又別去也。
筆者查《舊唐書·隱逸列傳》,知衛(wèi)大經(jīng)乃武則天時著名隱士,“則天降詔征之,辭疾不赴。”他在開元(713—741年)初時“已年老”,“如筮而終”。即以開元元年(713年)至開元四年(716年)計,杜甫當在1~5歲之間。因此從年齡上推算,衛(wèi)大經(jīng)的族子輩不該是杜甫少年時的朋友。
現(xiàn)在來看,或者“衛(wèi)八處士”就是《唐史拾遺》上講的杜甫等人的“小友”衛(wèi)賓。因為杜甫《贈衛(wèi)八處士》詩中寫與衛(wèi)八處士分別已“二十載”,又說“昔別君未婚,男女忽成行”。以乾元二年(759年)向上推算,杜甫與衛(wèi)賓分別時約在開元二十六年~二十九年(738—741年);再參照古代婚俗,當時衛(wèi)賓年齡當不過二十,所以才未婚;而杜甫已是27歲至30歲的人了。至于李白、高適均比杜甫年長。所以,衛(wèi)賓當然是“小友”了。查今李白集中不見有涉及衛(wèi)八的詩,但高適詩中有兩首,即《酬衛(wèi)八雪中見寄》與《同衛(wèi)八題陸少府書齋》。其中第一首系高適寓居淇上(在今河南衛(wèi)輝一帶)時作。據(jù)周勛初《高適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高適寓居淇上的時間約為開元二十九年(741年),高適酬衛(wèi)八詩估計也是這一年的作品。又,開元二十九年是開元年號的最后一年,這同杜甫自敘與衛(wèi)八分別時間大致吻合。所以,杜詩中的“衛(wèi)八處士”是衛(wèi)賓的可能性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