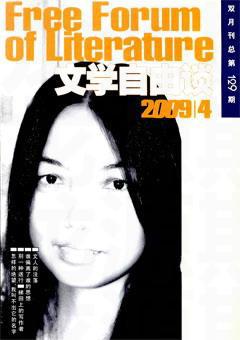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
沈東子
苦難如今是一個時髦的詞兒,用朋友龍子仲先生的話說,如今賣弄苦難成了一件時尚事。你的作品里有苦難蕩漾嗎,讀起來苦嗎?似乎有苦難才夠恢宏,夠博大。問題是苦難可以掛在嘴上嗎,可以賣嗎,賣掉的東西還叫苦難嗎?我想趁新鮮賣個三五年還是可能的,只是回過頭看,那苦難可能只是個笑話。這個話題老讓想起契訶夫的那個比喻,少女失戀和守財奴丟失錢包,二者都哭泣,二者的苦難都很真實,可是世人只同情前者。
舉個簡單的例子,《紅樓夢》之所以成為《紅樓夢》,是因為它的主線描寫了寶黛悲劇,作家對那悲劇寄予了同情,敘述是從容的,文字是悲憫的,小說在描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時,也寫了焦大的痛苦,可是如果曹夫子把大量筆墨給焦大,那小說就肯定不叫《紅樓夢》了。我寫過一篇文章,大意是說為什么焦大成不了怡紅院院長。焦大其實是有可能成為怡紅院院長的,如果他造反或者參加造反的話,或者說如果他革命或者參加革命的話,參加革命越早,就越可能做上院長,只是在曹夫子眼里,院長的事不值得描寫,焦大再焦慮,他也不想寫,他寧可寫黛玉的淚花。
寶黛的愛情悲劇就像五彩斑斕的氣泡,破了就沒了,再也復原不了,是一種命運的無奈,命運的無奈有很多種,堂·吉訶德與風車做徒勞的搏斗,老人捕魚捕回一架魚骷髏(《老人與海》),相形之下,焦大的夢想是有奈的,他想升官發財,想得到漂亮女人,并為此感到痛苦,這是一種地位的痛苦,若干年后,焦大的痛苦,紹興人阿Q也感覺到了。這種痛苦是有可能改變的,這種改變每天都發生。不客氣地說,過往許多年,我們的許多文學作品,包括獲獎文學作品,以人的尊嚴為假托,描寫的說是翻身做主,實際上是轉換和聚斂財富,同情和贊賞的都是造反獲得錢財,獲得地位的過程,趁著亂世一夜間可以把他人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積攢的財富居為己有,這種過程可以感動并征服別人,但不能感動或征服我。
高爾基說過的話有的不像話,但也有很精辟的,他在指出俄國十月革命的本質時說,單純的物質轉化不能提升一個民族的精神價值。用淺顯的話說就是,靠剝奪財富,把富人變成窮人的方式,不能改變社會的本質,只有創造出新的財富,才能實現人與人之間的相對平等。文學不是政治,也不是通訊報道,文學比政治和新聞高明得多,現實政治看重的是眼下利益的轉換,新聞表述的是淺層次的苦難,文學追問的是人性悲劇的根源,這種悲劇絕不是苦難兩個字可以概括的,它要比苦難豐富得多,它呈現的面貌可能是愁苦,可能是憤怒,也可能是欣悅,澹定和寧靜。
我曾經讀過一本俄羅斯小說,大為贊賞,這贊賞被一個領導知道了,他也找來那小說看,看過后對我說,我不覺得那小說有多好呀。這件事讓我既感動又納悶,感動的是我贊賞的小說他也要找來看,真夠給我面子的,納悶的是為什么我贊賞的小說他也要找來看呢,難道他不明白不同的作品感動不同的人?那部俄羅斯小說是諷刺斯大林時期的專制獨裁的,這領導一路順風順水,始終也不曾吃過多少苦頭,當然看不明白作家深藏的機鋒,看不懂表面從容敘述下的血水涌動,大概在他讀來,里面只有瑣事而已。換言之,《金光大道》或者《暴風驟雨》是不能感動我的,還有前些年或近幾年受到熱捧的好些部著名的小說,它們可能得過這種獎或那種獎,可是貼現實政治太近了,直接就貼在了政治的屁股上,不能感動我的原因也在于此。感人的作品有感人的原因,同樣的道理,不感人的作品也有不感人的原因,如果承認文學多元,這些本來都不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