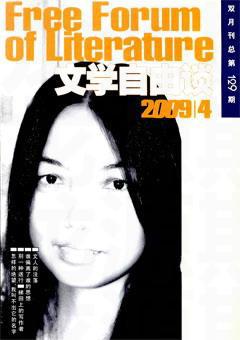謝有順回避哪些問題?
李 更
李更想約謝有順“對談”,有順先允后辭。此文便成了對談未遂的一個文本。也很有意思。只是刊出時不曉得放在哪個欄目,姑且就擱《對談》吧。
我的文學對話做了一年多了,許多朋友給予了熱情的支持并認真地配合,但有兩位朋友最后看了我的問題選擇了拒絕,一位是主動聯系我的詩人劉湛秋,一位是在廣東文壇有重要位置的謝有順。
有順兄弟在文壇上的進步就像他的名字一樣,我不知道還有誰比他更順利。原來我以為對話會非常順利、非常精彩,因為他有很好的口才,既善于采訪別人,也善于接受采訪,但是我沒有想到他拒絕我的理由是因為我不是問的“專業”問題。什么是專業問題?我有點犯糊涂。按照不才我的初步理解,他的專業問題應該是純粹的文學理論問題,這些我本來也想問,但這方面他有太多的文章和應付記者的采訪,我就不用畫蛇添足了。既然是我做采訪,當然有我的套路,我不會刻意迎合被采訪者的需要,因為我的對話不是一種政治宣傳,而是要探討一些問題,有時,辯論是必須的。如果完全要求對話者按照自己的意圖去提出問題,就不用我來麻煩了,我們的新聞機構包括作家協會會有許多的槍手,他們會比我做得更好。
下面是我和謝有順為了對話而進行的聯絡以及具體的對話問題。
有順兄:
今年差不多過半,不知兄現在有時間沒有,我做對話其實很簡單,我提出一些問題,兄可依次回答,如果同意,可將有關禁區明示,我好回避,謝謝。
李更2009.5.9
李更兄:
抱歉,最近這個月天天忙學生論文,無暇他顧,信遲復了。加上我自己的博士還沒畢業,畢業論文還沒寫出來,只好延遲畢業,現在博士論文規范很多,寫起來很辛苦,沒辦法啊。
采訪,如果能不做就不做吧,確實也覺得自己沒有什么要說的。不做就是幫忙我了,我被論文折磨得什么心思都沒有。看你的方便。如果你覺得要做,就發一些問題來,告訴我大約字數和交稿時間,我盡力回答就是。
謝謝你的信任。
謝有順,6月3日
有順兄:
真不知道你也要過考試關,其實你任何一本書都是合格的博士論文。
理解你的辛苦,但是我做對話是非常認真的,不深入研究對象我是不敢提問的,而且,你是重要人物,漏了你我的工作就不完整了,還是先感謝你對我的信任。
兄可直接在每道問題下回答,多多益善,我是拋磚引玉法。
李更兄:
簡單看了你的問題,我可能無法回答這些問題,而且我也不知該如何回答,像“你現在的名氣已經遠遠大過你的老師”這樣的話,我聽得心驚肉跳,我不知你從何處得出這樣的印象,我老師孫紹振的聲名之大,非一般人能比的啊。還有“你獨能左右逢源,成為老人和新人之間承上啟下的人物”之類,也讓我覺得像是在說另外一個人。還有諸如文學獎等有沒有潛規則之類,我怎么知道?被我們知道的規則就不是潛規則了啊。還有我是先讀博士(2006年5月錄取)再評上博導(2006年12月)的,先后順序是不能亂的,我不過是延遲畢業而已,但是博士是早于博導就開始讀的啊,這是中國大學的游戲規則,當博導就得讀博士,和別的都無關啊。我總不能當了博導就把博士也故意丟掉,呵呵。諸如此類,你的許多問題我大多都無從答起,還請見諒。以后再找機會吧。朋友間閑聊更好,我并不喜歡采訪之類,談得累。相信你能理解。
給你添了麻煩,再此致歉。來廣州時,請你吃飯吧。
祝好。
謝有順,8日
有順兄:
沒有想到你也有被難倒的時候,我一直認為你可能是惟一敢直面問題的評論家,我長期以來一直以為評論家并不是批評家,因為有批評,必然有反批評,有些批評家只能批評別人,卻害怕別人批評自己,甚至開博客,不準別人留言。
我評論作品,并不一定以表揚為主,那有時更像表演,給別人看的。
其實我是想和你認真討論一些問題,困難的是我們想問題的方法不一致。可能價值觀念不同,但不應該成為我們溝通的障礙。
另外,我說你名氣大過你老師并不過譽,我甚至認為他連我也不如,比如我1998年出版有《李更如是說》,發行七萬多冊,他在多少年以后跟風出版了《孫紹振如是說》,發行卻遭遇失敗就是例子。
可否對其他問題進行簡單回答?不能回答的就不用回答了,總不能全盤否定吧。
期待中。
李更
李更兄:
這跟能否直面問題無關,各人有各人觀察世界的角度,有不同,才有豐富性。但涉及到我的老師,我不能同意,這是我的倫理,相信你能尊重。發行量并不能說明問題,我的書最多的才發行一萬冊呢,和我老師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啊。而即便從發行量說,當年我老師的《幽默答辯五十法》發行量超過50萬冊,盜版本很多,但這并不是他的代表性著作,連劉再復都說,他最佩服的同代理論家是孫紹振。當然,行業不同,影響也是表現不同,這些其實都是次要的。但我確實無法回答這些問題,還請見諒。加上手頭被論文困住了,很難集中心思,下次吧。
祝好。若來廣州,還望聯系。
謝有順,9日
有順兄:
我們似乎跑題了,爭論你老師的問題好像已經無聊,但我還是非常感動,現在這樣捍衛自己老師的已經不多,我認為這是一種美德。
除了這些禁區,應該還是可以回答其它幾個問題,不會都是禁區吧?
李更兄:
這次采訪還是不做了吧,我實在回答不了這些問題,一回答,好像就是在辯解似的,這非我本意,我從來不試圖去辯解什么,哪怕是天大的誤解,我也養成了不辯解的習慣,文壇就那么點大,辯來辯去有什么意思呢?我早已對此失了興趣。
因此,除了工作的義務,我接受采訪,一般只談專業問題,而專業往往是枯燥的,這也非你所感興趣的,所以,非常抱歉。下次吧。其實,見面聊天可能比采訪更有趣,也更真實,相信你能理解。
祝好。
謝有順,16日
采訪謝有順提綱:
1:聽說謝有順這個名字,源于一次關于神童的傳說,他們說你在大學生時代就替老師捉筆,以假亂真,甚至比老師寫得還好,事實也是如此,你現在的名氣已經遠遠大過你的老師。有人說,實際上你只是福建長汀一個農民的兒子,沒有任何家學,是真正的天才,是嗎?
2:很多人知道你的智商高,其實你的情商更高,在今天的中國文壇,派系林立,不光是同輩人容易有矛盾,不同年齡段的寫作者更容易出現所謂代溝,傳統上老作家對年輕人的那種傳幫帶幾乎沒有了,因為文壇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名利場,相互之間充滿敵意,而你獨能左右逢源,成為老人和新人之間承上啟下的人物,你的秘訣在哪里?
3:我們知道,在中國文壇,背景和平臺是非常重要的資源,沒有這些,你就沒有話語權。比如說同樣是評論家,在北京寫作和在廣州寫作的影響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全國各地的寫作者都拼命往北京跑,到了北京就可能成為中央軍,而在地方,你再努力,也只是地方軍。這也不是現在才這樣,當年,沈從文無論如何都要留在北京那個大碼頭。我想知道,你當年為什么選擇廣州?
4:作為華語傳媒文學大獎的主要推手,你們當初是否有“另
立中央”的企圖?因為北京的所謂國獎多少年來囿于體制、延于眼光、誤于人情,漏掉了許多真正的好作品,你們的出現,對文壇進行重新梳理,樹立了新的文學標準,你們認為是代表了理想的民間方向嗎?還是想塑造另外一種權威?
5:我知道,在南京,也出現了大學有關人士組織的文學獎,其實在各個地方,目前已經有非常多的評獎,有的獎金并不比你們開出的少,甚至已經有聲音說你們是同仁獎,評委只有幾個人,代表小眾的胃口。還有說法,你們的獎是文學超女獎,講究的是娛樂功能,有嚴肅作家甚至拒絕你們的獎,還傳說你自己都要退出這個獎的操作,是嗎?
6:你一直重視發表文章應該是在所謂權威雜志而不是出版成書,因為現在出書實在太容易了,只要你有幾萬元,就可以找個出版社買個書號。有人說你認可的是“判官”裁判法,有編輯把關固然重要,但是我們知道,許多編輯自己的水平就不行,說他們思想傳統已經是厚道,許多雜志的編輯或者是通過大學分配,或者是走后門,甚至還有子承父業頂職的,他們中很多人并不愛好文學,只是作為一個飯碗而已,正是因為這些編輯的存在,幾乎所有的純文學雜志都失去了自己的市場,他們把大量代表新生代的文學力量擋在了文學的大門外,這是有目共睹的。就我了解的,××、×××、××××、××(責編注:此處系本刊處理)等等,真正有文學市場的作家甚至是反感在雜志上發表文字的,他們不認可中國文學雜志的編輯權威。你還是覺得在雜志上發表真的那么重要嗎?
7:在廣東文壇,北方作家的本土化有著特別的意義,一直有一些看法,認為在廣東這樣商業化十分嚴重的地方,作家們的思想已經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向去發展了,他們因著生存的危機感,無法安靜于書桌,所以本土作家沒有像內地作家那樣拿出厚度和深度都引人注目的文學作品,為了在市場經濟成功以后順利地完成文化的升級,找“外援”是一條不錯的捷徑,說白了就是引進“雇傭軍”,現在在廣東生活的、在廣東文壇活躍的許多作家,在來廣東之前,在其家鄉已經是非常成熟的作家了,有的甚至是很有成就的作家了,廣東作協的拿來主義在全國寫作者中間非常有影響,包括你,也是外來戶,怎么看這個問題?
8:其實歷史上,有相當多的作家都在廣東呆過,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近現代文學史上留下名字的作家不下百人吧,他們不僅在此生活,在這里收獲愛情和作品,甚至還在這里走完人生,如肖紅,但是他們都沒有打上廣東作家的標簽。惟一的歐陽山,知道他實際上是湖北人的恐怕沒有多少吧,歐陽山是真正本土化的代表,但他不屬于“外援”。“外援”也好,“雇傭軍”也罷,都是有組織地進行的,自然地流人不屬于這個范疇。我想說的是,這個“外援”能不能本土化的問題,有沒有水土不服的問題?比如,已經有一些作家在家鄉創作了很好的作品,而到了廣東,多年沒有有影響的作品,甚至數量都少了許多,生活質量上去了,作品質量卻下降了,你認為是什么原因?
9:無論今天的中國文壇有多熱鬧,誰也不能決定誰的作品可以永垂不朽,或者說是流傳下去,真正有市場的還是四大名著,新中國以來,中國文學很少出現成功之作品,我認為主要是因為作家們急功近利,沒有創造出類型化人物形象。所謂類型化人物,就是可以代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制度下產生的典型人物,比如阿Q,孔乙己,祥林嫂,魯迅因為這三個人物而成為魯迅。
為什么百多年來圖書一直是四大名著的天下?就因為四大名著的每部作品里面都有至少十個以上的類型化人物,這些人物甚至在今天還是家喻戶曉的,他們融人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可是同樣是今天,還有多少小說能夠出現這樣類型化的人物形象?我估計的數字非常悲觀。你的看法呢?
10:最后再說個八卦的問題,許多人知道福建的文學就是詩歌,因為有舒婷,因為有蔡其嬌,因為有1980年《福建文藝》的關于“朦朧詩”的討論。其實我們知道,福建文壇真正的意義是出了一大批有全國影響的評論家,劉再復、劉登瀚、蔣夷牧、南帆、孫紹振,包括你,這是一種地域因素嗎?現在的文學評論家,有許多被人指證為紅包評論家,他們熱衷于各種各樣的評獎活動,喜歡各種組織和個人的作品討論會,很多評論家,作品都沒讀,就信口開河,只要你給錢,他就敢幫你說,你遇到過這樣的情況嗎?還有,這些年多被文壇垢病的各類文學獎,里面到底有沒有潛規則?有不少現在很牛的作家公開說自己從來不看評論家的文字,也從來不在乎評論家的意見,但是私下里又不斷去找各個評論家幫忙,你遇到過這樣的人嗎?遇到以上這些人和事,你會怎樣對待?
11:另外還有個問題,你已經是中山大學的博導了,為什么還要去讀復旦大學的博士?是別人認為的作秀?還是真正想從那里學點東西?我知道中大有些師生是不滿的,比如徐晉如,因為他在中大讀博士,你這樣做,中山大學被人認為是復旦大學的兒子輩了。有人說,你本來在《南方都市報》已經有非常優厚的待遇了,并且,那里是文學宣傳十分理想的平臺,但是因為中山大學每年會給你幾十萬的課題費用,這對于文學似乎更加有實際意義,所以你選擇去大學。是真的嗎?幾十萬是什么概念?50萬還是80萬?是用在出版著作還是旅行、開會、洗腳、吃飯?(可以不回答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