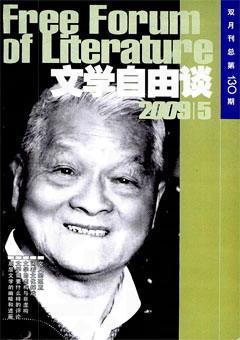“我要和你結婚”
陳歆耕
“我要和你結婚!”
“你說你沒想好?我知道你是嫌我長得那個了一些,你看我五官一個也不少,且功能都很正常。哦,個子是矮了一點,但你不了解個子矮的人普遍要比個子高的人聰明嗎?魯迅、拿破侖個子都不高……”
“你居然還是不愿意?唉,真是不可理喻……”
我這里不是在寫小說,也不是探討婚戀問題,而是比喻一種不正常的思維邏輯: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一廂情愿”、“強人所難”!如今,一方未得另一方同意而能成婚的可能幾乎沒有了,婚姻法規定戀愛自由。“捆綁不成夫妻”,大概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但持有“一廂情愿”、“強人所難”思維方式的人,在生活中并不少見。現舉近期發生在文壇的一例:
李更先生在剛出版的《文學自由談》第四期發表了一篇《謝有順回避哪些問題?》的文章,文章放在“對談”欄目下,其實只是作者的自說自話。文章的主要內容是說,作者要與評論家謝有順做一個訪談,或叫對談。作者設計了一些問題,用電子郵件發給謝有順。謝有順在看了他設計的問題后,婉拒了他的訪談要求。作者則三番五次地寫信要求謝有順回答他的問題。在謝有順婉拒回答他的問題后,作者就在這篇文章中公布了他與謝有順的往來信件和他設計的采訪提綱。看了這篇文章后讓我頓生很多感慨,有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也借此就教于李更先生——
其一,李更先生想采訪謝有順,無可厚非(且不論在目前體制下,有關部門規定要進行采訪須持有新聞出版署頒發的記者證)。但謝有順先生也同樣有權利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訪,這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但是作者“死打硬纏”式地三番五次說明理由,要對方回答他的提問,這既失自己的尊嚴,也是對對方的不尊重。其“強人所難”的思維方式,與本文開頭的比喻如出一轍。我覺得,謝有順先生表現得夠有風度,夠有耐心的了。反復在信件中說明難以回答他問題的理由。其實,他不需要作任何解釋,只要說一句“我對你的訪談沒有興趣”即可。
其二,在訪談不成后,作者未經對方同意,擅自在文中公開發表謝有順給他的信件,這是極不妥當的。不管謝有順的那些信件是否適合公開發表。同時,公布自己設計的問題提綱,以此告訴公眾:謝有順是一個不敢直面現實問題的批評家。這也有失做人的厚道。其實,看了作者設計的那些問題提綱后,也許讀者會得出恰恰相反的印象吧?不是謝有順不敢直面現實問題,而是那些問題大多都很無聊。
其三,從作者設計的訪談提綱看,問題多多。謝有順拒絕回答是正常的,如果接受了他的訪談,我覺得謝有順恐怕就不是現在我們所知的謝有順了。李更先生提出的很多問題,凡屬有正常思維的人,都難以回答。有例為證。且看第一個問題:“……你現在的名氣已經遠遠大過你的老師。有人說,實際上你只是福建長汀一個農民的兒子,沒有任何家學,是真正的天才,是嗎?”設身處地為謝先生想想,他該如何回答這樣的問題?謝有順在回信中說:“這樣的話我聽得心驚肉跳,我不知你從何處得出這樣的印象,我老師孫紹振的聲名之大,非一般人能比的啊。”不管謝有順和孫紹振比,誰的名氣大,但提出這樣的問題,一開始就逼著學生“冒犯”自己的老師,是要陷學生于不仁不義的地步,真是讓人匪夷所思啊。尊重乃至敬畏自己的老師,大概也算中國人的一個永遠不應過時的傳統美德。提問者難道連這樣的“常識”也沒有?另外,我第一次聽到中國的文學評論界還有“天才”一說,那怎么還有很多人唉嘆中國缺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樣的批評大家?謝有順是該順著對方的提問,承認自己是“天才”,或是謙虛地解釋“我不是天才”,呵呵,回答這樣的問題實在是風險重重。
再看問題二:“很多人知道你的智商高,其實你的情商更高,在今天的中國文壇,派系林立,不光是同齡人容易有矛盾,不同年齡段的寫作者更容易出現所謂代溝,傳統上老作家對年輕人的那種傳幫帶幾乎沒有了,因為文壇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名利場,相互之間充滿敵意,而你獨能左右逢源,成為老人和新人之間承上啟下的人物,你的秘訣在哪里?”且不談,李更先生用“充滿敵意”,把文壇描繪成閃爍刀光劍影的可怖“戰場”,是否有點危言聳聽?稱一個人“左右逢源”,且要他介紹“秘訣”,這對被訪者是一種褒獎,還是侮辱?呵呵,提出此種讓你心里感到不快,同時還要你回答問題的人,真是太有才了。
問題四:“作為華語傳媒文學大獎的主要推手,你們當初是否有‘另立中央的企圖?……”看了這個問題,我也感到“心驚肉跳”。它讓我自然聯想到了長征途中另立中央的張國燾。如此充滿“火藥味”的問題,簡直是把被訪者逼到了“刀尖”和墻角。你要不進入訪問者的問題圈套,承認自己有此“企圖”(謝有順有此“賊心”和“賊膽”嗎?);要不你堅決否認,讓人感到你很“虛偽”,說著言不由衷的話。
限于篇幅,無法一一列舉其中還有的一些問題。李更關心的是“文壇八卦”,而不是想與一位評論家探討文學問題。還有一些他在提綱和信件中所表達的觀點,稍有“常識”的人也可分辨出是破綻百出的。如李先生說到因文學雜志編輯水平不高,“幾乎所有的純文學雜志都失去了自己的市場……”只要對文學期刊生存狀況稍有了解的人,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嗎?文學期刊衰落的原因,恐怕遠遠不是如此簡單吧?把所有的文學期刊都辦成郭敬明的《最小說》那樣的東西,大概在中國也行不通的吧?還有,李更在給謝有順的回信中說到謝有順老師的名氣,甚至連他李更也不如,因為他的一本《李更如是說》發行到7萬冊,而孫紹振“跟風”出版的《孫紹振如是說》,“發行卻遭遇失敗”。文學作品或圖書與市場的關系,因素非常復雜,至今未有人能說得清楚。按照德國漢學家顧彬的觀點,在德國普遍認為,一本文學作品發行量高了,肯定是一本低俗讀物。當然,他的觀點也可商榷。但起碼可以說,發行量的大小與一個人的文學成就或名氣,并不完全成正比。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是用文言文寫成的80萬字的巨著,其受眾量、發行數或許也不如李更的“如是說”,但兩者的學術水準能放到一個天平上去評估嗎?李更先生以區區7萬冊發行量而自炫,不覺得可笑嗎?有些80后、90后青春寫手寫的書,常常發行到幾十萬、上百萬冊,如以此論“英雄”,李更先生顯然得拜他們為師了。
筆者在文中多次使用了“常識”一詞,深感梁文道先生說的這是一個“常識稀缺的時代”,確實切中肯綮,指出了一個我們這個時代普遍存在的“病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