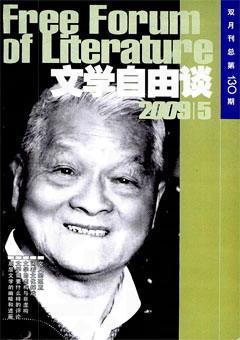獨特而高貴的“獨唱”
向衛(wèi)國
幟下發(fā)韌和成長起來的。比如翟永明式的女性獨白,伊蕾式的身體展銷,無不昭示出女性在存在意義上的當代歷史悖論:一方面是近乎決絕的反抗姿勢,另一方面是種種反抗最終都因其身體或心靈的裸露與被消費而自我消解,女性在強化自我意識的同時,也強化了其歷史的“他者”形象。
劉虹的“女書”一輯,顯然具有向這種可悲的歷史悖論挑戰(zhàn)的意味。她既沒有進行如泣如訴的內心獨白,也沒有以任何姿態(tài)當眾進行身體撫摸,而是以一個社會批判者的立場從多種視角切入這一主題。《特區(qū)的她們》、《封面上的她們》和組詩《深圳打工妹》等,直接將關注的目光投向她身邊那些飽受欺凌的底層婦女。如果說“打工者”是這一時代的弱勢群體,那么這些詩中的姐妹就是“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她們?yōu)樯娓冻龅模潜饶行源蚬ふ叨喑鰯?shù)倍的傷痕和淚水。面對《飄落的樹葉》中那個寧可跳樓也不賣淫的打工少女,當代文化和詩歌中那種搔首弄姿的身體舞蹈難免暴露出某種輕佻,甚至是故作傷感式的小資矯情。在血淋淋的事實面前,語言的力量是蒼白的。通過飽含悲憫的陳述,來呈現(xiàn)令人痛切的生存現(xiàn)實。這是劉虹詩歌的第一種女性視角。
而她的名篇《致乳房》,則將一場思接千古的“殺戮”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其驚心動魄的程度更不是一般的女性獨自可堪比擬。表面上看,這只是由于肉體的疾病所引起的一次外科手術,但由于其部位的特殊(乳房),詩人異常地敏感,迅速地從身體的體驗上升為對女性歷史深刻的洞察,由此展開了她獨特的文化批判。“你恣肆得一直令我驕傲,可里面充塞著到底幾處是陰謀,幾處是愛情?”詩歌從對乳房的歷史反思開始了生命的詰問,把女性的生命之痛超越個體而指向文化和歷史的:“而你是歷史,終要把心底的創(chuàng)傷移民到皮膚上”……這里有著鮮明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一種“乳房政治學”或“身體修辭學”的發(fā)明。詩人憑借著這一發(fā)明,再次顯示出強悍的批判立場。這是詩人的第二種女性視角。
從寫作和修辭的角度看,劉虹女性主義詩歌的代表作是《沙發(fā)》。這首詩可以說是對上面的現(xiàn)實立場和一般的歷史隱喻的雙重超越。“沙發(fā)”是詩人的獨特發(fā)現(xiàn),從表象到本質都極其符合女性的身體和歷史存在的性征,詩歌因此上升為一種整體性的象征。詩中每一句都是說的沙發(fā),每一句又都是說的女人,甚至暗藏著中國式的哲學:“使事物堅硬的一端頓時服軟”。但這種看似辯證的陰陽哲學中卻有不變的歷史本質:“從不許它站起來。”的確,中國就是一個哲學與歷史或者說思維與道德互相矛盾的國度,其中歷史和道德的維度總是占據(jù)著矛盾的主導方面。由于詩人對女性的歷史本身有著深透的理解,一旦發(fā)現(xiàn)了“沙發(fā)”這個絕妙的象征物之后,詩歌在極其輕松自如和幽默的輕諷語調中一氣呵成,對“沙發(fā)”這個形象進行的語義闡釋,像哲學論辯一樣精確,又像數(shù)學論證一樣充分;又由于“沙發(fā)”的整體性象征,每一句詩的深層意義和表面的語義幾乎達到了一一對應,使詩歌從內容到形式都堪稱完美。這是第三種女性的視角。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無論哪種視角,劉虹都不同于當代女性詩歌中流行的個體陛書寫,而是從宏觀的社會現(xiàn)實立場,為所有的“她們”集體立言。詩人一向反對那種自我撫摸式的小女子情調的詩歌,而是如作者所言:“我秉持‘先成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邏輯,強調‘大寫的人的詩歌,不把自己超前消費成‘小女人。”
四、“重”與“大”:詩歌價值觀的轉喻
綜觀劉虹的全部詩歌,《我歌唱重和大》是一首既具有現(xiàn)實的針對性,又隱含著詩人的詩歌價值觀的重要作品,它涵蓋了其全部詩作的終極性追求。一首歌唱“重”“大”之詩,隱含了詩的“重”“大”;反過來也一樣,詩的“重”“大”,使這首詩成為“重”“大”之詩。“重”和“大”成為一種詩歌價值觀的轉喻。因而這首詩跟《打工的名字》一樣,具有了“元詩”性質。詩中甚至有一段是直接“論”詩的:詩人耍空城計,他發(fā)誓要在詩里小得——找不見自己!詩前讓體溫小到0詩中消滅心跳和靈魂,以便詩后進駐文學史,比的是誰更小家子、小油子、小痞子女詩人比拼暴露癖,用詩引誘施暴兼自我施暴,玉體放逐了玉,剩下肉體一謙虛,就小成了負數(shù)。
這是對中國當代詩歌現(xiàn)狀的個人判斷和鞭辟入里的批判。詩歌既批判了現(xiàn)實中把一切重要之“事”往“小”里做的男人政治,也批判了爭著“做小”的女人伎倆,同時還批判了“耍空城計”(“找不見自己”;自我“小成了負數(shù)”)的當代詩歌,等等。豎著看,這是一種具有悠久源頭的歷時『生的詩歌價值的堅持;橫著看,這是一種共時性地對我們時代普遍存在的精神矮化和虛無主義的反抗。
可惜的是,我們時代的詩歌現(xiàn)實只有兩種:要么是精英化的技術主義,要么是民間化的口語主義,劉虹顯然兩種都不沾邊。尤其是,作為追求人格尊嚴、獨立思考的嚴肅詩寫者,劉虹始終拒絕加入詩歌江湖上任何一個為爭奪話語權而黨同伐異的小圈子,這正如評論家陳超所指出的那樣:“在中國詩壇習慣于拉幫結派利益共享的詩歌場域中,劉虹卻堅持個人化的寫作和思考,她讓寫作成為了生存和語言的真實摩擦,實現(xiàn)了寫作的真實感和緊張感。她成了無法被通約的‘這一個詩人。”
劉虹這種獨特而高貴的藝術品質,似乎注定了她作為一個詩人,只能獨享時代的寂寞。“重”“大”的詩歌和詩歌的“重”“大”,都只能在漫長的等待中,或者被歷史湮滅或者被歷史認證。但不管結局如何,都與詩人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