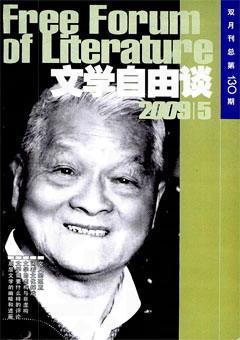關于《天行者》的問答
胡殷紅 劉醒龍
胡殷紅(下為胡):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您創作的《鳳凰琴》的故事感動了無數人。時隔十余年后,您怎么會再次想起續寫《鳳凰琴》,續寫民辦教師們的生存情狀,是什么緣由調動了你的創作熱情?
劉醒龍(下為劉):中篇小說《鳳凰琴》在《青年文學》1992年第五期發表后,編輯收到大量讀者來信,有許多人提出希望讀到《鳳凰琴》的續篇。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高揚同志,曾在《光明日報》上著文,也提及這樣的希望。我沒有趕那個熱潮,一方面是個人性格,不喜歡隨大流,就像這些年流行淺俗易讀的小長篇,而我偏偏要寫被人疑問“百萬字的長篇誰看”的有內容的厚重之作。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誤讀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體無意識”,不去細心地發現文本的真實意義,那樣的寫作不僅是無效的,甚至是負效果的。然而,這并不等于說,我不想寫。事實上,這么多年我一直在悄悄做著準備,無論是在青藏高原深處,還是在東南沿海,只要有機會見到鄉村學校,哪怕只是進去看上一眼,我也要進行一定的了解。并用各種形式,記錄下許多靈感。這么多年,有過太多想動手寫作的欲望。去年有機會遇上一位來
胡:在創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現在回頭來看,小說是否留有遺憾?
劉:一個成熟的作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寫作情緒,激憤是小說的天敵。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就這部小說來說,即便是在這一點上做得不好,我也不會遺憾。
胡:小說中寫到了多個人物,你最喜歡的是誰?為什么?
劉:我喜歡鄉村中所有的人。在這部小說中,我最喜歡的是葉碧秋的那位苕媽。信不信由你,在豐厚而神秘的鄉村,一棵從不言語的大樹都會是曠世的智者。
胡:小說對夏雪的悲情塑造似乎過于殘酷,這樣塑造她的好處在哪里?
劉:也許生活中,像夏雪這樣既時尚又純美的女孩,是惟一的。我希望她是一種美的標本。我更希望她是一種美的真實。
胡:說到農村教育,這些年有許多大學畢業生到農村支教,他們的到來為農村師資力量注入新鮮活力,對于這支隊伍您怎么看?
劉:我敬重一切前往鄉村任教的人,不管他們是以何種理由,也不管他們心懷何種想法,哪怕他只在某所學校里呆上一個星期,只要他教會孩子們一個字。
胡:你想在《天行者》中表達您的一種什么樣的情緒,是對民辦教師的同情,還是對教育體制的控訴?您在《天行者》中對民辦教師和農村教育的思考是什么?與寫作《鳳凰琴》時的思考有什么不同?
劉:在好的小說中,所描寫的某種行業,只是背景與載體,目的是讓思想的舟駛向遠方。與民辦教師之卑微相同的職業還有許多,好的小說不應當被理解寫了這個行業,就是為了解決某個行業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從中發現生命在最卑微時所展現出來的偉大意義。
胡:現在許多地方取消了民辦教師,對于“民辦教師”這個職業行將終結您如何評價?您曾說過他們是“20世紀后半葉中國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間英雄!”請展開給予闡釋。
劉:“民辦教師”是一段誰也繞不過的歷史。稱他們為“民間英雄”,是一種藝術的說法,就其貢獻來說,完全應當稱之為“民族英雄”!上個世紀后半葉,在急需人文教育的中國鄉村中,大部分教鞭都執掌在“民辦教師”的手里。如果不是他們的存在,中國的鄉村將會更加蒙昧。也正是由于民辦教師的存在,后來出現的社會大變革,其艱難程度也減輕了許多。這個時代太容易遺忘了。好像不丟掉歷史,就沒有未來。其實正好相反,沒有歷史就沒有未來。面對急劇變化的上個世紀最后30年,除了金錢與財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記得還有什么值得長存于記憶之中。即便是將日子過得較為舒緩的鄉村,急于忘記過去的也大有人在。而我,是一個十分戀舊的人。一想到往事,一方面會感動,一方面又會恐懼。文明的堅守傳播,不是自生自滅的野火,而必須是代代相傳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滅。依據官方的說法,“民辦教師”這個歷史遺留問題,已經全部解決。實際上,所謂解決,也就是“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鄉村代課教師的出現。他們的處境,甚至還不如當年的“民辦教師”。小說中,有這樣一段描寫:縣委領導中,有些人很鄙視民辦教師,說他們是不合格的教師,本來就該被淘汰。有人站起來,要在座的受過民辦教師教育的人舉手示意,結果,大部人將手舉了起來。這是一種誰也繞不過去的沉重的歷史。作為鄉村知識分子的這一類教師,一切的鄉村奇跡的醞釀與發生,本應當首先歸功于他們。然而,荒誕讓歷史與現實一次次地無視其偉大得不能再偉大的貢獻,以至于淪落為被人拒絕理解的地步。這一點也正是時代正在流行的頑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李清照的詩,正是剛剛過去的那個年代的鄉村知識分子的無與倫比的寫照。